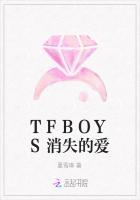后来才知道,因为见我喜欢那款游戏,志浩花了一千五百元钱,从一个老玩家手里买了“锦绣公子”的号过来。我心里是觉得有些不舒服的,一千五百元钱,买个游戏号,原本我们玩电脑游戏就是因为这种娱乐方式既可以消遣又比较节省,一千五,那是我辛苦两个月的薪水啊。何况我也不是那么喜欢玩游戏的,我对游戏的喜爱远没有到花钱进去的“痴迷”程度,之所以玩“剑侠”,更多的是因为喜欢和志浩在里头一起“打拼”的感觉。
但我也没抱怨他,无论如何,他也是为了我好,况且,男生在生活上、在理财上,比女孩粗放些、幼稚些,也是可以理解的,至少比精于算计的小气鬼要强。我公司里的男业务员就各个比女同事会算小账,偶尔在单位午餐,派他们去跑腿买盒饭,交到他们手上的饭钱是要一角一角数清楚的,生怕自己会赔钱进去;更有甚者唯一一次五个业务员一起出去吃饭,每人一碗四元钱的旦旦面,唯一的一个男生刘明辉吃完竟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好似不晓得饭后还有“埋单”这回事儿,后来我实在是忍受不了,去付了账。回到公司,另外三个女生都分别把钱给了我,那个刘明辉没给,我倒但愿他是忘记了。
慢慢地我发现,不只刘明辉,公司里的男同事普遍要比女同事会算计、会计较。或许,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吧,或许,是由于这个让人不得不低下头的现实吧。我能理解,并且也不想批评他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但是我还是觉得悲凉。我记得在家时,父亲的同事聚会都是他付账的,有时家里也会出现“财务吃紧”的状况,可母亲从未因此对父亲有过半句怨言,她说,男人,场面上的事儿,总要撑的。
有一天在办公室翻看一本杂志,上头有一位很女权主义、说话很尖刻的女作家在一篇短文里写道:“想找个像个男人的男人可真难!现在的男人越来越小气、越来越没有男人味、翘着兰花指打着小算盘,帅的标准也越发的扭曲,流行那种看着就让人起腻的小白脸,男性特征越来越少,基本被女性同化。”
我笑,我的志浩虽然不太会打算,虽然总会心血来潮地乱花钱,可是,至少,他是个“像个男人的男人”。
后来的一件事,更加地让我认识到了我的男同事的“算计与计较”,甚至是“手段与阴谋”,事情还是发生在刘明辉身上。
新招入公司的七个业务员里,有三个试用期内没有业绩,被辞退回家,两位达到了即定目标转成“正式员工”。虽然正式员工也没签合同、不上保险,但工资比试用期加了三百元,而且也终于是脱了“试用”的帽子,这些已经足够让人羡慕的了。
我和刘明辉被延长了试用期,我更加努力地去跑业务,经常连午饭都顾不上吃,回了公司乘着老业务员心情好就赔着笑脸向他们请教。我的确是很着急,我也不想掩饰我的急切,我急切地想做出业绩,早日转正。
可刘明辉却一点儿也不急,也不太出去跑业务,总是窝在公司里喝茶和接待兼文秘小齐聊天。有一次被田总碰上了,瞪了他一眼,他才每天和我们一样早出晚归了,只是,经常听其他业务员背地里说,他每天躲在游戏厅打游戏。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工作后的第三个月,我终于看到了希望,迎来了一个“奇迹”。一家小品牌的饮料工厂,策划部姓薛的经理竟然是华城人,我的老乡。我一开口,熟悉的乡音便融化了他原本挂在脸上的冰霜,他招呼我在办公桌边坐下,并且,给我倒了杯茶。
捧着热呼呼的茶杯,我的心里也暖暖的。
薛经理跟我说,他们公司有新品上市,正有广告投入计划,如果我们能在现在报价的基础上再低百分之三个点,那么我们的价位就比他们自己去报社打广告要低了,那样他们就完全有可能和我们合作。
然后他说出了一个广告预算的数字,我的心跟着狂跳了几下,按照那个数字算下来,我个人的提成,也会有五位数的数字了。而且,比报价再低百分之三个点,这个,并不难做到,我们公司和各大媒体、报社都有长期合作关系,他们给我们的价格比给一般商户要低五到八个点不等。
我兴冲冲地赶回公司,一路上,头脑里充塞着“守得云开见月明”、“坚持就会胜利”等激昂的句子。我终于要成功了,虽然这只是一小步,但这证明我还是有能力的,我还是出色的,我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就像在学校时,我坚信自己的能力一样。
销售部例会上,我如实汇报了饮品公司的情况,并且说如果公司报价能达到对方的要求,这一单,我有极大的把握能拿下来。
张经理听完了我兴奋的讲述,冷静地沉思了一下,说:“这样,小周,报价的事我先和田总商量一下,你那边也别透出口风说公司一定会做到他们想要的价位,先拖一拖,冷他们一段儿,或许公司不用做那么大的让步也能成交呢。总之这事急不得,你急了,就被动了。”
“可是,张经理,那边等我的回话呢。”我如何能不急啊,几十万的单子,那对我可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啊。
“那边你先别露面,他要是打电话给你,你就说公司正在争取,正在商量,拖他几回,把他拖急了,我们才有主动权!就这样,按我说的做。”张洋斩钉截铁地结束了关于我那张大单子的话题。
想了想,我觉得,或许张经理说的是对的,毕竟,他是个有过十来年业务经验的老业务了,而且他还是我的领导,无论从对经验的尊重还是从所处的位置上说,我都应该相信他。
于是我整整一周没去回访薛经理,没和他有任何联系,可是我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在记挂着我的大单子。我一次次地压抑着去找薛经理的想法,张经理说,要拖着,拖到对方急了,我们就有主动权了。可客户那边总是没有消息,现在急的是我,再也“拖”不下去的也是我。
我终于又一次去拜访了薛经理。薛经理对我还是很客气的,却没有了上一次的热情。
我急忙先赔礼说这阵子公司太忙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拜访,然后又和他讲了讲来前特地从网上搜集来的这几天发生在华城的一些新闻,在气氛再度变得亲切之后,我把话题引到了广告业务上。
“报纸广告不是和你们公司签了吗?而且还是我们公司副总做的决定。你不知道?我还想呢,怪不得我那个小老乡不见了踪影,原来是搭通了天地线直接找上公司老总了,自然就不用再来找我这个老乡了。”
好不容易等薛经理说完了语中带刺的一段话,我急忙问:“和我们公司签了?薛经理,是什么时候签的?是跟谁签的?签了多少?”
“就是你上次来之后的三两天吧,签了一个季度的广告投放,价位就是我和你要求的那样。来签合同的是你们公司的一个经理,姓张的,还有个业务员,是个男的,不记得姓什么了。对了,我有他的名片。”薛经理打开抽屉,拿出数十张堆放在一处的名片,“你等等,我找找啊。”
“不用了。”我有气无力地说,我已经看到了那张熟悉的深蓝色的名片,就在上面第三张,名片上的名字是“刘明辉”。
我急急地赶回公司,一路上胸中的一口闷气没有丝毫平复,反倒是越想越气愤、越想越委屈。凭什么,我开发的客户他们去签单,而且竟然不通知我一下、告诉我一声。欺负新人,也不是这样欺负的,而且,那个刘明辉他不也是新人吗,他不也是和我一样的没达到业绩目标的“试用员工”吗?
没有敲门,我径直走进张经理的小办公室,屋里两个人正在喝茶,见我闯进来,一齐抬头直直地看着我。是张洋和刘明辉。
张经理皱了皱眉头,看似对我的不礼貌有点不满。刘明辉端起茶杯,喝了口茶,借以掩饰着他脸上的慌张。
“张经理,我刚从‘新果乐’饮料厂回来,他们说已经和我们公司签约了?”我站在门边问。
张洋不置可否,指了指刘明辉身边的另一张椅子说:“坐。”
我站在门边不动,盯着张洋:“张经理,我是问,新果乐是不是和我们公司签约了?”
“噢,已经签了。”张洋说。
“和谁签的,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再问。
“公司签约一定要通知你吗?至于是和谁签的,这个你更没必要知道。”张洋的语气变得生硬。
“公司签约的确是没必要通知我,可是,那个单子是我先联系的,是我的业务范围。你不想告诉我是和谁签的也没关系,我已经知道了。”我看了看刘明辉,“是和你签的吧,刘明辉,而且是张经理和你一起去新果乐签的约,对这事儿我不想和你理论。张经理,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我的单子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成了别人的,请给我个理由!”
“新果乐公司的确是你先接触的,但是并不能说那就是你的单子,你还没有签约对不对?以你个人的能力,未必能签下这个大活儿来。刘明辉和那家公司的管理层能搭上关系,能说上话,这才是直接促成签单的关键。因而这个单子落在刘明辉名下没什么不对。”张洋说。
我不说话,双手的十根指头却紧紧地绞在一起。他说的全是谎话,他在骗我!如果刘明辉真的与新果乐的什么管理层有关系,那么在我知道这家公司要做媒体投放前他完全应该更早地得到消息,而且那天例会上我汇报情况的时候,如果刘明辉有这样“优越”的条件,他也一定会马上提出来,那样,这个单子就会名正言顺地落到他的头上了。背着我去签单,签了单近一周也不走露半点风声,这一切只能说明,他们心里有鬼。刘明辉和新果乐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事实,就像刘明辉是财务人事经理刘鸿滨的侄子一样的事实。
“小周,虽然单子是小刘签的,但是信息总是你先收集到的,所以这单生意,也不能说你完全没有功劳。这样,业绩记在小刘的名下这是没有疑问的,提成方面,我从小刘的奖金里提出百分之十,作为对你的奖励,你看怎么样?”虽然是商量的语气,但张洋看向我的目光,却没有半点商量的意思。
我笑了,难道这一切不好笑吗?明明是他们强抢了我的劳动成果,现在却拿出百分之十来,反倒好像对我进行了格外的“恩赐”一样,表现得那样的宽容大度并且等待着被“施舍”的我马上做出感激涕零的表情;而更好笑的是我,明知道是这两个人狼狈为奸,共同在我这里巧取豪夺我的胜利果实,我却偏偏送上门来,妄想向他们讨个公道、要个解释!
我向张洋这样说:“不必了,张经理,既然是刘明辉的业绩,分给我百分之十又算什么?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不会去沾不属于我的东西。张经理,我辞职,除了您批准以外,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张洋和刘明辉一齐望着我,带着点惊异。我在他们的目光里,微笑。
离职手续办得很快,我填了张单子,张洋签了字,田总不在公司,像我这样的业务员离职也不必惊动公司老总。据老业务员讲,离职最难过的一关在财务刘鸿滨那儿,他会想尽各种名目克扣员工的工资。
拿着辞职审批表走向财务室的时候,我想如果刘鸿滨为难我,我就和他大吵一架,拼着这半个月白干了,我也要出了这口恶气。那时的我身体里充满了力量,一种愤怒的力量,从未有过的一种想要大声地把自己的怒气吼出去的冲动。
刘鸿滨却没给我发泄的机会,他把我的工资尽数结给我,甚至还有一小笔刚刚发布还没收回广告发布费用的小单业务的提成,他也提前结了给我。他一定是早就在他侄子那里听说了我辞职的始末,巴不得让我尽快干脆利落地离开公司,永远也不要回来。
走出公司的大门,我没有去回下深洼的车站,我延着门前的公路向前走,一直地走,越走越茫然,越走越心酸。我失业了,我又要回到原点重新寻找工作,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以这样一个仓皇的结尾急急收场,除了口袋里的四百块钱,我还收获了一场令我愤怒的愚弄。
前方的路又在哪里呢?我的下一份工作又将在何处呢?
天空忽然就阴暗下来,仿佛是为了配合我的心情。短短的十几分钟,四点多的北京,竟然黑暗得像是晚上七八点钟的样子,狂风乍起狂烈地撕扯着我的长发,轻而易举地穿过我的风衣,寒冷倾刻侵袭全身。瞬间便是瓢泼般的大雨,披头盖脸地落下来,雨下得焦急、狂乱,不由分说。雨点落在地上,带起阵阵雨雾,周围的景物变得模糊,人们四处寻找着藏身之所,不一会儿,我周围已经没有几个行人了。
我寒冷、恐慌、害怕,我努力地睁大双眼,四处搜索着希望找到一些熟悉的景物,希望弄清楚我到底身在何处。我想回去了,回到大学村,回到我和朵朵的家里。至少,那里可以遮风避雨,至少那里感觉不到寒冷,至少那里有朵朵、有丹露,有许多我熟悉的人,至少,那里还有志浩……
可是,我竟然找不到一点儿与记忆中相关的景物,我迷路了。
我加快了脚步,我在大雨里疾走、我在大雨里狂奔,身边飞驰而过的汽车无数次带起地上的积水,我的衣服上很快布满肮脏的泥痕,我不理,只是快步地向前奔跑;一个身披雨衣踩着单车的人低着头从我身边越过,车把手划在我的手腕上,殷红的血顺着伤口涌出来,立刻被雨水冲洗干净,我感觉不到痛疼,只是向前走,向前走;我的脚步倾斜,身体摇晃,可我还是坚持着,固执地向前走,向前走……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要找到车站,我要找到回去的路,我要回家,我要回到一个我熟悉的地方,我不要在这样寒冷的、陌生的、仓皇混乱的雨雾里。我要见到朵朵,我要见到志浩,我要看到他们,我想和他们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