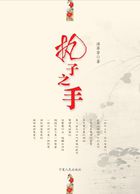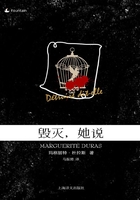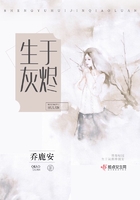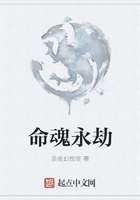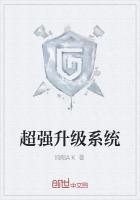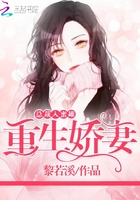咸丰十年冬,因外国侵略者侵占北京,咸丰帝避走滦阳热河行宫,朝廷上下乃有迁都之说。京官具奏者甚多,湖北、河南、山西诸省疆臣也纷纷陈奏,众口一声,以为迁都乃当时第一良策。唯曾国藩称:“有人则可秦可滦,均足自立,无人则滦失而秦亦未必得。”他根据历史事实,进一步论述道:“中兴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汉迁许都而亡,晋迁金陵而存。拓拔迁云中而兴,迁洛阳而衰。唐明皇、德宗再迁而皆振,僖宗、昭宗再迁而遂灭。宋迁临安而盛昌,金迁蔡州而沦胥。大抵有忧勤之君,贤劳之臣,迁亦可保,不迁亦可保;无其君,无其臣,迁亦可危,不迁亦可危。鄙人阅历世变,但觉除得人之外,无一事可恃也。”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深交。任京官时,又广交友朋,以文会友,他除了师事理学名家唐镜海、倭艮峰外,另外如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了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动来与曾国藩结交。他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事业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曾国藩交游的目的很明确:“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他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他的事业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李鸿章做《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他“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昴。终奠九土,踣此狂丑”。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清史稿》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问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存在久电”。
成功语录:治人不基,不外乎刚柔兼济、软硬兼施。
鼎之轻重,未可问焉
人生在世,不要吾从哪里来,更不要寻吾到那里去,一切都会随时间消逝在历史的足迹下,成于此,败亦于此。
湘军成立之初,原系保卫地方性质,并无出境作战计划。后以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清廷不得已,乃命曾国藩率军援鄂,可是曾国藩以准备未妥,迟迟不出兵,清廷多少有一点不满之意,及湘军克复武汉,便有人向咸丰进言,去了一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因此清廷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时,曾国藩照例的辞呈尚未寄出,而清廷便已收回成命,另易他人。这不但使曾国藩面子难堪,且使湘军将领,无不愤慨,湘军造反的原因,实基于此。
曾国藩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军以后,原来咸丰帝临死的遗言,克复金陵者王,可是事实上,仅仅给以一个一等侯。曾国藩幼女曾纪芬曾言,家乡一闻此讯,多说侯爵太细。太细即太小之意,不满之辞,已露言表。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几乎是过云历代战争结束后的必有现象。太平军完了,便有许多御用官吏,便乘机制造罪状,打击湘军,而且想将湘军将领,一网打尽,这样毒辣阴谋,编修蔡祺奏劾曾国藩、曾国荃破坏纪纲;监察御史朱镇,奏劾湘军纪律废弛,并列举湘军将领罪状。其他如胜保、穆缉阿之流,更是散布谣言,无的放矢。清廷乃下诏命,要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这便是湘军造反运动的近因。
打了十多年烂仗,花了许多老百姓的钱,却要办理军费报销,这不是十二道金牌是什么?这一诏命一到,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四人,便秘密活动要拥戴曾国藩出面,反抗清廷。
当曾国藩在南京城破,太平天国覆亡,进入残破不堪的石头城后,全城余烬未息,颓垣败瓦,满目凄怆,不忍卒睹。有一晚上,大约十一点钟,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进入卧室小休,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忽然来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国藩报告,曾国藩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中军复以未见九帅,曾国藩即传令召曾国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藩听见曾国荃已到,才整装步入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坐,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巡弁取纸笔,巡弁进以簿书纸,曾国藩命换大红硾笺,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掷笔起,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莫之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为两行上下联,联说: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读联语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凛然,最后则是皇然。众将围在曾国荃之后,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表情不一。曾国荃于是用黯然的声调对大家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千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一段笔记显示南京城破后的湘军确曾有过拥立曾国藩做皇帝的一幕,可是在专制王朝,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九族的,所以在笔记上看不见“拥立”字样,而将领们也不敢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的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相对之间,都不点破。
曾国荃和湘军攻灭太平天国,再造清朝,立下了盖世大功,以当时湘军士气之盛,战功之伟,如果拥立曾国藩,是用不着费气力的;而曾国藩以十四字联语,把他们的打算消弭于无形。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力的如王闿运、郭松焘、李次清皆是。当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欲以盛筵相贺,曾国藩不许,只准各贺一联,李次清第一个撰成,有“王侯无种,帝王有真”句,曾国藩见到立即撕毁,并斥责了李次清。曾国藩死后,李曾哭以诗有“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句。
李联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符曾意,其后张裕钊来安庆,以一联呈曾,联说:
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
曾国藩一见此联,击节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为不工整,曾国藩勃然曰;“你们只知拉我上草窠树,(是句湖南土话,湘人俗称荆棘为草窠树)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干。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盖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
至于王闿运的劝进更是大家所熟知的,也有载于《投笔漫谈》。据说王谒曾,说个不停,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曾国藩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几上有所点画,不多时,曾起立更衣,王闿运站起来窃视几上曾写的什么,只见依稀尽是一个“妄”字。
后来王不得意于曾幕,有“我惭携短剑,只为看山来”句。王在衡阳及成都讲学时,则对学生大骂:“曾大(指曾国藩)不受抬举。”王晚年撰自挽联有:“纵横计不受,空留高咏满江山”句,不无耿耿。
还有传说,曾国藩寿诞,胡林翼曾送曾国藩一联,联说:
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胡亲送此联给曾,曾对胡联大为赞赏,胡告别后遗一小条在几上,赫然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见到这一字条,惶恐无言,悄悄的撕成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左宗棠写好这一联稿专差送给胡林翼,请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易,加封转曾。曾阅后乃将下联的“似”字用成气候硃笔改为“未”字,原封送还胡。胡见到曾的修改,、乃在笺末大批八个字曰:“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曾国藩改了左宗棠的下联一个字,其含意就完全变了,因为“鼎之轻重,未可问焉”!宜其胡林翼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
曾国藩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的时候力克安庆,遣人往迎曾国藩东下。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船上众人眼见彭玉麟的一名心腹差弁,送一封封口严密的信上船来,曾国藩把信拿到后舱去看。但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文说: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候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内巡抚官倪人垲,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又亲眼目睹曾国藩面色立变,他急得不遑择言的说;
“不成语,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
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肚里。
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便点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心目之中,决无“华夏之防”的种族观念,他所有的只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君,天也”偏狭国家思想,他一味“效劳朝廷,忠君报清”,不过是为了争取异族皇帝赐给他高官厚爵,地位和利益而已。
曾国藩以中国道统为任,从容乎疆场之上,沉潜于礼义之中,他自练团勇起,到平定太平天国为止,前后十余年,虽然打过不少败仗,遇到不少拂逆,可是他从没有杀过一员将领,最重的处罚不过是劾免。当他在世时,湘军的纪律和统帅的尊严都能维持。在湘军和太平军转战期间,曾经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有时十决十荡,有时旅进旅退,有时被攻而溃,有时被围而破,可是他的大将没有一员投降于对方。以一支地方团勇起家,军储又半由自给,能树立这种风气,使将帅士卒视曾国藩为慈母、为严父,真是难能而可贵。
不过,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曾国藩“自立为帝”就真的能入主北京,一统中华吗?这很难说,最起码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曾国藩何等人物,他怎么会冒诛九族之险而舍弃己到手的功业呢?所以我们要说曾国藩就是曾国藩,他绝对成不了宋太祖,也不敢搞“陈桥兵变”。
成功语录: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家书传世,历久不衰
在曾国藩所有的著作中,以其家书最为著名,流传最广。自清末出版以后,传之于乡村城市。旧社会,识字之家,多备有一册,教育子弟奋发上进,有所作为。
近年来,正如重新认识和评价曾国藩一样,《曾国藩家书》又得到学者们和平民百姓的青睐,各种版本的出版物行销于市场,读曾国藩之书一时蔚然成风。
那么,《曾国藩家书》的魅力何在呢?
曾国藩一生成就,可以说都是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化下,能以儒家“孝悌、忠信”作为生平准则为人处世而获得的。
“孝悌忠信”这种生活原则,虽曾被历代帝王用来维护过他们的封建统治,但这个原则能有这样巨大的作用,不能说不是它在实际上能维护人类的尊严,是一种人们共同的需要,也是人类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以协调发展必不可少的秩序。所以这一原则,对于建立起一个人人得以和谐相处的生活环境,也是很有价值的。不应简介地把它看作就是封建性质的东西对它全盘否定。
曾国藩的家书,是其毕业奉行“孝悌忠信”的生活最为可信的实录。在他这数百封家信中,他以亲切的口吻、流畅的文笔、真实地表达了他所有的成功、失败、得意、困惑的感情。
人们可以从这些信中,具体地看到生活现实与理性教条的碰撞,在一身居高位者心中激起的千般情绪;可以看到他怎样在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坚持“孝悌忠信”,而使他内对长辈、平辈、晚辈,外对皇帝、上司、同级、下级都通权达变获得成功。他的这些故事,不仅可以使我们读起来会感到生动有趣,不比读一部小说逊色,更有价值的是,在这些故事中包含的许多即使在今天的生活中,也很有意义的教训和经验。有人说,它是一部协调人际关系的指南,一部正直、严肃地为人处世的教科书。
应该说,其最大的魅力在于诚恳。曾国藩一生以“诚”相标榜,在家书中,对待亲人,它的字里行间,更有一种真诚的热情在流露,其中,不夹杂着世上常见的虚伪和造作成份,这是最能感人的,在家书中有许多篇是曾国藩教训其弟弟的,之所以不引起对方的反感,恐怕就在于这个诚字上。
我们可以看这祥一个小例子:
曾国藩在京时,他还负起教育诸弟的责任。他叫几位弟弟寄文到京,改阅后再寄回去。曾国荃本来随他在京读书的,后来曾国荃回去了,他写信给他的几位阿弟说:
九弟在京年半,余散懒不努力。九弟去后余乃稍能立志,盖余实负九弟矣,余尝语岱云曰:“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九弟之无长进,是我之大不孝也!”惟愿诸弟发奋立志,念念有恒,以补我之不孝之罪,幸甚!幸甚!(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致诸弟书)
这样的兄长,兄弟能不受感动?人读此家书能不感动?
《曾国藩家书》中,内容极为广泛,大到经邦纬国,进德为官,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活,人际琐事,事无巨细,无不涉及。尽管许多信又长又啰嗦,平均每封信在一千字至三千字左右,但我们今日读起来仍不禁有亲切之感,也恐怕是为信中的诚恳所打动。
在曾国藩的家书中,充分反映了传统儒学的为人立世之道,表露了曾国藩在人品、精神上令人夺目的一面,这也是人们喜欢曾氏家书的原因之一。下面我们把这些内容编录,并加以解释,读者自可含英咀华。
在家书中,曾国藩坦露了他的立志修身志向和为人处世的法则。
他以“君子庄敬日强”自勉。为此他勤于自省,在寄其父亲的信中曾说:
曾国藩曾寄父一函说:
男从前于过失每自忽略。自十月以来,念念改过,虽小必惩。(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家书)
又寄弟一函说: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同上)
曾国藩不但注意反省,兼重慎独,我们于其日课中可以知之。其日课四条中,一为“慎独则心安,”其言说: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能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家训》卷下)
至于待人之道,曾国藩因人而异。曾国藩对于家庭端重“孝弟”二字。他曾致弟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