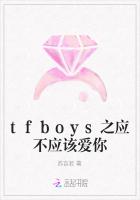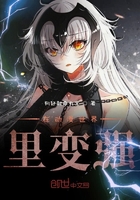人生由立志开始。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是追求人生目标的的决心和信念,它为曾国藩的一生提供了精神动力,其声名事业,皆求一“志”开始。
曾国藩在二十岁以前,虽然读书为文,但无志向,到二十一岁那年,才立志学圣贤,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他号“涤生”。这涤生二字,便是在这时候改的。改后他痛下决心道:涤是涤去旧染的污秽,正如袁了凡所说的“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他又给自己写了一条座右铭道: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曾国藩常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浴”苦志学业,到了进京中进士以后,与唐镜海、倭艮峰等大儒交往,他的思想更进了一步,此时他要穷理达德,做圣贤的功夫,他的事业则在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而以匡时救世为事事。
又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址,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温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为使志向得以实现,曾国藩以存诚自养。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而最基本的则在于诚意、正心,曾国藩以此自励,并以勉励僚属子弟。
曾国藩以儒家思想作为他的立身态度,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致诸弟书说: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辞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在这番话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功名事业之外,极其重视进德修业之事,以为如此方能无忝其所生。这还是他在初为翰林时的思想。及至晚年,功业已成,身名俱泰,他所时切在念的仍是他自己的德行与学问。如同治八年八日日记说: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剪除改徒之时,忧愧曷已!
念生平所做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
曾国藩的道德文章,即使不能说是千古以来所罕有,至少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人物。尤其是在道光咸丰以后,世风日下,人心,日伦,整个国家社会都有分崩离析之危险的时候,竟然能有曾国藩这样一个节行文章俱属卓荦不凡的人出来挽救清政府,转移社会风气,实在可说是清政府的福分,曾国藩如此的过份谦抑自咎,适足以使人觉得他的成就太不平凡。曾国藩《湘乡昭忠祠记》中的一段话,颇可以看出他自己的抱负。文说: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还游之远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他在这一段文字中所提出的“诚”“拙”二字,正是他自己所用来鼓舞人心与转移风气的特性。薛福成所撰《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亦曾说到这点,而且特别以强调,说: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故太常寺卿唐鉴,故道员何桂珍,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动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
由以上所述可知,曾国藩能在天下动荡之时挺身而出建立伟业的原因了。
成功语录: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向收获,只向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