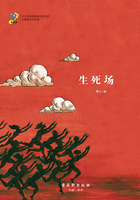一、国民政府的成立
1925年7月1日,随着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战斗的胜利,按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正式成立国民政府。
7月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蒋介石、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为委员。蒋介石凭借着战功在军事委员会中占据首要位置,因为军委会主席由国府主席汪精卫兼任,首席委员由外交部长胡汉民兼任,二人既不懂军事又不管军事。而且身为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的谭延闿和曾参与指挥军事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8月20日被刺牺牲)又排在后面,所以名列第三的蒋介石成为事实上的首席委员,这说明他在军事上的地位已超越长期主管军事工作的谭延闿、许崇智、廖仲恺、朱培德、程潜、李烈钧等人,成为国民党事实上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6月15日的决议,8月26日,各建****和党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对其作了具体编制:
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党代表原是此时已被刺身亡的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第一团团长和党代表是刘峙、贺衷寒,第二团团长和党代表是沈应时、金佛庄,第三团团长和党代表是钱大钧、包惠僧;第二师师长是王懋功,第四团团长和党代表是刘尧宸、徐坚,第五团团长和党代表是蒋鼎文、严奉仪,第六团团长是陈继承;第三师师长是谭曙卿,第七团团长和党代表是谭曙卿和蒋先云,第八团团长和党代表是徐庭瑶、张际春,第九团团长和党代表是卫立煌、王逸常。
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副军长鲁涤平,党代表汪精卫,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四师师长张辉瓒,第五师师长谭道源,第六师师长戴岳,教导师师长陈嘉祐。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克靖。第七师师长王钧,第八师师长朱世贵,
第九师师长朱培德兼。
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朗如。第十五师师长李群,第十六师师长练炳章。
1926年初将程潜的部队建国攻鄂军改编为第六军。
第六军:军长程潜,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林伯渠)。第十七师师长邓彦华,第十八师师长胡谦,第十九师师长杨源浚。
国民政府成立,使汪精卫成为了广州政坛的头号人物,然而他的上台并未使局势平稳,反而出现了新的一轮权力之争。
孙中山逝世之后,只留下了政治遗嘱,并未指定接班人。以他的政治常识,应该知道这样做的巨大危害,尤其是在中国。不知道是他老人家故意为之,还是认为身后的几位国民党骨干都不足以领袖群伦,让他们听天由命去吧。当时的大元帅府内外谁也推不出一个让各方能接受的继承人来。于是各方政治势力都对这个位子产生了角逐的想法。包括云南的唐继尧,也想入非非。
当时最有希望的是代帅胡汉民和汪精卫。而胡的资历还略高于汪。胡汉民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同盟会、国民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他不仅在党内阅历最深,资格最老,而且一向为孙中山所倚重。民国初年就做过广东都督,后来曾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政治会议主席、大元帅府秘书长、广东省长等等。在孙中山北上后一直担任代理大元帅,这个职务可以理解为孙中山之后的第二把手。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元老,中央委员和右派分子都很拥护胡汉民,在他们心目中胡是孙中山想当然的接班人。
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觉得由自己来继承孙中山的地位是顺理成章的事。为了夺取最高领导权,他积极谋求军界的支持,3月31日,他领衔军政界首脑杨希闵、谭延闿、许崇智、刘震寰等发出宣言:在国民会议未实现,中华民国合法政府未成立以前,所有一切制度实施,汉民等敬谨赓续孙大元帅成规,戮力同心,并期发扬光大,以完成国民革命之工作。
但是胡汉民的弱点是很明显的。他虽然参加革命最早,追随孙中山时间最长,然而在许多重要政策问题上却与孙中山存在重大分歧。首先对联俄联共的政策表示怀疑,对改组国民党很不热心。这在当时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使得苏联顾问们和****方面对他并不支持,这一方面当时在广东力量很大。第二就是胡汉民身边的人极其庸碌无能,口碑很差,以致影响人们对他的好感。最关键的还有一点,胡汉民是文官出身,与军界关系很疏远,尤其和当时广州的实力派人物许崇智关系很僵,甚至对立。他与其他将领也少有来往,对新兴的军事力量——黄埔军校更是漠不关心,与蒋介石、廖仲恺等貌合神离。他想不到当时一个小小的蒋校长能兴起多大的风浪。因此上,胡汉民既没有军队的支持,又缺乏新兴力量的拥护,在当时的主流派别中影响甚微,大家对代帅不过敬而远之。
至于汪精卫,他与胡汉民一起工作了二十多年,私交甚厚,从同盟会时期开始,就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国民党改组后的“一大”前后,两个人仍是很团结的。当时少数右派分子反对国共合作,极力散布国民党将被****的言论。胡、汪曾经联名通电,驳斥他们。
1924年7月,根据孙中山建议,国民党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孙中山自任主席,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伍朝枢、邵元冲为委员,是国民党最高政治指导机关,是沟通党与政府的桥梁,以实现党对政府的领导。在这个委员会中,胡汪的排名是第一第二的。
1924年底,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后先生病情加重,汪一直守护在左右,并随时向各方通报情况,甚至起草了先生的政治遗嘱。这期间,胡汪二人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1925年1月28日,孙中山授权汪精卫发布命令,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移往北京,由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于右任、陈友仁、李大钊、邵元冲为委员,处理一切政务。胡汉民被排除在外。从此汪精卫的党内地位开始超过胡汉民。
汪精卫思想比较激进,以左派面目出现,与苏联顾问,****人士关系密切,赢得了不少实力派人物的拥护。
廖仲恺虽然比汪、胡资历略低,但是孙中山最信赖的人物,担任许多党政军要职。
至于蒋介石当时的地位还不足以同以上三位相提并论,但是他手握军权,又得到孙中山的格外信任,实力也很可观。
但是当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众望所归成为了主席,胡汉民仅仅是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这又不免让很多人愤愤不平了。加上一些其他的因素,广州政局再一次出现跌宕起伏。
在7月底的数日内,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蒋介石几遭行刺,好在大难不死。后来查明主使者是商团头子陈伯廉。而廖仲恺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1925年8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被刺杀于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外。
“廖案”发生后,国民党广州当局在鲍罗廷的参与、支持下,决定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廖案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以应付非常之局势”。查办“廖案”,成为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被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侦查、审讯期间,波澜起伏,牵连面极广,并扯进了大批上层人物。事态正如粤语所谓崛(秃)尾龙拜山——搅风搅雨。广州陷入了政局更加动荡、社会更为不安的局面。
案发后的第三天,粤军第三军长李福林带来“人证”,向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举报胡毅生(胡汉民的堂弟)、魏邦平、朱卓文、林直勉的问题。其中说:8月初在文华堂,“曾亲眼看见并亲耳听见”朱卓文与林直勉坐在一起,“口口声声说非杀廖仲恺不可”。“廖案”特委于是下令拘捕胡毅生、林直勉、魏邦平等。在铁路工人李甫的指引下,由周恩来率黄埔军校学生逮捕了林直勉。而胡毅生、魏邦平等脱逃。
关于李福林举报的内容,在汪精卫等人当时的谈话、文章中,仅公开了上述朱卓文、林直勉等人扬言杀廖的部分,而其中还有些内容,未曾公布过。据当时任许崇智卫士连连长(稍后为宪兵营营长)的林祥所述,当年7月间,粤军将领李福林、魏邦平(粤军总部高等顾问)、梁鸿楷(粤军第一军军长)、梁士锋(旅长)、张国桢(第五师师长)、杨锦龙(旅长)等,曾在李福林的家乡——广州珠江南岸的大塘村,召开“反共倾覆政府的会议”,内容是:“拟首先推翻许崇智、蒋介石,重组政府”。廖仲恺被谋杀后,李福林害怕东窗事发,乃“出面自首”,告发秘密,将“会议”的情形及与会人员,连锅端出。因是之故,当“廖案”特委下令拘捕胡毅生、朱卓文、魏邦平、林直勉时,蒋介石同时即提出要“剪除谋叛军队”,并且在“未曾商准许总司令”的情况下,首先派其团长沈应时逮捕了粤军第五师师长张国桢,同时抓获了旅长杨锦龙。
李福林的检举,因牵进了许崇智部粤军的许多将领,使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务主席、并且是“廖案”特别委员会成员的许崇智,深深陷入了困境之中。许崇智起初不但不同意逮捕张国桢,而且在决定逮捕梁鸿楷等人的时候,明确表示“拒绝执行”,因而,只得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出面做工作。鲍罗廷1926年2月在北京向苏联布勃诺夫使团作报告时,详谈“廖案”前后情况,其中说他“花了许多天时间,设法迫使许崇智去同梁鸿楷作斗争”。鲍的手法是向许挑明“胡汉民与廖仲恺谋杀案有关这一事实”,“所以决定要把他(胡)赶出一切机关。人们甚至谈到要逮捕胡汉民”。他接着说“我们这样处理胡汉民,立即对许崇智起了作用,所以他表示同意逮捕梁鸿楷”。正是在鲍的“迫使”之下,许崇智于8月25日以开会为由,召梁鸿楷、梁士锋、郑润琦(第三师师长)、招桂章(总部舰务处长)至粤军总部,当即拘捕梁鸿楷、梁士锋、招桂章,而放出郑润琦。接着,蒋介石出动兵力,分别解散了梁鸿楷、杨锦龙、梁士锋在广州及西江的各军队。
梁鸿楷、张国桢等人被捕之后,汪精卫、蒋介石乃指派曾任大本营军需总局局长、潮梅军军长的罗翼群,会同欧阳格、周恩来,共同组成“军事法庭”,对梁鸿楷等人进行审判。从1925年4月起兼任黄埔军校军法处长的周恩来,被指定为“审判长”。蒋介石当时对罗翼群说:“他们(梁鸿楷等)个个脑满肠肥,捞钱不少,全都是你的熟人。我拟请你去和他们家属商量,共同筹足一百万元报效给政府,作为东征的开拔费,如能办到,我便从宽处理他们。”蒋并且说这是“照上年审判程天斗的办法”来处理的。后来,蒋介石又说不要张国桢、梁士锋、杨锦龙的“报效费”。结果,张国桢、梁士锋、杨锦龙三人被枪决;而梁鸿楷等人在“报效”了一笔金额后,获得了释放。
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胡汉民在“廖案”发生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涉嫌人物。案发之日,他已被排除在“廖案”三人特委之外。在文华堂攻击、谩骂过廖仲恺的胡毅生,很快被锁定为重要追查目标,这条线索随即追到他的堂兄胡汉民头上。胡汉民于是更被牵进案中,被怀疑为杀廖主使者。汪精卫妻陈璧君回忆说:“全市哗然,谓杀廖君者,必为胡汉民。”在“廖案”的涉嫌者中,最尖端的人物,就是胡氏兄弟。8月25日,当蒋介石派军队搜捕胡毅生时,士兵包围并搜查了胡汉民的住宅。胡描述说:“房门外枪声大作”,大批人“冲到房中”。胡汉民乃被移居于黄埔军校,等于软禁。
当时,胡汉民对自己所蒙受的怀疑,曾经断然予以否认,说“此案毫不知情”,并且说这是“以‘莫须有’三个字,置我予死地”。当胡居留黄埔,四受责难时,戴季陶对传媒发表谈话,说胡汉民是个很平和之人,委婉提出对胡汉民、胡毅生兄弟应区别对待,而“决不能相提并论”。9月1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常会上说:“胡毅生虽与汉民同志为兄弟,然胡毅生此次谋杀廖仲恺同志举动,汉民同志事前毫不知情,何能代为负责?”
然而,汪一边说对胡氏兄弟要“区别对待”,另一面却以“廖案”特委的名义,决定“胡汉民出洋”。鲍罗廷的态度更是“必须让他(胡)离开”。当胡去国之际,汪精卫对记者发表了谈话。
记者问:“君与汉民同志同患难共死生二十余年,近日得毋稍有芥蒂乎?”汪说:“君曾读《孟子》否?‘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瞽瞍且然,何况于象?吾辈书呆,即未闻近世革命党人律身行己之义,何至不读《孟子》。若因此有所芥蒂于心,死何面目见总理乎?”
汪实际上是趁机将胡“请”出广东,送往万里之外的俄国。与此同时,汪又以参加国民外交代表团的名义,将林森、邹鲁等人派赴北京。邹鲁当时被认为是胡派得力干部之一,在讨伐杨刘及成立国民政府等问题上,与汪、廖、许、蒋持有不同的意见,并指与“廖案”沾边。汪显然也是借查案之机,将不同政见者“请”出广东。
那么,胡汉民兄弟与“廖案”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
胡毅生之涉嫌“廖案”,是因为他有反廖言论。作为自我辩解,胡毅生、林直勉等都自陈公开骂廖不等于阴谋杀廖。胡毅生逃走后致书汪精卫,辩称其反廖言论是在公开场合说的,“然一面公然骂廖,一面秘密杀廖,同人虽愚,宁至于此!”胡并斥责汪是“据耳食之谈,以为信谳,枉法弄权”。胡毅生还发表《告内外同志书》,申明他与杀廖没有关系。
案发之初,胡毅生受社会舆论、特别是受查案侦探“重视”的程度,不在朱卓文之下。但到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时,他却似乎已经淡出了办案者的视线。陈公博在那次大会上曾应代表要求,以“廖案”特别法庭检察委员的身份,作“关于廖案检察经过”的报告,陈对胡毅生的定性,仅仅是“无聊政客”四个字。他当时公布了一份“廖案人犯”名单,无论是在“主要的”还是“间接关系”的部分,都剔除了胡毅生之名。稍后,“廖案”检察委员会《关于廖案之公判请求书》和陈公博在特别法庭上的“论告”词,也都没有提到胡毅生。那么,是不是因为胡毅生这时尚未捕获归案,仍然潜逃在外,才不便于点他的名呢?看来不是的。因为同样是潜逃在外的朱卓文,就不但屡被当局提及,而且被指为“主谋正凶”,还受到悬赏通缉。国民党“二大”是查办“廖案”呼声最高的时候,胡毅生在这种时候,以及在稍后特别法庭的审讯中,悄然消失于办案者的视线之外,这应当不是偶然的。
前面说过,“廖案”发生将近一个月(9月15日)时,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常会上,公开为胡汉民辩解,说他对此案“毫不知情”,“何能代为负责”?为胡将来一旦重出作了保留。到国民党二大时,不过两三个月时间,因西山会议派的出现,胡的政治地位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一位因涉嫌“廖案”而放逐海外者,变成了汪、蒋的“统战对象”。在缺席情况下,胡在国民党“二大”高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并选进中央常委。这是因为汪、蒋需要争取胡汉民共同对付他们当时最主要的**********──西山会议派的缘故。这一点,应当就是胡毅生之所以被“廖案”特别法庭的检察官、审判官“忽略”了的原因所在。在“廖案”中,胡氏兄弟这时似乎已经被解脱矣。从此之后,不仅胡汉民在国民党中的“领袖”地位没有改变,而且事过境迁,胡毅生也当上了国民政府委员、“国大”代表、“总统府”顾问,抗战时还被蒋介石安排到国民党党史编委会工作。1957年,胡毅生病逝于台北,于右任写的挽联云:“离乱悲元老,存亡忆故人”。看起来,胡氏兄弟涉嫌“廖案”的那笔历史旧账,在国民党人那里,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然而,胡氏兄弟虽然因为上述“政治需要”而脱身,但历史的谜团,不等于就此烟消云散。1926年2月,鲍罗廷在北京向苏联使团谈“廖案”时说到:当有人问胡汉民“是否该干掉廖仲恺”时,“他(胡)的回答是沉默不语”。陈公博1939年所撰《苦笑录》一书,提到“廖案”发生前,一名叫李天德的铁血团成员问胡汉民:“外间有人说先生(胡汉民)要杀廖仲恺,是不是?”当时“胡先生不答”。身为“廖案”检察官的陈公博,在当年“廖案”特别法庭上虽然“忽略”了胡氏兄弟,而事过之后,他所爆出的这条材料,却与鲍罗廷当年对苏联使团所述,何其相似乃尔!鲍、陈均据而认为胡汉民是杀廖的“默许”者。陈公博还明白说:“自然不是胡先生当面指使凶手,但团体里酝酿暗杀廖先生,而胡先生不加制止,这是事实。”鲍、陈所言,虽然仍未能进一步落实,但事关重大,焉能不了了之?故胡氏兄弟与“廖案”的关系,虽能遮掩于一时,却未能漂白于天下。提到“廖案”,人们总还会提到他们兄弟俩。他们的“历史问题”,还在那里挂着。
李福林举报的“大塘会议”,从实际的情况分析,可能是粤军军官们的一次聚谈。当时李福林、魏邦平、梁鸿楷、张国桢等人,对汪、廖、许、蒋歼灭杨刘、改组政府,内心存有不满。当廖仲恺、蒋介石派黄埔军校学生搜查赌馆时,又与李福林的“福军”发生过冲突,双方拔枪相向,关系十分紧张。李福林担心他会与杨刘一样,遭到歼灭的命运。可以想象,这帮人当时的谈话,可能很“出格”,借助酒兴,什么“反叛”、“反骨”的话,都会随口而出。他们之被整肃,看起来乃是“咎由自取”。
那么,梁鸿楷这几个人的情况怎么样呢?
毛思诚撰蒋介石“年谱”初稿,1925年8月25日条下,有“发见港英谋覆政府,以梁鸿楷为总司令,魏邦平为省长之大阴谋”一语。这是蒋对魏、梁等人定下的基本调子。此时汪、蒋的言谈和文章,说到魏邦平、梁鸿楷,多是这个说法。然而,到了国民党“二大”时,陈公博那篇“廖案检察经过报告”,仅仅将魏邦平和梁鸿楷定性为“失意军人”,不但未将他们列入“廖案”人犯名单,而且连“勾结港英”,“谋覆政府”这八个字,也没再提及。这其中的奥妙,应当就是前文提到的梁鸿楷等在“报效”了一笔金钱之后,已经获得了释放。据罗翼群说,梁鸿楷等五人“合共献出报效费三十三万元”;而林祥则从梁鸿楷的弟弟梁振楷的口中,得知“一共缴款十六万元”。数目无论多少,梁鸿楷等人在缴纳金钱后而获得了释放,这是实有其事的。故《申报》1925年9月24日的国内专电所谓:“在黄埔监守梁鸿楷之学生军一连,受莫雄、郑润琦运动,巧私释放。……黄埔之杨锦龙、谭启秀、林直勉、梁士锋,闻亦与梁鸿楷同时逃脱……”这一报道是不确实的。同样,《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2日刊出的“梁鸿楷终身监禁”的消息,也是靠不住的。梁鸿楷被释放后,还与李福林合办防务经费(番摊),获得了厚利。抗日战争时梁鸿楷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广东省政府顾问,1956年死于台湾。上述“报效”内幕,既然并非出于虚构,那么汪、蒋加在梁鸿楷等人头上涉嫌“廖案”与“推翻政府”的大帽子可信程度如何,就应当打个折扣,打个问号了。
在梁鸿楷一案中被处死的张国桢,广东南海人,早年与蒋介石同在援闽粤军总部任参谋,与蒋积有怨恨。叶少华(曾任第四军军法处处长)所撰《有关张国桢的若干情况》一文说:“蒋介石对张国桢,早在‘廖案’发生的两年前,已萌杀机了。”案发之时,张国桢自辩他与“廖案”没有关连,曾经说“廖死关我屁事”。当有人劝他逃走时,他又说:“戆居,我都使走(别犯傻,难道连我也需逃走)?”蒋介石不经许崇智的同意,擅自逮捕并置张国桢于死地,这其中是否另有隐情?当然是个谜团。又有资料说:“被拘留于粤军总部的杨锦龙、梁士锋,许崇智下台时,总部的人忘记将他们释放,蒋介石知道,又忙派人将他们两人杀了。”他们的死,同样是不明不白的。
然而,梁鸿楷、张国桢等被捕后,许崇智所遇到的麻烦,并未成为过去。9月5日,许崇智奉命担任“财政监督”,不过几天(即9月9日)时间,蒋介石即向汪精卫告状,说“许崇智不顾大局,把持财政,心欲限制本军的发展,可胜慨然”。很显然,由汪、许、蒋三人组成的“廖案”特委,这时只剩下了汪、蒋二人。自从8月25日之后,许崇智实际上已经被排出了权力中心,成为边缘人物,并始终未能走出他所陷身的困谷。
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是蒋介石于9月19日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以“解决反革命各军”的名堂,出动军队,宣布广州全市戒严。蒋派出的军队包围了许崇智的住宅,“四面放枪”,实行武力威逼。夜10时,蒋介石给许崇智送去了一封长信,以劝许“不如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的口气,令其立即去职。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将这封信解读为:“盖当时公(蒋)欲出师长江,以图本党之发展,而许不赞其行故也。”似乎是因为许不赞成“出师长江”,才遭致蒋的不满,其实不是这回事。《蒋介石年谱初稿》附有此信全文,其措辞强硬,咄咄逼人:“廖案发生,阴谋暴露,而害党叛国者,均为吾兄所部,而吾兄不引咎自责,幡然悔悟,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竟酿成此巨变惨剧,岂不可痛。”斥责许崇智“空谈革命,口是行非,信用已失,名誉扫地”。全文2000多字,字字是逼许下台之利刃。
许崇智当时打电话给汪精卫,询以何故?汪即回函,大意谓:“余虽一书生,但敢信非威力所能屈。余决不因在卫戍司令威力之下,便妄赞同蒋氏此项措施。实为认定此事,非如此解决不可。”又谓:“余敢信介石对公事虽毫不假借,不讲感情,但决非余不讲感情之人。为先生计,为大局计,亦莫善于暂行赴沪,一任介石将此一切难题,及感情上不能解决之难题解决后,即请先生回。”汪精卫在对媒体发表的谈话中,明确支持了蒋介石,说党内、外“若因此事有不谅于介石者,余愿分其谤也”。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许崇智只好缷职,在陈铭枢的“护送”之下,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粤军第四师师长许济,亦被令缷职随行。
9月19日夜,蒋介石又逮捕了广东财政厅长李基鸿和军需局长关道。其理由是“因李、关侵蚀国币,接济反革命军也”。其实,李基鸿是廖仲恺死后才担任省财政厅长的,上任不到一个月。
9月20日,蒋介石又派出军队,到东莞的虎门、莞城、石龙一带,分别包围、追缴粤军第三师师长郑润琦、第三旅旅长莫雄所部的枪械。郑、莫既未沾“廖案”的边,也未参加什么“大塘会议”,当8月25日许崇智诱捕梁鸿楷等时,郑曾应召至总部,问明情况后已经放出。而莫雄还被许派赴广九路,执行解散粤军林树巍部的任务。现在,郑、莫所部却被戴上了一顶“反革命军队”的帽子,被收拾得一干二净,郑、莫狼狈而逃。如果说,胡汉民离境还蒙上一层“客气”的外衣,还给他开过“欢送会”的话,那么许崇智及郑、莫等人的问题,则完全是用枪杆子解决的。
《许济自传》写道:当其时有人曾问于许崇智,何以让蒋如此作为呢?许崇智回答说:“孙先生去世不久,我若与之(蒋)争论,不知者,意我为党见不合,及以我为权力而争。我桑梓十余年来,被新旧军阀、官僚祸害,人民精疲力尽,谁能分别?惟有看他行践如何。革命事业正与不正,自有公论,那时人人得而诛之,讨伐岂能少我一分子?”许崇智并嘱许济一同离粤。许济写到这里,对蒋介石使用了“恶毒阴险,混淆黑白,甚于袁氏陈逆等”的字句,可见其心中的不平。
总而言之,许崇智的“跟斗”,是因李福林的检举而栽倒的,而李端出的东西到底有几斤几两?却是个哑谜。许崇智被罢官卸职,其部下被驱逐、被逮捕、被枪毙,其部队被并吞。许崇智的这个“跟斗”,栽得不可谓不重矣。故就实际而言,在“廖案”查办过程中,许崇智是受牵连最广,受打击最重的一位。
一时间蒋介石风头劲猛,广州政坛甚至谈蒋色变。借着这股猛劲,蒋介石居然又拘禁了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在广东北部出兵驱逐了熊部川军。
熊克武,字锦帆,四川井研人,生于1881年,1905年加入同盟会,受命为四川同盟会主盟人,1911年参加黄花岗起义。1915年到云南参加护国斗争,1923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初,熊部川军被刘湘、杨森逐出川境,退至贵州。9月,熊派但懋辛、石青阳到广东面见孙中山,表示愿与孙中山一致行动,共同出兵北伐。11月间,当孙中山派谭延闿出兵江西时,熊部川军也由黔东开入湘西,以期进攻鄂西,与广东“北伐”军会师武汉。然而,熊部入湘,却引起湘军赵恒惕的忌恨。1925年1月,谭延闿在江西受挫,湘军东边警戒解除,赵恒惕于是准备驱熊。3月底,赵授意湖南省议会通过驱逐川军出境案。4月,赵军向湘西进攻,以破竹之势占领了桃源、常德、澧州、辰州等地。熊克武不能立足湘西,又无法返回四川,只好率领所部第一、二军,由湖南进入广东。7月底,熊军离开湘西,跋涉千里,经广西龙胜、兴安、全县、贺县、桂岭等地,于8月底9月初到达粤北连山、连县、阳山一带,与谭延闿部湘军会合,熊的司令部驻扎连县。
国民政府派湘军师长谭道源,携现款2万元,军服1万套及苏联顾问团所赠医药费1万元,到连县慰劳川军。谭向川军表示:政府一定补充川军的装备,按实际人数接济军饷,并决定划连山、连县、阳山、乳源四县,给川军驻防。谭并希望川军能出兵,讨伐陈炯明。熊克武答应,川军将派7个团参加东征。
此时,蒋介石、汪精卫电邀熊克武,到广州面商军政问题。熊遂于9月19日在其部师长喻培棣等陪同下,启程南下,于24日到达广州。连日拜会汪精卫、谭延闿、鲍罗廷及其他党政军要员,并在广州市广大路设立川军总司令部驻穗办事处。
10月2日,蒋之手下捕获陈炯明派来的奸细张识万,在他的身上搜出陈炯明9月20日致熊克武的一封信。其中写到:“此次闻余致堂兄赴沪,弟适自沪返港,不能相遇,刻已电请余君回港一商。吾兄为吾党健者,久著微声,必能协力救国,望密派妥员赴港,面达机宜,同策进展。”信中提到的余致堂,即余际唐,为熊部川军军长。
此外,早在本年3月第一次东征时,在兴宁林虎司令部内,曾查获川军军长但懋辛1924年9月在广州写给林虎的一封信,信中写到:“如中山不听,则联络在粤之滇、桂、豫各客军,与中山脱离,使中山自去。盖中山已陷于绝境,仅仅汉民、汝为、仲恺,亦无济也。”蒋介石和汪精卫由是怀疑熊克武与陈炯明暗中勾结。
10月3日,蒋介石以设宴为名,诱熊至寓所,将熊克武及其军长余际唐、师长喻培棣,以及随行人员刘棱、熊晓岩、丁毂音、王子骞、吴庶咸等拘捕,蒋并派兵解散了川军驻穗办事处。接着,蒋又在熊的住所,搜出但懋辛的两封信。一封是8月30日但致熊克武信,其中说:“兹有刘君毅夫,曾充云南航空署长,其副官张君应鎏,弟于海上相晤,均为我军进止忧。刘君与魏礼堂(应是魏丽堂,即魏邦平)及竞存(即陈炯明)隐青(即林虎)诸军接头,而又不识交通若何及各军现驻地安在,故特派张君前来,交通一切。如我军欲与各军联络,请即派员随同张君前往干办一切。”另一封是8月30日但懋辛致余际唐信,内容是介绍刘毅夫同余际唐交往。蒋认为,这是熊克武通敌谋危政府的证据。熊被捕后,拒不承认有反叛之事。
10月4日,蒋介石等以国民政府名义发布“重要通令”,谓熊克武“交通敌人,谋危国民政府,罪状昭然,人证俱获,实难再得姑容。已饬广州卫戍司令,立将熊克武扣留,听候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判。”随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二次会议,决定停止熊的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开除其党籍。蒋介石还发布《告川军将士书》,派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围歼连、阳川军。
当时,第二军和第三军均驻韶州。奉令后,由北路军警备司令鲁涤平任指挥,以张辉瓒率兵三团,炮兵一营为第一路,经乐昌、星子,向连县南进;以戴岳率兵三团又一营为第二路,经龙归、阳山向连县西进;以王均率所部为第三路,由英德沿连江,向阳山、连山前进。10月上旬,革命军到达星子、阳山一线。川军军长汤子模“乞降”,鲁涤平令各路急进,包围川军于连县境内。川军有的被缴械,有的经东陂进入湖南。经过桂军白崇禧部的堵击和湘军赵恒惕的收编,熊部川军,全部陷于瓦解。
驱逐熊克武川军是发生在“廖案”之后,第二次东征之前的特殊时刻,时局紧张,国民政府难免有草木皆兵之嫌。作为主要军事领导人,蒋介石对于时局紧张之际,任何有害于国民革命的反对力量也表现了坚决予以清除的态度和举动。尽管有些过火,但这一举动终究是保证了广东全省的统一,根除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