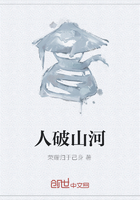文希宁猝不及防被众人盯着,只觉得若把当日寻见朱玉华尸首的整个经过说过,骆晓更是洗不脱嫌疑,可此时一众目光都落在自己身上,就连骆晓也心疑究竟是甚么原因致使一众人都把自己当杀人凶手看待。
她已经处在容不得退下去的境况中。心中想起种种有关指向骆晓的证据,心内犹豫再三忽然惊愕的盯着面前神色苍白的骆晓,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她心中产生,万一这骆晓真是杀害朱玉华,或者说是帮凶之一,自己又该如何处置。
她只害怕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因为对骆晓的感情早已包庇了他,旁边的朱老爷见文希宁神色惊愕,又是一阵催促,文希宁听他催促,不免更觉慌张,定下心想,我只是叙述我亲眼见到的,若他真是无辜的,又何必会因为这些被人误解呢?
她毕竟经历的世事不多,心思还是过于天真,须知在这种场合下,她若把这真话说出,而且还是以这番身份定会坐实骆晓凶手身份。她此时年轻天真,又唯恐自己包庇骆晓,便把当日自己与应虞怀所见所闻都如实说了出来。
众人听她嘴里说辞,说道在客栈里从小二这儿打听说朱玉华被骆晓叫去城北的破宅子,不由一阵唏嘘,皆是盯着骆晓,须知这一话便要骆晓与这朱玉华之死脱不开关系。直至说道最终他们发现奄奄一息,命不久矣的朱玉华,听众各自皆是屏住呼吸,他们或多或少知道这朱玉华死前留下甚么证据,当说起这应虞怀执着这朱玉华的手指,写下这“骆”字时,更是一片哗然。
骆晓此刻盯着文希宁,他从未如此直接的与她对视,连是出声说道:“那不是我让她过去,是那阿观要她去的,她扮作我模样的!那“骆”字定是没有,我被她们带走之前不曾见过!”
他还想全盘托出阿观报仇详情,不想此刻周围皆是指责自己声音,没任何一个人听他解释说话,就连文希宁听到他所说话语,私心也不愿去听。
他见文希宁话语说完便把头低下,差点就是喊出声音来,可心中见她不抬头,心头恍然一凉,道她也是要误解自己,自己当真如何解释也不管用。
此刻心中苦痛,不仅是因为自己被误解,更是因为陷自己于此地步的人,正是他爱恋着的文希宁。
他头颅渐渐低下,也不愿去看她,更是灰心至极,乃至连解释的想法也打消,因为周遭没人会听,文希宁恐怕更不会相信。之前见到文希宁从珠帘后出来,振奋的心情已经完全不见,他那时候将受伤手腕给众人看,妄图在爱慕女孩面前自证清白,可而今呢,陷自己于众人怀疑地步的,正是她文希宁。他本身修习寒性真气,而今因被所爱人误解,倒是自怨自艾,也不徒解释甚么。耳旁因为不久前内伤外伤疲乏缘由,嗡嗡作响。
应虞怀见骆晓已低头服罪,见周围众人如今已把他当成杀害朱玉华的真凶不疑,想起之前文希宁出来时他神色里焕然一现的神色,他只准备对他进行最后一次确认,问道:“阿观小姐去这破宅子里可是你要他去的。”骆晓听他问话,此时他心头好无生气,纵使有文希宁言语佐证自己已经成为恶人,他仍是一字一句答道:“并不是我叫她去的,我那时也被人擒住了。”
他这问题一回答,应虞怀心衬当日自己与师妹见这朱玉华迟迟不返,前去询问客栈里伙计时被告知正是他托伙计带信告诉朱玉华去破宅子里见面,此时骆晓一口回绝,他心里只当是骆晓死不认罪了。
他脑海里这时又想到另一个突破口,想起骆晓刚才叙述中所说自己手足无力,只能见着朱玉华惨遭杀害,思量他若是没有力气。怎么如今又从这他口中所谓那群真凶手上逃了出来呢?尽管这场面上骆晓已然是全无优势,他却仍不放手,要坐实他罪名还死人公道,遂又问骆晓道:“你说你当时身上伤势过重,加之长久没有进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朱小姐被别人杀害,可如今你却又逃了回来,你能告诉我其中原因么?”
骆晓此时心内交错情绪低落到极点,只得人家问一句,他答一句,有气无声地回应虞怀:“她们不晓得我打坐休息一夜,伤势稍微有所恢复了,是以逃脱了。”
这旁边众人早有直接叫嚣把骆晓直接送官府的人了,可应虞怀却仍颇有耐性,顺着他所答接着问道:“那可否告知我你所学的武功名字呢?我知道这世上不少内家心法有疗伤效用。不知道骆公子所学的是哪一家或者又是师出何门呢?”
骆晓听他这么问心头一黯,只觉得自己胸口沉闷口中声音都已变化的完全不像自己“我不清楚,我也不是何人弟子。”
此时这种极具压迫的四周坏境,甚至让他生出不顾一切的逃离朱府的念头。他这话在应虞怀这种大派弟子看来自然毫无说服力,他可不信骆晓为了开脱罪责所说的甚么古怪天马行空的故事,既是疗伤,又是催寒。又心衬,你若是有这种催寒的本领,就该算是内家真气的高手了何必还须如此,只要稍微懂得使用内力鼓起内劲就可挣脱开寻常锁拷。
第二十四章夜寂月明水映寒
他这时转身望见自己师妹低头,想起那日小二说话,问她道:“师妹你说那日小二描述之人,是不是姓名骆晓,衣裳同他打扮一模一样?”
文希宁嗯了一声再无其他言语,他见文希宁低头模样难免觉得心中酣畅。又看而今“低头服罪”的骆晓,更是生出鄙夷想法,他本来还以为让师妹失语的骆公子会是甚么厉害的人物,如今一看,只觉得是骆晓往日在这朱玉华与文希宁面前充作好人博得了师妹的好感,而今师妹能够重新认识他真面目也为时未晚。
此刻他见文希宁与骆晓都低着头,心中还当她对骆晓有所不舍留念,心想这小子嘴里胡话连天,我且要让师妹看清楚这小子不老实的模样,思绪至此随即朝文希宁问道:“师妹,你与骆公子曾同过路,可知道他使得是那派武功。”
“我也不清楚。”文希宁只觉得这几个字说出口,浑身心力都好像被抽干一样。
依旧是这熟悉的声音,却再难回到当初乍然入耳时的美好。
骆晓突然觉得原本以为自己与文希宁之间所存在的微妙而美好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脑海与未曾进食的腹部一样都空空如也,耳旁嗡声更甚,搅得他头脑似是开裂般疼痛。
他脑海疼痛,私心一想她说的偏偏却又是实话,自己又如何能怪她。只不过是曾经存于心中的奢望落空,所谓的爱恋不过是绮丽幻想,一厢情愿。他耳边嗡嗡乱想,盖是因疲乏至极,一种梦过人醒的回味梦境的可笑意味漂浮在心中。他以前多多少少认为文希宁多少对自己存在些映像偏爱,如今看来那只是自己一厢情愿了,不明白而今的她为何执意要将杀害朱玉华的罪责安在自己身上,自己明明从未见朱玉华在地上留过甚么字迹,她为何要这么说。
梅嫂曾抱着幼年自己说过的话语又在脑海回想,她曾多么预见性质的告诉自己不要过分希翼其它的东西,那只会使双方都不好过。是啊,自己原先就是个爹娘不要的哑巴能奢求什么呢,每日能有一碗饭吃自己就该知足,何故自取其辱恋上跟自己毫不般配的文希宁。
他是怎么也预料不到自己一直在自作多情。在面对文希宁,眼前低头指证自己的文希宁,他彻彻底底被击败了,在情感上妄加决定出击的那一刻,已经注定赌的一分都不剩,只是这短痛让人奔溃不及长痛容人消化。
他目色已经被泪水浸润,也许他自己也未注意到心中的爱意有这么压抑沉重。抬头望着眼前低头女子,仿若又变回当初的哑巴,只不过原先自己是不能说话,可现在却是自己所说的话语无人相信,就是文希宁也不相信。
文希宁呢,她一直低头自然不晓得眼前骆晓灼灼相望,她听骆晓再无说话,当他是谎言被戳破,再无言辞替自己解释。她突然觉得好累,想起骆晓手臂上赫然伤疤,决心去不想,又心头慌乱不知所以,直到这最伤这骆晓之时,文希宁才知道原来早在当日二人林中逃窜时,自己手足无措跟在头发湿漉漉的少年身后时心中就已经有了他的影子。
她觉得口中被泪水呛到,隐忍着不发作。之前来洛阳城时她已经染上风寒,现如今,头脑更是一阵眩晕。口中泪水咸湿,可她却甚么也哭不出来,她一直要求自己克制,隐藏着自己感情。自娘亲去世始,这人世中已经再难寻找到可以让自己全心依靠的人了。
她初遇骆晓之时,山洞中两人略显尴尬的相处,乃至最终牢房中的那唯一一声骆大哥,她恐怕是如何也喊不出口了。
两人最为亲近的时候竟然是二者生命最危险的时刻。
之后朱玉华的玩笑,叫两个有心人刻意装作无心莫名添了层冰壁,她没主动打破,这骆晓也没打破。
她只以为这层距离是自己可以轻易打破了,只要等待自己适应调整好了,可哪想到如今命运却把骆晓与自己放在了对立面,她不愿意相信骆晓是这害了自己好姐姐朱玉华的人,可这事实真相乃至骆晓的否定回绝,自己是绝对不会听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