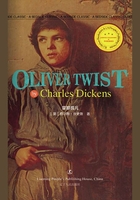“应该的。”刘不才也很机警,答得十分漂亮,“若不是那票丝弄得他焦头烂额,照他跟二哥你的交情,一定还要赶来替我伯母磕头拜寿。”
这一下倒提醒了庞二,皱着眉头说:“老胡长袖善舞,我最佩服他。何至于弄得如此!而且我也不懂,他是怎么跟洋人搞决裂的?照朱福年说,他心太急了些,让洋人看透他的实力,趁机‘拿跷’,不知道有没有这话?”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他跟洋人打交道,都是一位姓古的经手,所以这方面的情形,我隔膜得很。”
“你是说古应春?这个人我也知道,极能干的,洋人那里的信用也很好。老胡有他,如虎添翼,所以越发叫人弄不懂了。”
话要入港了,刘不才暗暗高兴,表面上却还是装佯,“怎么弄不懂?”他问。
“应该可以做得极出色的事,为啥弄得这样子狼狈,我就不懂。我想,以老胡和姓古的手腕,加上老胡跟我的实力,我真不相信搞不过洋人!”
“是啊!”刘不才做出被提醒的神气,眨着眼,皱着眉说,“照规矩说,不应该如此。到底啥道理,这趟我回上海倒要问问他。”
“我们一起走。”庞二立即相邀,“我早就要走了。只为家母的整生日,分不开身,还有几位比较客气的朋友,明天都要走了,快的话,我们后天就可以动身。”
案头正好有本皇历,刘不才随手一翻,看到后天那一行,一个大“宜”字下,密密麻麻的小字,不问可知是黄道吉日。看皇历有句俗语,叫做“呆人看长行”,长行的都是宜什么,宜什么,如果是个“破日”,只有短短一行,四个大字:“诸事不宜”。
“后天宜乎出门。”他正好怂恿,“过了后天,就得隔五天才有好日子,我常在外面跑,无所谓,你好久不出门了,该挑个好日子。”
“那,”庞二略一沉吟,毅然作了决定,“准定后天走。”
于是,刘不才陪客,庞二料理出门的杂物。纨袴子弟好面子,送人的礼物就装了半船,除了南浔的土产以外,还有两箱瓷器,是景德镇定烧的,庞老太太“六秩华诞”的寿碗,预备分送那种礼到人不到的亲友。
五月底的天气,又闷又热,出门是一大苦事,但庞二有庞二的办法,在水路上“放夜站”,白天找浓密的柳荫下将船泊下。船是两条,一条装行李,住佣人,一条是他跟刘不才的客船,十分宽敞,听差的以外,随带一位十分伶俐的小丫头服侍,纳凉、品茗、喝酒、闲谈,十分逍遥自在。
谈风月、谈赌经以外,少不得也谈到胡雪岩。庞二虽是纨袴,但出身生意人家,与做官人家那种昏天黑地、骄恣狂妄的“大少爷”毕竟不同,不但在生意买卖上相当精通,而且颇能识好坏、辨是非。加以刘不才处处小心,说到胡雪岩这一次的受窘,总是旁敲侧击,以逗人的怀疑和好奇为主。因此,庞二不能不拿古应春的信,重新找出来,再看一遍。
这一看,使得他大为不安。当时因为家里正在做寿,贺客盈门,忙得不可开交,无暇细思,朱福年来了以后,也只是匆匆的交代一番,说照胡雪岩的意思办就是。这话乍看不错,其实错了,以自己与胡雪岩的交情,如何去赚他这个九五扣一万六千银子?当然是照洋人的原价收买。
“糟了!糟了!”他不胜懊丧地说,“老胡心里一定骂我不够朋友!刘三哥,你要替我解释。”接着,他把他的疏忽,说了给刘不才听。
“庞二哥,你也太过虑了,老胡绝不是那种人!感激你帮忙还来不及,哪里会多心?”
“这叫什么帮忙?要帮忙就该——”庞二突然顿住,心里涌起好些疑问。道理是很明白地摆在那里,要讲“帮忙”,就得跟胡雪岩采取一致的态度,迫使洋人就范。论彼此的交情,应该这么办,况且过去又有约定,更应当这么办。
而目前的情形是,显而易见的各行其是了。到底是胡雪岩自己知难而退,解消了齐心一致对付洋人的约定,还是另有其他缘故?必须弄个清楚。纨袴子弟都是有了疑问,渴望立即求得解答的脾气,所以庞二吩咐船家,彻夜赶路,兼程而进,到了上海,邀刘不才一起在“一品香”客栈住下,随即命他的贴身跟班庞义,去找朱福年来见面。
在路上,刘不才已隐约听庞二谈起他的困惑,心里在想,这一见上面,说不定有一顿声色俱厉的斥责,自己是外人,夹在中间,诸多不便,因而表示要先去看胡雪岩,庞二亦不坚留,只说等下请他约了胡雪岩一起来,大家好好叙一叙。
“这下要‘猪八戒’的好看了!”听刘不才说了经过,古应春兴奋地看着胡雪岩说,“我们照计行事吧!”
朱福年的底细已经摸清楚了,他本来是想“做小货”的,亏得有庞老太太做寿一事,到了南浔,庞二先提胡雪岩的信,他见机改口,说是“正为这件事,要跟二少爷来请示”。这下,就如尤五所预料的,变成为东家赚钱,无可厚非。古应春亦就针对这情形作了布置,有个丝商也是南浔人,生意不大,人却活跃,跟庞二极熟,与古应春也是好朋友,预备通过他的关系,将胡雪岩与朱福年的秘密交涉,透露给庞二。
这个“秘密交涉”已经了结,五千银子已经退了回来。古应春“存心不良”,另外打张收条给他,将同兴钱庄的笔据,捏在手里,作为把柄。但是胡雪岩却不愿意这样做了。
“不必,不必!一则庞二很讲交情,必定有句话给我;二则朱福年也知道厉害了,何必敲他的饭碗?”他说,“我们还是从正路上去走最好。”
所谓“正路”就是将交情拉得格外近,当时决定,借怡情老二的地方,为庞二接风。本来想即时去看他,当面邀约,怕他正跟朱福年谈话,诸多不便,决定先发请帖。
“有个人要请他作陪客。”古应春笑嘻嘻地说,是不怀好意的神气。
“你是说朱福年?”胡雪岩说,“照道理应该。不过,我看他不会来。”
“不管他来不来,发了再说!”
请帖送到一品香,带回来一网篮的东西,有寿碗,有土产,另外还有庞二的一封信,道谢以外,表明准时践约。
时刻定的是“酉正”,也就是傍晚六点钟,庞二却是五点半钟就到了。欢然道故之余,胡雪岩为他引见了尤五和古应春。
庞二对古应春慕名已久,此时见他是个举止漂亮、衣饰时新的外场人物,越有好感。至于对尤五,听说他是漕帮中的顶儿尖儿,先就浮起一层神秘之感,因而看他朴实拙讷,更为好奇。纨袴子弟常喜结交江湖人物,尤五又是忠厚可亲的样子,自然一见如故。觉得这天来赴胡雪岩的邀约,大有所得。
“你那里的那位朱先生呢?”胡雪岩问道,“怎么不跟你一起来?”
一提到朱福年,庞二的笑容尽敛,代之而起的神色,不仅歉仄,还有恼怒。
“老胡,”他略一踌躇,“还是我们私底下谈的好。”他又转脸问怡情老二,“二阿姐,可有清静房间,让我们谈一歇?”
“有的,请过来。”
怡情老二带他们到了尤五平时烧酒的小房间,红木炕床上摆着现成的烟盘,她一面点上那盏“太谷灯”,一面问道:“庞二少,要不要烧一口白相?”
庞二喜欢躺烟盘,但并没有瘾,此时有正事要谈,无心烧烟来玩,便摇摇头,表示不要。怡情老二也知道他们讲的是“私话”,便悄悄退了出去,顺手掩上了房门。
“老胡,”庞二的声音很奇怪,是充满着忧虑,“你看我那个姓朱的,人怎么样?”
胡雪岩略一沉吟答说:“我跟他不熟。”
“人虽不熟,你跟他有过交往。你的这双眼睛,像电火一样,什么都瞒不过你。我们是好朋友,而且说句老实话,我佩服的人也没有几个,你就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这番话说得太恳切了,使胡雪岩在感动以外,更有不安,拿他的话细细玩味了一番,似乎是他对朱福年起了绝大的怀疑。莫非——“姓朱的拆了你的什么烂污?”他忍不住问出口来。
“现在还不敢说。”庞二点点头,“我一直当他忠心耿耿,人也能干。现在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怎么呢?”
“事情就是从你身上起的。我在想,既然我答应了你,请你全权去跟洋人打交道,何以会搞成这个样子。所以一到就找了朱福年来问,越问越不对,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只觉得他好像不知道我跟你的交情,跟你不大合作。老胡,”庞二加强语气问,“是不是这样?”
胡雪岩不肯马上回答,有意踌躇了一会才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必再谈它。”
“这样说来是有的!可见我的想法不错。接下来我问我自己的生意。”
庞二咽了口唾沫,很吃力地说:“人与人之间,不能起疑心,一起疑心,处处都是毛病——”
“这话也不尽然。”胡雪岩插了句嘴。
“我不是冤枉他,确确实实有毛病。”
“是不是账上有毛病?”
“账还没有看,不过大致问了几笔账,我已经发现有讲不通的地方。譬如说你这面吧,我在南浔就关照他:照人家胡老板的意思办。今天问他,他说货价还没有送过来,这就不对了。”
“这没有什么不对。”胡雪岩要表示风度,便得回护朱福年,“照交易的规矩,应该由我们这面跟他去接头,我们因为货色先要盘一盘,算清楚确数,才能结账,所以耽搁下来了。”
“不然!”庞二大摇其头,“信义通商,你我的交情,他不是不晓得,既然我这样说了,他应该先把货款送过来,账随后再结不要紧。现在他的做法,替我得罪朋友,可以说是得罪同业,我要他做啥?”
听庞二的口气,预备撤换朱福年。这原是胡雪岩的本意,现在他的想法不同了,庞二够朋友,他为庞二设想,不能杂以私意,因此他也大摇其头。
“庞二哥,光是为这件事,你大光其火,是说不通的——”
“当然,还有别的。”庞二抢着说,“譬如,泥城桥有块地皮,也是他来跟我说的,预备买下来造市房出租。这话有两个月了,我总以为他已经成交,今天一问,说是让人家捷足先登了。问买主是哪个,他又说不出来。老胡,你想,既然晓得人家捷足先登,怎么会不晓得人家姓啥?为啥不问一问买主?所以我要去查一查,看看是不是他自己在捣鬼?此外还有好些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从前我相信他,都忽略了,现在听起来,处处是毛病。这个人绝不能再用。你说是不是?”
胡雪岩对他那方面的情形,不甚明了,不肯轻作断语,未答之前,先问一句:“你那面‘抓总’的是哪个?”
“就是他!我那样子信任他,他对不起我,这个人真是丧尽天良。”庞二愤愤地答说。
其实这是无足为奇的事,豪门巨室的账户,明欺暗骗,东家跌倒,西宾吃饱的情形,比比皆是。看样子朱福年也是心狠手辣的人,照庞二这种态度,说不定他一不做,二不休,反会出大毛病。
因此他庄容警告:“庞二哥,你千万动不得!他现在搞了些啥花样,你还不清楚,你在明里,他在暗里,你的形势就不利。大家不破面子,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出大毛病。一听说你有动他的意思,先下手为强,拆你个大烂污,你怎么收拾?”
这话说得庞二一愣,好半天答不出话来。
“不说别的,一本总账在他手里,交易往来,人欠欠人,只有他最清楚,账里出点毛病,等你弄清楚,已是一两个月以后的事,他早就布置好了。你又能奈其何?”
“老胡,亏得你提醒我!现在没有别的好说了,你我的交情,你不能不帮我这个大忙。”
“当然。只要帮得上,你说,怎么帮法?”
“他的毛病,一定瞒不过你,我不说请他走路的话,只请你接管我的账,替我仔仔细细查一查他的毛病。”
“这件事,我不敢从命。做不到!”
庞二大为沮丧:“我晓得的,你待人宽厚,不肯得罪人。”
“这不是这么说法!庞二哥你的事,为你得罪人,我也认了,不过这样做法要有用才行,徒然得罪人,没有益处,何必去做它?你听我说——”
胡雪岩有三点理由,第一,怕打草惊蛇,反逼得朱福年去舞弊使坏;第二,庞二手下用的人很多,就算要换朱福年,也该从伙计当中去挑选替手,徐图整顿,此刻弄个不相干的人去查账,仿佛看大家都靠不住,是跟朱福年走在一条路上,通同作弊,岂不令人寒心?第三,胡雪岩也实在抽不出那许多工夫替他专办这件事。
“而况,我对你那方面的情形又不清楚,贸贸然下手,一年半载不能完事,在我有没有工夫,且不去说它,就怕一年半载下来,查不出名堂,那时你做东家的,对伙计如何交代?”
“这没有什么!我现在可以断定,朱福年一定有毛病。”
“毛病可以弥补的——”
“对啊!”庞二抢着说道,“只要你一去,他看见厉害的人来了,赶紧想法子把他的毛病弥补起来,你不就帮了我的大忙了吗?”
这话倒也驳他不倒。胡雪岩想了一会,总觉得庞二的做法,不甚妥当,就算将朱福年的毛病查出来了,甚至于照庞二的如意算盘,把胡雪岩三个字抬了出去,就能叫朱福年敛迹,弥补弊病,然而以后还用不用他呢?这样想着,便问出口来:“庞二哥,这朱某人的本事到底怎么样?”
“本事是有的。”
“如果他肯改过,实实在在替你办事,你还用不用他?”
“如果是这样,当然可以用。不过——”他摇摇头,觉得说下去就没有味道了。
“我懂你的意思。”胡雪岩停了一下说,“人不对,请他走路,这是普通人的做法,你庞二哥要么不出马,一出马就要叫人晓得厉害,佩服你确是有一套。”
这两句话,最配争强好胜的纨绔脾气,所以庞二精神一振,有了笑容。
“老胡,你这两句话我交关听得进。你倒再说说看,应该怎么做法?”
“要像诸葛亮‘七擒孟获’那样,‘火烧藤甲兵’不足为奇,要烧得他服帖,死心塌地替你出力,才算本事。”
“话是一点都不错,不过,”庞二踌躇着说,“我实在没有这份本事。”说到这里,突然眼睛一亮,拍着自己的后脑勺,“我真糊涂了!现成的诸葛亮在这里。老胡,”他停了一下,喜逐颜开地又说,“我送你股份,你算是跟我合伙,也是老板的身份,名正言顺来管事,不就可以收服朱福年了吗?”
胡雪岩的打算就是如此,不过自己说不出口,难得庞二的想法相同。光就是这一点,便值得替他出一番力了。
胡雪岩有项过人的长处,能在心血来潮之际,作出重要而正确的决定,思路快不足为奇,能快又能细致深刻,就只有他有此本事。
此刻便是这样。因为庞二先作提议,就是个极好的机会,他抓住了题目的精义,立即便有一篇好文章交卷。“庞二哥,”他正色说道,“生意是生意!分花红彼此礼让,是交朋友的情分、义气,不可一概而论。我是不赞成吃干股这一套花样的,如果你看得起我,愿意让我搭点股份,我交现银出来。”
“好啊!”庞二欣然同意,因为这一来,胡雪岩就更加出力。他问:“你想要多少股子?”
“我的实力比你差得远,只能来个两成。”
“一句话!我们重新盘过,你十万,我四十万,我们五十万银子下手,上海的市面,可以捏在手里了。”
“准定如此,庞二哥,”胡雪岩带点兴奋的神色,“我的钱庄,你也来点股子。索性大家滚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看好不好?”
“怎么不好!礼尚往来,再好不过!而且便宜不落外方,你在上海立一爿分号起来,我们自己的款子存在自己的钱庄里,岂不方便?”
胡雪岩的打算就是如此,他还有进一步的打算,此刻却不宜先露,只是连连称“是”。接着又说定庞二的股份,真个礼尚往来,他也是十万,彼此只要立个合伙的合同,划一笔账,都不必另拨现银。
他们谈得津津有味,外面却等得心急了,酒已经回烫过两遍,再烫就要走味,怡情老二推门望到第三遍,看他们还没有住口的样子,忍不住便轻轻咳嗽了一声。
这下才惊醒了庞二,歉然说道:“对不起,对不起,害他们久等了,我们出去吧!”
等坐定下来,第一件事是叫局。怡情老二亲自捧过一只长方红木托盘,里面是笔砚局票,拈笔在手,先问庞二。
“我好久没有到上海来了,市面不灵。”他想了想说,“叫宝琴老三吧?”
“是怡红院的宝琴老三吗?”怡情老二问。
“对了,怡红院。”
“这一节不做了。”怡情老二说,“节前嫁了个道台,做官太太去了。”
于是庞二又想了两个人,非常不巧,不是从良,便是开了码头,他不免怅惘,说一声:“随便找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