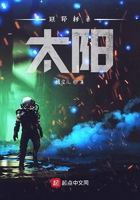到了不可开交的时候,便要由阜康出面来“挺”了。那时永兴盛便成为俎上之肉,怎么宰割都可以,或者维持它,或者接收了过来。当然,这要担风险,永兴盛是个烂摊子,维持它是从井救人,接收下来可能成为不了之局。整个计划,这一点是成败的关键所在。胡雪岩颇费思考,想来想去,只有这样做法最稳妥,就是临时见机行事,能管则管,不能管反正有江苏官方出面去提款,自己这方面并无干系。
然而这样做法,稳当是稳当,可能劳而无功,也可能损人不利己,徒然搞垮永兴盛。转念到此,觉得现在还不到决定的时候,这事如果真的要做,还得进一步去摸一摸永兴盛的底,到底盈亏如何,陈老板另外有多少产业,万一倒闭下来,“讲倒账”有个几成数?这些情形都了解了,才能有所决定。因此,等周一鸣一到,他就这样问:“你那个在永兴盛的朋友,对他们店里的底细,究竟知道多少?”
“那就说不上来了,不过,要打听也容易,永兴盛的伙计大都跟陈老板和那个‘冲天炮’不和,只要知道底细,一定肯说。”
“好的,你托你那朋友去打听。”胡雪岩说,“事情要做得秘密。”
“我知道,不过,这不是三两天的事。怕你老等不及。”
“不忙,不忙!”胡雪岩说,“你打听好了,写信给我就是。”
“是!”周一鸣停了一下又说,“我把胡大老爷的事办好了,就动身到扬州,先看看情形,倘或没啥意思,我到上海来投奔你老。”
“我也希望你到我这里来。果真扬州没意思,我欢迎你。不过,不必勉强。”胡雪岩仍旧回到永兴盛的话头上,“你那个朋友叫啥?”
“他姓郑,叫郑品三。”
“为人如何?”
“蛮老实,也蛮能干的。”
“这倒难得!老实的往往无用,能干的又以滑头居多。”胡雪岩心念一动,“既然是这样一个人,你能不能带他来见一见?”
“当然!当然!他也晓得你老的。”
“他怎么会晓得?”
“是我跟他说的。不过他也听说过,杭州阜康的东家姓胡。”周一鸣问道,“胡大老爷看什么时候方便?我带他来。”
“你明天就要动身,你今天晚上带他来好了。”
真假丈夫
小狗子果然很巴结,“午炮”刚刚放过,人就来了,一共来了五个人,三个留在院子里,带着麻袋和扁担。一个带进屋来,不用说,是阿巧姐的丈夫。
据说他姓陈,四十岁左右,畏畏缩缩,是个极老实的人,臃臃肿肿一件棉袄,外面罩着件簇新的毛蓝布衫,赤脚草鞋。进得门来,只缩在门边,脸上说不出是忸怩还是害怕。
“请坐,请坐!”胡雪岩转脸问小狗子,“都谈好了?”
“谈好了。”说着,他从身上掏出来两张桑皮纸的笔据,连“休书”都预备好了。
胡雪岩接过来看了一遍,写得十分扎实,表示满意,“就这样!”他指着周一鸣说,“我们这面的中人在这里,你算是那方面的中人。还要个‘代笔’,就挑金阊栈的账房赚几个。”
“胡大老爷,”小狗子赶紧抢着说,“代笔我们带来了。”接着便往外喊了一声:“刘先生!”
五个人当中,只有这个“刘先生”是穿了长衫的,獐头鼠目,不似善类。
胡雪岩忽然动了疑心,然后发觉自己有一步棋,非走不可的,却忘了去走。因此,一面敷衍着,一面把周一鸣拉到一边,悄悄说道:“有件事,我疏忽了。你看,这姓陈的,像不像阿巧姐的男人?”
“这怎么看得出来?”
“万一是冒充的,怎么办?钱还是小事,要闹大笑话!”胡雪岩说,“我昨天忘了关照一句话,应该请他们族长到场。”
“那也可以。我跟小狗子去说。”
“一来一往,耽误工夫也麻烦。”胡雪岩说,“只要‘验明正身’,不是冒充,他们陈家族长来不来,倒也不生关系。”
“哪个晓得他是不是冒充?”周一鸣说,“除非请阿巧姐自己来认。”
这倒是一语破的!除此以外,别无善策。胡雪岩考虑了一下,断然定下了缓兵之计。于是周一鸣受命招待小狗子吃午饭,胡雪岩则以要到钱庄去兑银子作托词,出了金阊栈,坐轿直奔潘家。
一张名帖,附上一个丰腴的门包,胡雪岩向潘家的门房,坦率道明来意,他家主人见不见都无所谓,目的是要跟阿巧姐见面。
潘叔雅是惮于世俗应酬的“大少爷”,听得门房的通报,乐得偷懒,便请阿巧姐径自出见。她一见胡雪岩空手上门,颇为失望,不免埋怨:“你也要替我做做人!我在这里,人家客气得不得了,真正叫人不安。”
“你放心!我已经打算好了,一定叫你有面子。现在闲话少说,你马上跟我回客栈,去认一个人。”
“认一个人!认哪个?”阿巧姐眨闪着极长的睫毛,异常困惑地问。
“你想想看,还有哪个是非要你去认不可的?”
这句反问,就点得很清楚了,然而阿巧姐却越感困惑,“到底怎么回事?”她有些不悦,觉得胡雪岩办这样的大事,不该不先商量一下,所以很认真地表示:“你不说清楚,我绝不去。”
胡雪岩十分见机,赔着笑说:“你不要怪我独断独行,一则是没有机会跟你说,二则是免得你操心,我是好意。”
“谢谢你的好意。”阿巧姐接受了他的解释,但多少还有些余憾,而且发觉处境颇为尴尬,“当面锣,对面鼓,你叫我怎么认法。”
“不是,不是!用不着你照面,你只要在壁缝里张一张,认清楚了人,就没你的事了。”接着,胡雪岩把如何收服了小狗子的话,扼要说了一遍。
“你的花样真多!”阿巧姐笑着说了这一句,脸色突然转为严肃,眼望着砖地,好久不作声。
这神态使得胡雪岩有些着急,同时也有些失悔,事情真的做得欠检点了!阿巧姐与她丈夫的感情不太好,只是听了怡情老二的片面之词,她本人虽也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与夫家几乎已断绝往来,但这种门户人家的话,靠不住的居多,俗语说得好:“骗死人不偿命”,自己竟信以为真,一本正经去办,到了紧要关头,就会变成自讨苦吃,阿巧姐固然不见得有意欺骗,然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看样子是别有衷曲,须当谅解?说来说去是自己鲁莽,怪不得她。
怪不怪她在其次,眼前的难题是,阿巧姐如果不肯点头,小狗子那面就不好交代。跑到苏州来做这么一件荒唐事,传出去成为笑话,自己的这个面子却丢不起。因而急于要讨她一句实话。
“阿巧姐!”他神色严重地说,“到这时候,你再不能敷衍我了,你心里的意思,到底怎么样,要跟我实说!”
“咦!”阿巧姐深感诧异,“我几时说假话敷衍过你?”
“那么,事情到了这地步,你像煞要打退堂鼓,是为啥?”
阿巧姐觉得好笑,“我又不曾像县大老爷那样坐堂,啥叫打退堂鼓?”她这样反诘。
话越发不对了,细辨一辨,其中有刺,意思是说,胡雪岩做这件事之先,既未告诉过她,更未征求同意,这就是“不曾坐堂”,然则又何来“退堂鼓”可言?胡雪岩心想,阿巧姐是厉害角色,此时不宜跟她讲理,因为自己道理欠缺,讲不过她。唯有动之以情,甚至骗一骗她再说。
于是他先认错:“这件事怪我不好。不过我一定顺你的心意,绝不勉强。现在人在那里,你先去认一认,再作道理。人不对,不必再谈,人对了,看你的意思,你说东就东,你说西就西,我决无二话。”
人心到底是肉做的,听得他这样说,阿巧姐不能再迟疑了,其实她的迟疑,倒不是对她丈夫还有什么余情不忍割舍,只是想到她娘家,应该让胡雪岩拿笔钱出来,替她娘养老。这个条件,似乎应该在此时一并来谈,却又不知如何谈法。迟疑者在此,而胡雪岩是误会了。
“那么你请坐一坐,我总要跟主人家去说一声。”她又问,“你可曾雇了轿子?”
“这方便,我轿子留给你,我另雇一乘。”胡雪岩说,“到了金阊栈,你从边门进来,我叫人在那里等你。”
这样约定了,胡雪岩先离了潘家,轿子是阊门附近的,坐过两回,已经熟识,等吩咐妥当,另雇一乘,赶回金阊栈,再赁一间屋子,关照伙计,专门守在边门上,等阿巧姐一到,悄悄引入,然后进来照一照面,无须开口。
一切布置妥帖,胡雪岩方回到自己屋里,坐候不久,周一鸣领着小狗子等人,吃了饭回来,一个个脸上发红,似乎喝了不少酒。彼此又作了一番寒暄,胡雪岩便海阔天空地谈苏州的风光,周一鸣会意,是要拖延辰光,就在一旁帮腔,谈得极其热闹,却始终不提正事。
小狗子有些忍不住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隙,插进一句话去:“胡大老爷,我们今天还想赶回木渎,时间太迟了不方便。现在就动手吧!”
“喔,喔,”胡雪岩歉意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再略等一等,等钱庄的伙计一到,凑够了银钱,我们马上动手。好在只是画一个花押,快得很。”
这样一说,小狗子就又只好耐心等候,但局促不安的情状,越来越明显。胡雪岩冷眼旁观,心头疑云愈密,暗暗又打了第二个主意。
正想托词把周一鸣找到一边商量,那守候的伙计出现了,他也很机警,提着茶壶来冲茶,暗中使了一个眼色,竟连周一鸣都不曾发觉。
于是胡雪岩告个便,在另一屋中见着阿巧姐,悄悄说道:“回头我引一个人出来,你细细看,不要作声。我马上又会回来。”叮嘱完了,仍回原处,对阿巧姐的丈夫招招手。那个畏畏缩缩的中年人,只是望着小狗子,用眼色在讨主意。
“胡大老爷,你有啥话,跟我说!”
“没有啥要紧话,不过,这句话也不便让外人听见。”胡雪岩又连连招手,“请过来,请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