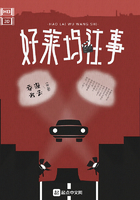因此,他竟没有一句话说。这一方面是感到对阿巧姐安慰,或为七姑奶奶辩护都不甚合适,另一方面也实在是沮丧得什么话都懒得说了。
一见萧家骥的脸色,胡雪岩吓一大跳,他倒像害了一场病似的。何以跟阿巧姐见了一次面,有这样的似乎受了极大刺激的神情?令人惊疑莫释,而又苦于不便深问,只问得一句:“见过面了?”
“见过了。我们谢过了尘师太,告辞吧!”
了尘又变得很沉着了,她也不提阿巧姐,只殷勤地请胡雪岩与萧家骥再来“随喜”。尼姑庵中何以请男施主来随喜?这话听来便令人有异样之感,只是无暇去分辨她的言外之意。不过,胡雪岩对人情应酬上的过节,一向不会忽略,想到有件事该做,随即说了出来:“请问,缘簿在哪里?”
“不必客气了!”
胡雪岩已经发现,黄色封面的缘簿,就挂在墙壁上,便随手摘下,交给萧家骥说:“请你写一写,写一百两银子。”
“太多了!”了尘接口说道,“如果说是为了宝眷住在我们这里,要写这么多,那也用不着!出家人受十方供养,也供养十方,不必胡施主费心。”
“那是两回事。”萧家骥越出他的范围,代为回答,“各人尽各人的心意。”
接着,萧家骥便用现成的笔砚,写了缘簿,胡雪岩取一张一百两的银票,夹在缘簿中一起放在桌上,随即告辞出庵。
回营谢过朱管带,仍旧由原来护送的人送回上海。一路奔驰,无暇交谈,到了闹区,萧家骥才勒住马说道:“胡先生,到你府上去细谈。”
于是遣走了那名马弁,一起到胡雪岩与阿巧姐双栖之处。粉奁犹香,明镜如昨,但却别有一股凄凉的意味。胡雪岩换了一个地方,在他书房中闭门深谈。
听萧家骥转述了阿巧姐的愤慨之词,胡雪岩才知道他为何有那样的痛苦的神态。当然,在胡雪岩也很难过。自他认识七姑奶奶以来,从未听见有人对她有这样严苛的批评,如今为了自己,使她在阿巧姐口中落了个阴险小人的名声,想想实在对不起七姑奶奶。
“胡先生,”萧家骥将一路上不断在想的一句话,问了出来,“我师娘是不是真的像阿巧姐所说的那样,是有意耍手段?”
“是的。”胡雪岩点点头,“这是她过于热心之故。阿巧姐的话,大致都对,只有一点她弄错了。你师娘这样做,实实在在是为她打算。”
接着胡雪岩便为七姑奶奶解释,她是真正替阿巧姐的终身打算,既然不愿做偏房,不如分手,择人而事。他虽不知道七姑奶奶有意为阿巧姐与张郎中撮合,但他相信,以七姑奶奶的热心待人,一定会替阿巧姐觅个妥当的归宿。
这番解释,萧家骥完全能够接受,甚至可以说,他所希望的,就是这样一番能为七姑奶奶洗刷恶名的解释。因此神态顿时不同,轻快欣慰,仿佛卸下了肩上的重担似的。
“原说呢,我师娘怎么会做这种事?她如果听说阿巧姐是这样深的误会,不知道要气成什么样子?”
“对了!”胡雪岩矍然惊觉,“阿巧姐的话,绝对不能跟她说。”
“不说又怎么交代?”
于是两个人商量如何搪塞七姑奶奶。说没有找到,她会再托阿金去找,说是已经祝发,决不肯再回家,她一定亦不会死心,自己找到白衣庵去碰钉子。想来想去没有妥当的办法。
丢下这层不谈,萧家骥问道:“胡先生,那么你对阿巧姐,究竟作何打算呢?”
这话也使得胡雪岩很难回答,心里转了好半天的念头,付之一叹:“我只有挨骂了!”
“这是说,决定割舍?”
“不割舍又如何?”
“那就这样,索性置之不理。”萧家骥说,“心肠要硬就硬到底!”
“是我自己良心上的事。”胡雪岩说,“置之不理,似乎也不是办法。”
“怎么才是办法?”萧家骥说,“要阿巧姐心甘情愿地分手,是办不到的事。”
“不求她心甘情愿,只望她咽得下那口气。”胡雪岩作了决定,“我想这样子办——”
他的办法是一方面用缓兵之计,稳住七姑奶奶,只说阿巧姐由白衣庵的当家师太介绍,已远赴他乡,目前正派人追下去劝驾了,一方面要拜托怡情老二转托阿金:第一,帮着瞒谎,不能在七姑奶奶面前道破真相;第二,请她跟阿巧姐去见一面,转达一句话,不管阿巧姐要干什么,祝发也好,从良也好,乃至于步了尘的后尘也好,胡雪岩都不会干预,而且预备送她一大笔钱。
说完了他的打算,胡雪岩自己亦有如释重负之感,因为牵缠多日,终于有了快刀斩乱麻的处置。而在萧家骥,虽并不以为这是一个好办法,只是除此以外,别无善策,而况毕竟事不干己,要想使劲出力也用不上,只有点点头表示赞成。
“事不宜迟,你师娘还在等回音,该干什么干什么,今天晚上还要辛苦你。”
“胡先生的事就等于我师父的事,”萧家骥想了一下说,“我们先去看怡情老二。”
到了怡情老二那里,灯红酒绿,夜正未央。不过她是“本家”,另有自己的“小房子”。好在相去不远,“相帮”领着,片刻就到。入门之时,正听得客厅里的自鸣钟打十二下,怡情老二虽不曾睡,却已上楼回卧室了。
听得小大姐一报,她请客人上楼。端午将近的天气,相当闷热。她穿一件家常绸夹袄对客,袖管很大也很短,露出两弯雪白的膀子,一只手膀上戴一支金镯,一只手腕上戴一支翠镯,丰容盛鬋,一副福相。这使得萧家骥又生感触,相形之下,越觉得阿巧姐憔悴可怜。
由于胡、萧二人是初次光临,怡情老二少不得有一番周旋,倒茶摆果碟子,还要“开灯”请客人“躺一息”。主人殷勤,客人当然也要故作闲豫,先说些不相干的话,然后谈入正题。
萧家骥刚说得一句“阿巧姐果然在白衣庵”,小大姐端着托盘进房,于是小酌消夜,一面细谈此行经过。萧家骥话完,胡雪岩接着开口,拜托怡情老二从中斡旋。
一直静听不语的怡情老二,不即置答。事情太离奇了,她竟一时摸不清头绪,眨着眼想了好一会才摇摇头说:“胡老爷,我看事情不是这么做法。这件事少不得七姑奶奶!”
接着,她谈到张郎中,认为七姑奶奶的做法是正办。至于阿巧姐有所误会,无论如何是解释得清楚的。为今之计,只有设法将阿巧姐劝了回来,化解误会,消除怨恨,归嫁张宅,这一切只要大家同心协心花功夫下去,一定可以有圆满的结局。
“阿金不必让她插手了,决绝的话,更不可以说。现在阿巧姐的心思想偏了,要耐心拿它慢慢扭过来。七姑奶奶脾气虽毛糙,倒是最肯体恤人、最肯顾大局,阿巧姐的误会,她肯原谅的,也肯委屈的。不过话可以跟她说明白,犯不着让她到白衣庵去碰钉子。我看,胡老爷——”
她有意不再说下去,是希望胡雪岩有所意会,自动作一个表示。而胡雪岩的心思很乱,不耐细想,率直问道:“二阿姐,你要说啥?”
“我说,胡老爷,你委屈一点,明天再亲自到白衣庵去一趟,赔个笑脸,说两句好话,拿阿巧姐先劝了回来再说。”
这个要求,胡雪岩答应不下。三番两次,牵缠不清,以致搁下好多正事不能办,他心里实在也厌倦了。如今好不容易有了个快刀斩乱麻的措施,却又不能实行,反转要跟阿巧姐去赔笑脸,说好话,不但有些于心不甘,也怕她以为自己回心转意,觉得少不得她,越发牵缠得紧,岂不是更招麻烦?
看他面有难色,怡情老二颇为着急,“胡老爷,”她说,“别样见识,我万万不及你们做官的老爷们,只有这件事上,我有把握。为啥呢?女人的心思,只有女人晓得。再说,阿巧姐跟我相处也不止一年,她的性情,我当然摸得透。胡老爷,我说的是好话,你不听会懊悔!”
胡雪岩本对怡情老二有些成见,觉得她未免有所袒护,再听她这番话,成见自然加深,所以一时并无表示,只作个沉吟的样子,当作不以为然的答复。
萧家骥旁观者清,一方面觉得怡情老二的话虽说得率直了些,而做法是高明的。另一方面又知道胡雪岩的心境,这时不便固劝,越劝越坏。好在阿巧姐的下落明了,在白衣庵多住些日子亦不要紧。为了避免造成僵局,只有照“事缓则圆”这句话去做。
“胡先生也有胡先生的难处,不过你的宗旨是对的!”他加重了语气,同时对怡情老二使个眼色,“慢慢来,迟早要拿事情办通的。”
“也好。请萧少爷劝劝胡老爷!”
“我知道,我知道。”萧家骥连声答应,“明天我给你回话。今天不早了,走吧!”
辞别出门,胡雪岩步履蹒跚,真有心力交瘁之感。萧家骥当然亦不便多说,只问一句:“胡先生,你今天歇在哪里?我送你去。”
“我到钱庄里去睡。”胡雪岩说道,“你今天还要不要去见你师娘?”
“今天就不必去了。这么晚!”
“好的。”胡雪岩沉吟了一会,皱眉摇头,显得不胜其烦似的,“等一两天再说吧!我真的脑筋都笨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拉拉扯扯、弄不清爽的麻烦!”
“那么,”萧家骥低声下气地,倒像自己惹上了麻烦,向人求教那样,“明天见了我师娘,我应当怎么说?”
这一次胡雪岩答得非常爽脆:“只要不伤你师娘的心,怎么说都可以。”
回到钱庄,只为心里懊恼,胡雪岩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市声渐起,方始朦胧睡去。
正好梦方酣之时,突然被人推醒,睁开涩重的睡眼,只见萧家骥笑嘻嘻地站在床前,“胡先生,”他说,“宝眷都到了!”
胡雪岩睡意全消,一骨碌地翻身而起,一面掀被,一面问道:“在哪里?”
“先到我师娘那里,一翻皇历,恰好是宜于进屋的好日子,决定此刻就回新居。师娘着我来通知胡先生。”
于是胡家母子夫妇父女相聚,恍如隔世,全家大小,呜咽不止,还有七姑奶奶在一旁陪着掉泪。好不容易一个个止住了哭声,细叙别后光景,谈到悲痛之处,少不得又淌眼泪。就这样谈了哭、哭了谈,一直到第三天上,胡老太太与胡雪岩的情绪,才算稳定下来。
这三天之中,最忙的自然是七姑奶奶。胡家初到上海,一切陌生,处处要她指点照料。但是只要稍微静了下来,她就会想到阿巧姐,中年弃妇,栖身尼寺,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不知生趣何在。
因此,她不时会自惊:不要阿巧姐寻了短见了?这种不安,与日俱增,不能不找刘不才去商量了。
“不要紧!”刘不才答说,“我跟萧家骥去一趟,看情形再说。”
于是找到萧家骥,轻车熟路,到了白衣庵,一叩禅关,来应门的仍旧是小音。
“喔,萧施主,”小音还认得他,“阿巧姐到了宁波去了!”
这个消息太突兀了,“她到宁波去做什么?”萧家骥问。
“我师父会告诉你。”小音答说,“我师父说过,萧施主一定还会来,果然不错。请进,请进。”
于是两人被延入萧家骥上次到过的那座精舍中。坐不到一盏茶的工夫,了尘飘然出现,刘不才眼睛一亮,不由得含笑起立。
“了尘师太,”萧家骥为刘不才介绍,“这位姓刘,是胡家的长亲。”
“喔,请坐!”了尘开门见山地说,“两位想必是来劝阿巧姐回去的。”
“是的。听小师太说,她到宁波去了?可有这话?”
“前天走的。去觅归宿去了。”
萧家骥大为惊喜,“了尘师太,”他问,“关于阿巧姐的身世,想来完全知道?”
“不错!就因为知道了她的身世,我才劝她到宁波去的。”
“原来是了尘师太的法力无边,劝得她回了头!”刘不才合十在胸,闭着眼喃喃说道,“大功德,大功德!”
模样有点滑稽,了尘不由得抿嘴一笑,对刘不才仿佛很感兴味似的。
“的确是一场大功德!”萧家骥问道,“了尘师太开示她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们听听?”
“无非拿‘因缘’二字来打动她。我劝她,跟胡施主的缘分尽了,不必强求。当初种那个因,如今结这个果,是一定的。至于张郎中那面,种了新因,依旧会结果,此生不结,来世再结。尘世轮回,就是这样一番不断的因果,倒不如今世了掉这番因缘,来世没有宿业,就不会受苦,才是大彻大悟的大智慧人。”了尘接着又说,“在我养静的地方,对榻而谈,整整劝了她三天,毕竟把她劝醒了!”
“了不起!了不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刘不才说,“不是大智慧人遇着大智慧人,不会有这场圆满的功德。”
“刘施主倒真是辩才无碍。”了尘微笑着说,眼睛一瞟,低头无缘无故地微微笑着。
“了尘师太太夸奖我了。不过,佛经我亦稍稍涉猎过,几时得求了尘师太好好开示。”
“刘施主果真向善心虔,随时请过来。”
“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刘不才张目四顾,不胜欣赏地,“这样的洞天福地,得与师太对榻参禅,这份清福真不知几时修到。”
了尘仍是报以矜持的微笑,萧家骥怕刘不才还要噜苏,赶紧抢着开口:“请问了尘师父,阿巧姐去了还回不回来?”
“不回来了!”
“那么她的行李呢?也都带到了宁波?”
“不!她一个人先去。张郎中随后会派人来取。”
“张郎中派的人来了,能不能请了尘师太带句话给他,务必到阜康钱庄来一趟。”
“不必了!”了尘答说,“一了百了,请萧施主回去,也转告胡施主,缘分已尽,不必再自寻烦恼了。”
“善哉!善哉!”刘不才高声念道,“‘欲除烦恼须无我,各有因缘莫羡人!’”
见此光景,萧家骥心里不免来气,刘不才简直是在开搅。一赌气之下,别的话也不问了,起身说道:“多谢了尘师父,我们告辞了。”
刘不才犹有恋恋不舍之意,萧家骥不由分说,拉了他就走。
一回到家,细说经过,古应春夫妇喜出望外,不过七姑奶奶犹有怏怏不乐之意,“你还应该问详细点!”她略有怨言。
这一下正好触动萧家骥的怨气,“师娘,”他指着刘不才说,“刘三爷跟了尘眉来眼去吊膀子,哪里有我开口的份?”接着将刘不才的语言动作,描画了一遍。
古应春夫妇大笑,七姑奶奶更是连眼泪都笑了出来。刘不才等他们笑停了说:“现在该我说话了吧?”
“说,说!”七姑奶奶笑着答应,“刘三叔,你说。”
“家骥沉不住气,这有啥好急的?明天我要跟了尘去‘参禅’,有多少话不好问她?”
“对啊!刘三叔,请你问问她,越详细越好。”
古应春当时不曾开口,过后对刘不才说:“你的话不错,‘欲除烦恼须无我,各有因缘莫羡人’。小爷叔跟阿巧姐这段孽缘,能够有这样一个结果,真正好极!不必再多事了。刘三叔,我还劝你一句,不要去参什么禅!”
“我原是说说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