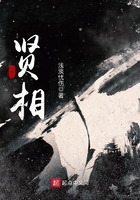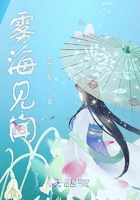宓本常心里又是一跳,汇丰的存款只有六万多,开十万的支票,要用别家的庄票去补足,按规定当天不能抵用,虽可情商通融,但苦于无法抽空,而且当此要紧关头,去向汇丰讨情面,风声一传,有损信用。
转念到此,心想与其向汇丰情商,何不舍远就近向姓毛的情商,“毛先生,”他说,“可不可以分开来开?”
“怎么分法?”
“一半汇丰、一半开本号的票子?”
姓毛的微微一笑,“不必了。”他说,“请你把存折还给我。”
宓本常心想,果不其然,是张兆馥耍花样,原来“馥记”便是张兆馥,此人做纱花生意,跟胡雪岩是朋友,宓本常也认识,有一回吃花酒,彼此都有了酒意,为了一个姑娘转局,席面上闹得不大愉快。第二天宓本常酒醒以后,想起来大为不安,特意登门去陪不是,哪知张兆馥淡淡地答了一句:“我是你们东家的朋友,不必如此。”意思是不认他作朋友,如今派人上门来提存,自是不怀好意,不过何以要提又不提了,其中是何蹊跷,费人猜疑。
等将存折接到手,姓毛的说道:“你害我输了东道!”
“输了东道?”宓本常问道,“毛先生你同哪位赌东道?赌点啥?”
“自然是同张兆馥--”
姓毛的说,这天上午他与张兆馥在城隍庙西园吃茶,听说阜康挤兑,张兆馥说情势可危,姓毛的认为阜康是金字招牌,可保无虞。张兆馥便说阜康在汇丰银行的存款,只怕不足十万,不信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如果阜康能开出汇丰银行十万两的支票,他在长三堂子输一桌花酒,否则便是姓毛的作东。
糟糕到极点了!宓本常心想,晚上这一桌花酒吃下来,明天十里夷场上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传说,阜康在汇丰银行的存款,只得五万银子。
果然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非力挽狂澜不可。宓本常左思右想,反复盘算,终于想到了一条路子,将上海道衙门应缴的协饷先去提了来,存在汇丰,作为阜康的头寸,明天有人来兑现提存,一律开汇丰的支票。
宓本常每回到上海道衙门去催款或打听消息,都找他的一个姓朱的同乡,一见面便问:“你怎么有工夫到这里来?”
宓本常愕然,“为什么我没有工夫?”他反问一句。
“听说阜康挤兑。”姓朱的说,“你不应该在店里照料吗?”
宓本常一惊,挤兑的消息已传到上海道衙门,催款的话就难说,但他的机变很快,心想正好用这件事来作借口,“挤兑是说得过分了,不过提存的人比平常多,是真的,这都是十月二十一日的一道上谕,沿江戒严,大家要逃难的缘故。阜康的头寸充足,尽管来提,不要紧。”他紧接着又说,“不过,胡大先生临走交代,要预备一笔款子,垫还洋款,如今这笔款子没有办法如数预备了,要请你老兄同邵大人说一说,收到多少先拨过来,看差多少,我好筹划。”
“好!”姓朱的毫不迟疑地说,“你来得巧,我们东家刚到,我先替你去说。”
宓本常满心欢喜,而且不免得意,自觉想出来的这一招很高明,哪知姓朱的很快地就回来了,脸上却有狐疑的神气。
“你请放心回去好了。这笔洋款初十到期,由这里直接拨付,阜康一文钱都不必垫。”
宓本常一听变色,虽只是一瞬间的事,姓朱的已看在眼里,越加重了他的疑心,“老宓,我倒问你句话,我们东家怪我,怎么不想一想,阜康现在挤兑,官款拨了过去,替你们填馅子,将来怎么交公账?”他问,“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打算?”
宓本常哪里肯承认,连连摇手:“没有这话,没有这话!”
“真的?”
“当然真的,我怎么会骗你。”
“我想想你也不会骗我,不然,你等于叫我来‘掮木梢’,就不像朋友了。”
这话在宓本常是刺心的,唯有赔笑道谢,告辞出来,脚步都软了,仿佛阜康是油锅火山等着他去跳似的。
回到阜康,他是从“灶披间”的后面进去的,大门外人声鼎沸,闻之心惊,进门未几,有个姓杜的伙计拦住他说:“宓先生,你不要到前面去!”
“为啥?”
“刚才来了两个大户,一个要提二十五万、一个要提十八万,我说上海的头寸,这年把没有松过,我们档手调头寸去了,他说明天再来。你一露面,我这话就不灵了。”
山穷水尽的宓本常真有柳暗花明之乐,心想说老实话也是个搪塞法子,这姓杜的人很能干,站柜台的伙计,以他为首,千斤重担他挑得动,不如就让他来挑一挑。
于是他想了一下说:“不错!你就用这话来应付,你说请他们放心,我们光是丝就值几百万银子,大家犯不着来挤兑。”
“我懂。”杜伙计说,“不过今天过去了,明天要有交代。”
“那两个大户明天再来,你说我亲自到宁波去提现款,要五天工夫。”宓本常又说,“我真的要到宁波去一趟,现在就动身。”
“要吃中饭了,吃了饭再走。”
“哪里还吃得下饭。”宓本常拍拍他的肩,“这里重重托你。等这个风潮过去了,我要在大先生面前好好保荐你。”
哪知道午后上门的客户更多了,大户也不比上午的两个好说话,人潮汹涌、群情愤慨,眼看要出事故,巡捕房派来的那个“三道头”追问宓本常何在,姓杜的只好说实话:“到宁波去了。”
“这里怎么办?”
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有阿章说了句:“只好上排门。”
绝地求生
螺蛳太太已经上床了,丫头红儿来报,中门上传话进来,说阜康的档手谢云青求见。
“这时候--”螺蛳太太的心蓦地里往下一落,莫非胡雪岩得了急病?她不敢再想下去了。
“太太!”红儿催问,“是不是叫他明天早上来?”
“不,”螺蛳太太说,“问问他,有什么事?”
“只说上海有电报来。”
“到底什么事呢?去问他。”螺蛳太太转念,不是急事,不会此刻求见,既是急事,就不能耽误工夫,当即改口,“开中门,请谢先生进来。”她又加了一句,“不要惊动了老太太。”
红儿一走,别的丫头服伺螺蛳太太起床,穿着整齐,由丫头簇拥着下了楼。
她也学会了矫情镇物的工夫,心里着急,脚步却依旧稳重,走路时裙幅几乎不动--会看相的都说她的“走相”主贵,她本人亦颇矜持,所以怎么样也不肯乱了脚步。
那谢云青礼数一向周到,望见螺蛳太太的影子,老远就垂手肃立,眼观鼻、鼻观心地等候着,直到一阵香风飘来,闻出是螺蛳太太所用的外国香水,方始抬头作揖,口中说道:“这样子夜深来打扰,实在过意不去。”
“请坐。”螺蛳太太左右看了一下,向站在门口的丫头发话,“你们越来越没有规矩了,客人来了,也不倒茶。”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我接得一个消息,很有关系,不敢不来告诉四太太。”
“喔,请坐了谈。”说着,她摆一摆手,自己先在上首坐了下来。
“是这样的。”谢云青斜欠着身子落座,声音却有些发抖了,“刚刚接到电报,上海挤兑,下半天三点钟上排门了。”
螺蛳太太心头一震,“没有弄错吧!”她问。
“不会弄错的。”谢云青又说,“电报上又说,宓本常人面不见,据说是到宁波去了。”
“那么,电报是哪个打来的呢?”
“古先生。”
古应春打来的电报,绝不会错,螺蛳太太表面镇静,心里乱得头绪都握不住,好一会儿才问:“大先生呢?”
“大先生想来是在路上。”
“怎么会有这种事?”螺蛳太太自语似的说,“宓本常这样子能干的人,怎么会撑不住,弄成这种局面?”
谢云青无以为答,只搓着手说:“事情很麻烦,想都想不到的。”
螺蛳太太蓦地打了个寒噤,力持平静地问:“北京不晓得怎么样?”
“天津当然也有消息了,北京要晚一天才晓得。”谢云青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明天这个关,只怕很难过。”
螺蛳太太陡觉双肩有股无可比拟的巨大压力,何止千斤之重?她想摆脱这股压力,但却不敢,因为这副无形中的千斤重担,如果她挑不起来,会伤及全家,而要想挑起来,且不说力有未逮,只一动念,便已气馁,可是紧接着便是伤及全家,特别是伤及胡雪岩的信誉,因而只有咬紧牙关,全力撑持着。
“大先生在路上。”她说,“老太太不敢惊动,另外一位太太是拿不出主意的,谢先生,你有什么好主意?”
谢云青原是来讨主意的,听得这话,只有苦笑。他倒是有个主意,却不敢说出来,沉默了一会,依旧是螺蛳太太开口。
“谢先生,照你看,明天一定会挤兑?”
“是的。”
“大概要多少银子才能应付?”
“这很难说。”谢云青说,“阜康开出去的票子,光是我这里就有一百四十多万,存款就更加多了。”
“那么钱庄里现银有多少呢?”
“四十万上下。”
螺蛳太太考虑又考虑之后说:“有四十万现银,我想撑一两天总撑得住,那时候大先生已经回来了。”
谢云青心想,照此光景,就胡雪岩回来了,也不见得有办法,否则上海的阜康何至于“上排门”,不过这话不便直说,他只问道:“万一撑不住呢?”
这话如能答得圆满,根本就不必谢云青夤夜求见女东家,“谢先生,”螺蛳太太反问道,“你说,万一撑不住会怎么样?”
“会出事,会伤人。”谢云青说,“譬如说,早来的、手长的,先把现银提走了,后来的一落空,四太太你倒设身处地想一想,心里火不火?”
这是个不必回答的疑问,螺蛳太太只说:“请你说下去。”
“做事情最怕犯众怒,一犯众怒,官府都弹压不住,钱庄打得粉碎不说,只怕还会到府上来吵,吵成什么样子,就难说了。”
螺蛳太太悚然而惊,勉强定一定心,从头细想了一遍说:“犯众怒是因为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不公平了!索性大家都没有,倒也是一种公平。谢先生,你想呢?”
“四太太,”谢云青平静地说,“你想通了。”
“好!”螺蛳太太觉得这副千斤重担,眼前算是挑得起来了,“明天不开门,不过要对客户有个交代。”
“当然,只说暂时歇业,请客户不必惊慌。”
“意思是这个意思,话总要说得婉转。”
“我明白。”谢云青又说,“听说四太太同德藩台的内眷常有往来的?”
德藩台是指浙江藩司德馨,字晓峰,此人在旗,与胡雪岩的交情很深,所以两家内眷,常有往还。螺蛳太太跟德馨的一个宠妾且是“拜把子”的姐妹。
“不错。”螺蛳太太问,“怎么样?”
“明天一早,请四太太到藩台衙门去一趟,最好能见着德藩台,当面托一托他,有官府出面来维持,就比较容易过关了。”
“好的,我去。”螺蛳太太问,“还有什么应该想到,马上要做的?”
一直萦绕在螺蛳太太心头的一个难题是:这样一个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大变化,要不要跟大太太说?
胡家中门以内是“一国三公”的局面,凡事名义上是老太太主持,好比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大太太仿佛恭亲王,螺蛳太太就像前两年去世的沈桂芬。曾经有个姓吴的翰林,写过一首诗,题目叫做“小姑叹”,将由山西巡抚内调入军机的沈桂芬,比作归宁的小姑,深得母欢,以致当家的媳妇,大权旁落,一切家务都由小姑秉承母命而行。如果说天下是满洲人的天下,作为满洲人的沈桂芬,确似归宁或者居孀的姑奶奶,越俎代庖在娘家主持家务。胡家的情形最相像的一点是,老太太喜欢螺蛳太太,就像慈禧太后宠信沈桂芬那样,每天“上朝”--一早在胡老太太那里商量这天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办,通常都是螺蛳太太先提出来,胡老太太认可,或者胡老太太问到,螺蛳太太提出意见来商量,往往言听计从,决定之后才由胡老太太看着大太太问一句:“你看呢?”有时甚至连这句话都不问。
但是,真正为难的事是不问胡老太太的,尤其是坏消息,更要瞒住。螺蛳太太的做法是,能作主就作主了,不能作主问胡雪岩。倘或胡雪岩不在而必要作主,这件事又多少有责任,或许会受埋怨时,螺蛳太太就会跟大太太去商量,这样做并不是希望大太太会有什么好办法拿出来,而是要她分担责任。
不过这晚上谢云青来谈的这件事是太大了,情形也太坏了,胡老太太如果知道了,会受惊吓,即令是大太太,只怕也会急出病来。但如不告诉她,自己单独作了决定,这个责任实在担不起,告诉她呢,不能不考虑后果--谢云青说得不错,如今要把局势稳住,自己先不能乱,外面谣言满天飞都还不要紧,倘由胡家的人说一句撑不下去的话,那就一败涂地,无药可救了。
“太太!”
螺蛳太太微微一惊,抬眼看去,是大丫头阿云站在门口,她如今代替了瑞香的地位,成为螺蛳太太最信任的心腹,此时穿一件玫瑰紫软缎小套夹,揉一揉惺忪的倦眼,顿时面露惊讶之色。
“太太没有睡过?”
“嗯!”螺蛳太太说,“倒杯茶我喝。”
阿云去倒了茶,一面递,一面说:“红儿告诉我,谢先生半夜里来见太太--”
“不要多问。”螺蛳太太略有些不耐烦地挥着手。
就这时更锣又响,晨钟亦动,阿云回头望了一眼,失惊地说:“五点钟了,太太再不睡,天就要亮了。今天‘大冰太太’来吃第十三只鸡,老太太特为关照,要太太也陪,再不睡一会,精神怎么够?”
杭州的官宦人家称媒人为“大冰老爷”,女媒便是“大冰太太”,作媒叫做“吃十三只半鸡”,因为按照六礼的程序,自议婚到嫁娶,媒人往还于乾坤两宅,须十三趟之多,每来应以盛馔相飨,至少也要杀鸡款待,而笑媒人贪嘴,花轿出发以前,还要来扰一顿,不过匆匆忙忙只来得及吃半只鸡,因而谓之为“吃十三只半鸡”。这天是胡三小姐的媒人,来谈最后的细节,下一趟来便是十一月初五花轿到门之前吃半只鸡的时候了。
螺蛳太太没有接她的话,只叹口气说:“三小姐也命苦。”紧接着又说,“你到梦香楼去看看,那边太太醒了没有?如果醒了,说我要去看她。”
“此刻?”
“当然是此刻。”螺蛳太太有些发怒,“你今天早上怎么了?话都听不清楚!”
阿云不敢做声,悄悄地走了,大太太住的梦香楼很有一段路,所以直到螺蛳太太喝完一杯热茶,阿云方始回来,后面跟着大太太的心腹丫头阿兰。
“梦香楼太太正好醒了,叫我到床前问:啥事情?我说:不清楚。她问:是不是急事?我说:这时候要谈,想来是急事。她就叫阿兰跟了我来问太太。”
螺蛳太太虽知大太太的性情一向迟缓,但又何至于到此还分不出轻重,只好叹口气将阿兰唤了进来说:“你回去跟太太说,一定要当面谈,我马上去看她。”
一起到了梦香楼,大太太已经起床,正在吸一天五次第一次水烟。“你倒真早!”她说,“而且打扮好了。”
“我一夜没有睡。”
大太太将已燃着的纸煤吹熄,抬眼问道:“为啥?”
螺蛳太太不即回答,回头看了看说:“阿兰,你们都下楼去,不叫不要上来。”
阿兰愣了一下,将在屋子里收拾床铺里衣服的三个丫头都带了出去,顺手关上房门。
螺蛳太太却直到楼梯上没有声响了,方始开口:“谢云青半夜里上门要看我。他收到上海的电报,阜康‘上排门了’。”
大太太一时没有听懂,心想上排门打烊,不见得要打电报来,念头尚未转完,蓦地省悟,“你说阜康倒了?”她问。
“下半天的事,现在宓本常人面不见。”
“老爷呢?”
“在路上。”
“那一定是没有倒以前走的。有他在,不会倒。”大太太说了这一句,重又吹燃纸煤,“呼噜噜、呼噜噜”地,水烟吸个不停。
螺蛳太太心里奇怪,想不到她真沉得住气,看起来倒是应该跟她讨主意了,“太太,”她问,“谢云青来问,明天要不要卸排门?”说到这里,她停下来等候大太太的反应。
有“上排门”这句话在先,“卸排门”当然就是开门做生意的意思,大太太反问一句:“是不是怕一卸排门就上不上了?”
“当然。”
“那么你看呢?”
“我看与其让人家逼倒,还不如自己倒。不是,不是!”螺蛳太太急忙更正,“暂停营业,等老爷回来再说。”
“也只好这样子。老爷不晓得啥辰光到?”
“算起来明天下半天总可以到了。”
“到底是明天,还是今天?”
“喔,我说错了,应该是今天。”
“今天!”大太太惋惜地说,“就差今天这一天。”
她的意思是,胡雪岩如能早到一天,必可安渡难关,而螺蛳太太却没有这样的信心。到底是结发夫妻,对丈夫这样信任得过,可是没有用!她心里在说,要应付难关,只怕你还差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