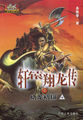我瞪了乐遥一眼,冷不丁地做了一个鬼脸,乐遥没料到,傻愣了几秒钟,知道我是惹不起的主儿,便扭头望向别处。怪草却突发奇想地说:“哎,不如我们收留它吧?”
“啊?”我被怪草心血来潮的建议惊了一下,停住了轮椅,低头问怪草,“你说真的还是假的?你要收留它?”
谁知道这流浪猫也像是通了人性,竟然也跟着我们停了下来,在怪草的脚边喵喵直叫,逗得怪草开心地叫道:“你们看,你们看,它还真听得懂人话呢!”
显然乐遥和怪草同属一国,他们俩一个弯腰,一个蹲下来,在路边就逗起了一身是泥的流浪猫。我用余光瞟了他们几眼,感觉眼前这画面真像是一家人在享受天伦之乐,乐遥用手挠了挠流浪猫,它在地上娇气地绕地打着滚,而怪草则咯咯笑个不停,我显然成了不合群的异类。
怪草用手肘蹭蹭我的胳膊,说:“嗡嗡,你也来玩玩嘛,你看它多可爱啊!”说着,不知什么时候被她抱起的流浪猫被她举到了我面前,我啊地大叫了一声,吓得往后弹跳了好几步。那猫也受惊不浅,逃亡似的从怪草的手里挣脱开,跳到了地上,乐遥忙靠过去热心地安抚它。
怪草问我:“嗡嗡,你怎么了啊?这猫咪很乖的,不会伤害人的!”
我吓出一身冷汗,支支吾吾地说:“我……我……我怕猫……”
“啊?”怪草和乐遥同时像看怪物一样打量着我。乐遥说:“你要说你害怕老鼠,我还能理解,你说你害怕猫,要不要这么夸张?”
我激动地叫了起来:“喂!你知道什么呀!我有阴影!我小时候被猫咬过!”
“好吧,当我没说过话。”乐遥无奈地耸了耸肩膀,抱起流浪猫,回到怪草身边。即便是在我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收留了这只流浪猫,两人自动将我排除在外,开始剪刀石头布地决定谁把猫咪带回家。
就这样,乐遥成了流浪猫的新主人。
准确地说,他成了奔奔的主人。
没错,他们连猫的名字都想好了,奔奔。
他们俩一路上欢声笑语,因为奔奔由怪草抱着,我连稍微接近它都觉得头皮发麻,推轮椅的责任就落在了乐遥身上,最后,我倒成了他们的保镖。
那一刻,好像以前我们斗嘴的某一刻,我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生气郁闷这个点上,会暂时忘记怪草的病情,以及她失去的那一截小腿。我会在心里闷闷地唠叨他们俩的小八卦与我联想的小暧昧,就像曾经怪草在关键时候袒护乐遥,我也会如此愤愤。
你们那么默契,那么默契怎么不去结婚?
当然,这些吐槽仅限于心里活动而已。
热闹的节日气氛随着春节的逼近而更加浓郁,怪草的爸爸妈妈在除夕夜前一天,为了保险起见,带怪草回医院输了一次液,可是,谁也没料到,这一去却带来一个坏消息。怪草回家之后,便一直窝在被窝中,看上去仿佛只是闭着眼睛在睡觉,但眼珠却在眼皮底下不断滚动,时不时还有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打湿了枕头。
她连续好几天都拒绝与人交流,她妈妈没有办法才在正月初三给我打了电话,于是,我向老爸老妈请假,告诉他们不能随同去亲戚家拜年了,然后,直奔怪草家。
一路上满是年味,孩子们在家门口放鞭炮、玩礼花,怪草家也来了亲戚拜年,客厅里还一片喜气,到了怪草的房间却是另一种极端。静悄悄、无声无息的,怪草枕着靠背,默默地望向窗外,脸上几乎没有血色。
即使面对这样的怪草,我还是告诉自己一定要打起精神来,于是,我一脸兴奋地跑到怪草的床前,笑嘻嘻地涎着脸道:“怪草,新年好哦!快看我给你带了什么新年礼物!”我抱着一瓶子千纸鹤,在怪草面前晃了晃。
怪草却没有像以前那样也同样以笑脸迎人,她缓缓地把脸侧向我,轻声说:“嗡嗡,舒亮他死了。”
我手里的玻璃瓶啪的一声落在了地上,死亡第一次离我这么近,我不如怪草那么冷静,眼泪瞬间便像盐汽水,在摇晃之后,被人拧开了瓶盖,溅了出来。
半个月前,我才在重症病房门口看过他……
两三个月前,我和怪草举行阅读会的时候,他还在我们面前耍宝……
差不多半年前,第一次见到他和怪草在一起的时候,还在心里讨厌这个人的存在……
现在,他就死了吗?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很难想象我们所说的生命的脆弱,真的是如此不堪一击。
怪草面无表情地盯着前方雪白的墙壁:“嗡嗡,你还记得我出院之后的第二天,就下雪了吗?那时候,我们还高高兴兴地围着暖气,看着窗外白茫茫的一片……那是冬天的第一场雪,下得那么安静,舒亮就是在那一天去世的……你说,那飘下来的雪花中,有没有夹着舒亮的羽毛呢?他……应该是化做天使飞走的吧……如果天使必须借助雪花才能掩饰自己飞向天空的场面,我真希望这个世界从此不再下雪了,这样是不是代表好人就永远不会死了呢……”
我捂着脸,尽量抑制住哭声,低声地啜泣着,可眼泪还是控制不住。我低下头,盯着落在地上的千纸鹤,每一只千纸鹤都像在动,它们挥动着翅膀,好似只要打开窗户,便会随时飞走。
我与舒亮并没有太多交集,然而,为他留下的这些眼泪的背后,是对生命的敬畏与惶恐。我害怕,害怕有一天怪草也会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我,离开这个世界,只要一想到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再也见不到怪草了,我的心便充满惶恐,只有眼泪才能暂且填满这种惶恐之后的空虚与无助。
这一天,怪草一个人断断续续地说了很多,说的全是她曾经的病友们的故事,很多人的名字她都没有提起,只是用字母来表示。
她说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她曾有过一个十分要好的病友A,那时候怪草还没有接受化疗,是整个病房里第二个依然有头发的人。与那个女生一样,这里面好像有一种互相庆幸的情绪在捣乱。
“和我稀稀疏疏的看起来营养不良的黄头发比起来,她的头发真漂亮,垂直的黑发到达腰际,黑得发亮。我还记得在她做完手术的那天晚上……她因过了麻药时效而痛苦地呻吟着,我悄悄走到她的床边,把自己的一只耳机塞进了她的耳朵里,我们俩躺在同一张床上,听着同一首歌。”
直到电池耗尽,在黑夜中发亮的眼眸,仍注视着天花板。
A说,做完手术之后就是化疗,这样就意味着保不住头发了,她舍不得。
说到这里,她扭过头局促地笑了,说她死也不会做化疗,一定会在头发掉光之前离开这里。
当时怪草以为这只是玩笑,可是几天之后,她真的失踪了。从那之后,没有再出现。
“失落了一阵后,偶然听到了护士们聊天。原来,在A生病之前,有一家知名的广告公司找过她,想请她拍洗发水广告……我一下子理解了她的离开,曾经有过光芒的星星,怎么接受得了瞬间变成流星的命运?”
另一个叫做B的病友,是个高挑美丽的女孩儿。平时睡在靠墙的床位,是个冷美人,不爱说话,总是窝在床上,一言不发。吃药打针,她是最按时按点的那个。可是,她总是很孤单,没有朋友来探望,也没有亲人来照顾。”
清冷的病房在午后寂静得可怕,大家都有午睡的习惯,只有B不睡觉。她的床头放着一个行李箱,没事的时候,她就把里面的东西翻出来重新整理,反反复复,不知疲惫。
“我犹豫了很久,有一天终于鼓起勇气和她说话。我问她,为什么每天都在整理行李。你猜她怎么说?她竟然说,人活着就是随时准备去死,像我这样的人,更是如此。”
想死的人,却努力活着,人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自欺欺人。
几天后她就转院了,被几个全副武装的男护工给抬走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听说检验科的复查结果出来了,她是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无论愿意无否,她都不再属于这里。
“但,我知道她不是那样的人……其实,她也有对生命的渴望。在她的枕头下面,藏着一封磨破了边角的信,是她前男朋友写给她的。她爱他,他也爱她。她骗他要去一个遥远的地方,不知何时才能归来,他却决定等下去。”
B走后,病房里进行了一次全面消毒。医护人员在B的床位边,看到被床单遮掩住的墙皮剥落的白墙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相同的一句话:我要活下去。
多想好好活下去,重新变成一个健康的人,出现在深爱的人面前,告诉他,我们重新开始吧……但是,她也许永远失去了这个资格……而她爱的人,再也等不到她的出现……
怪草的病友C平时很乐观也很搞笑,是整个病房的开心果,她的家人总是以非常幽默的方式陪伴着她、鼓励她。看上去很快乐的一家子,让人以为他们都有一颗彪悍的心。
直到后来亲眼看到了他们的悲痛,怪草去厕所的途中看到她姐姐在走廊尽头,窝在漆黑的角落里大哭,那是她第一次听到绝望的哭声——捂住嘴巴想控制音量,声音却从手指的缝隙间漏出。怪草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只是回到病房,拿了一包纸巾跑出来递给她。
怪草说:“那时候她妈妈还经常在从家乡过来的时候带来很多莲蓬,分给每个床位很多很多,那也是我吃到的最原始的莲子……很苦涩,但很纯朴,我到现在还记得它的味道。”
后来,C的病情就开始恶化得很快,每次化疗之后,反应都非常大。那种穿透耳膜的尖叫声常常直接射入我的心房,大家都默默地走开了,谁也不忍心继续看着这一幕……我觉得当时她的叫声,远远超过了我们所谓的撕心裂肺的号叫……她的家人试图安抚她,但是几乎是徒劳,我们也因此经常没能睡好觉,但是大家并不怪罪她,只是觉得她好可怜。接着没多久,她的家人决定给她办出院手续。病友们还深刻记得她穿好自己的衣服,笑着对大家说:‘我回家吃中药了,吃好了一定回来告诉你们哦’……可是,不久之后,就听护士们说,她回家之后,很快就不行了……
然而,曾经很多次看到C父母站在病区的过道里拮据地掏口袋,讨论医疗费的问题。
不是因为想出院……是没有钱了,实在没有能力支付她的医疗费了。
或许,原本她可以活更久。
“D是个很懂事的孩子,她是朝鲜族人,我们经常叫她教我们韩语,偶尔我还会试图和她用韩语对话。那时候我还跟她说了很多在中的事情,告诉她我喜欢神起,喜欢在中,总有一天,我会到韩国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她说她也想跟我一起去……可是,现在都没有机会了吧。嗡嗡,重新再住院的话,我特意告诉医生护士,千万不要把我再安排到我住过的那个病房,我不是讨厌她们,而是害怕,害怕我再去的时候,她们有的人已经不在了……我截肢之后,有一回在康复室,遇到了以前病房的一个病友,她跟我说,D已经不在了……嗡嗡,你知道吗,你看到过的我的室友们,或许很快就会从这个世上悄无声息地消失。”
生命的终结没有任何信号。
戛然而止的音符,困顿在封锁的生命线上。
静静地倾听,啜泣声渐渐停息,我注视着怪草一张一合的嘴巴,收拢的心口逐渐舒张。我想在怪草的世界里有一块地方,里面住着不止从A到Z这些用英文字母代替的人,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是我接触过的,还有一部分我只能在怪草的口中,找到她们曾经活在这个世上的痕迹。
能够被记住的人,都是幸运的,这样至少活在记忆里的,还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把每一个黎明看做生命的破折号,把每一个黄昏看做生命的分隔符,谁也不知道突然降临的意外会不会给生命画上一个始料未及的句号。
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努力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