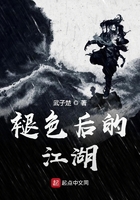1
每天早晨,到了固定时间,离我家不远的巴扎上就有叫卖烤鸡蛋和烤“卡瓦”的吆喝声。然后,混合着烤肉、烤玉米、烤茄子、烤馕的焦香味顺着风飘得好远,就着这一股子香气,我早上吃早饭的时候都忍不住地多吃了好几口。
寻着味儿,我在巴扎上一棵巨大的核桃树下,看见好几个维吾尔族人蹲着站着,手里拿着个烤蛋,嘴里直哈气。摊子上的小铁皮车上有堆炭灰,里面埋着数枚鸡蛋,黄黄白白的,一旁码放着一溜子已烤好的鸡蛋。
烤的鸡蛋为什么会这么香啊,烤蛋的老头笑嘻嘻的,每天都有新词夸他的鸡蛋。可它怎么不会烤爆了,成为“炸蛋”,蛋黄四溅呢?我蹲在摊子旁,琢磨了老半天,原来,烤鸡蛋用的是木柴灰,将鸡蛋放进灼热的柴灰里,要不停翻动,慢慢烤,火候要恰到好处。
终于有一天,我从老爹的衣服口袋里偷了两毛钱,在烤蛋摊子买了两个蛋,笨手笨脚地把蛋壳剥开,烤蛋真的与煮的不同啊,肉脆脆的,一口咬下去,很紧实爽口,蛋黄有股淡淡的焦香。
正吃着,看见我身旁有两个拖着鼻涕的小巴郎,各持一个烤鸡蛋,以蛋的小头相撞,“啪——”光头男孩的蛋壳被碰破了,而蛋壳没破的长脸男孩却得意地跳起来,一只小脏手朝他伸了过去,作为输家的光头男孩将自己的这枚烤鸡蛋递给赢了的长脸男孩。
我站在那里,看了看手里的这枚烤鸡蛋,犹豫了一下,就转身离开了。回到家里,见老爹用了个木托盘把菜端上来,见到他,猛一紧张,手里的烤蛋一下子落了地。
“老爹,你看她这么大人还整天没大没小——”是二弟。他指着我笑着说。笑得袒护,惯使。老爹看了看我,没说话。
晚上,老爹讲了个故事,里面的一首歌好像就是对我的警告:南瓜没有手,南瓜没有脚,可南瓜在追乌龟。显然,乌龟在骗人,它天性不诚实,还说不知道南瓜还有手脚。可我觉得,一定是南瓜从屋顶的藤蔓上掉下来追它,追过草地,追过白水河,它追的样子一定让乌龟惊魂未定。
老爹是不是觉得这首歌更适合我呢?我才冤枉呢。后来,再路过烤鸡蛋的摊子,我总是要小心地看看四周,看看有没有什么球状的东西朝我滚过来,雨点一样地砸向我,在土路上追赶我。
除了去河坝子和巴扎玩,我们这些小孩子还喜欢捉弄一下路人。
那天,一辆拉土豆的车从菜市场路过,土豆堆成了小山一样,把平板车的轮胎压得瘪瘪的。当这辆拉土豆的车从巷口路过,早有一些孩子等在那里了,将铁钩子藏在身后,笑嘻嘻地看着拉车人的身子弓得像一只大虾,等他一脸狐疑地慢慢走过去,身后,大大小小的土豆就落了地。
对于吃煮熟的土豆我是很有经验的。最重要的是不能一边吃土豆一边喝水,这样的话很容易胀肚子,还容易噎着,脖子一挺一挺的,看上去和一只生了气的鸡一样蠢。
可二弟偏偏就和一只生了气的鸡一样蠢。
那天,我站在家门口一副没心没肺的无聊样,吸引住了这一带有名的“二流子”阿布力孜的注意。他从我家门口路过,远远地朝我吹了个口哨,笑嘻嘻地对我说:
“你家里还有石头吗?”
“啥石头?”我傻乎乎地问他。
他咧开嘴笑了:“你装什么装啊。艾山造的假玉石都卖到‘口里’去了,生意好得很。”
艾山?在当地,可是很少有人这么认真地说出二弟的名字。我笑嘻嘻地看着他——艾山?艾山造假玉石?这个“二流子”,这么多年来他不只学会了整天闲逛和小偷小摸,竟然也学会做生意了——造假玉石?
我看着他,小孩子无聊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我讨好地拽了下他的衣角,倒是很有兴趣想听下去他到底还要说什么。
后来我知道了,二弟,他,还有他们,跟着一些外地人在偷偷仿造一种古玉石。
我从前在玉石巴扎上见过的——那是些从死人的墓室里挖出的古玉,一颗颗看起来诡异得很,仿佛每一颗石头上都禁锢着一个会说话的灵魂。
古玉若是真的,色泽好的,比如枣红色,一定是由尸体的死血浸染成的。墓中有石灰侵蚀,玉石表面呈鬼魅的桃花斑,还有褐色、粉色、青色——只要知道根据什么原理而成色,那么就可以大胆地做手脚加工加色了。
它是一个失传的绝技:把新玉做旧。
旧玉新工是一门技艺。
比如,把新玉石放进牛奶里泡,然后在锅里反复蒸煮,玉石就会产生古灰色的旧玉效果。
还有使新玉产生深红色橘皮纹效果的办法。
我记得古好像有一次说过这件事:好像是乾隆年间南方无锡的一个人发明的。这块石头要先混合好多的铁屑一起搅拌,再用烧热的醋浇淋,要一点点地浇,然后埋在湿泥地里数月,才能取出。
这是因为玉为铁锈所蚀,玉的身上会布满深红色的橘皮纹,而且还有土斑灰。
如此,就像块古玉了。如此一变身,就更加地值钱了。
那真是个独门秘方,很像是跟冶炼金属有关。
只是,传闻中的这门技艺相当神秘,一般都是闭门操作,让幼小而深邃的我感到十分稀奇,很想偷师窃技。
可是我是个女孩子,这么小,性情又这么毛糙,怎么会有耐心学成这门手艺?还是算了。
现在是二弟。
后来听古说,外地人还有人发明了一种偏方,就是使用了一种新科技:用微波炉给皮面枯槁的玉石“焗色”,只要控制得当,滋润通透的好玉色足可以假乱真了。
他说自己没见过微波炉,我也没见过,也都只是道听途说。
后来,也就是好多年的一天,我有幸看过一个人用这种方法“焗”坏了的石头,黄黄绿绿的,假假的,显得浮肿。
多年以后,和田的玉石巴扎还有这种包了皮子的石头卖,一堆一堆的,看起来是要论斤的,但是做得比以前还花哨,一个个滚圆饱满,围观的人还是那么多,上当的人还是那么多。看了可以不买,指指点点不要紧,算一算,一颗要不少钱呢,就有些舍不得了。
可一旦拿起来又讲了价,就一定要买走,一点都不许赖。
就在当天,我急匆匆地来到了玉石巴扎上。巴扎上嘈杂,混乱,人潮涌动。
玉石摊子,草药摊子,瓜果摊子——小贩们在人群中窜来窜去。卖干果的人在屋顶上各自拉一块简单的篷布,炎热的阳光从篷布的缝隙中倾洒下来,一股热气在脸上蒸腾。
牲畜摊子上,许多的羊聚集在一起。它们的脖子上系着绳子,主人牵着它们慢慢穿过拥挤的市场。一个衣衫很破的男人蹲在杂货店的门口,顶着脏污的缠头一动不动,仿佛一条立在墙角的旧麻袋。
到处都是人群,黑筒子一样的羊羔皮帽子千般百种地在头上浮动,不时地转变方向,或急或缓,手里捏着,怀里抱着貌似玉石一样的东西,远远地看着路人。你慌他不慌,没钱却有的是时间用来消磨手中的玩意儿。
我在一个又一个的玉石摊子上走动,气氛好像不一样了。但我说不出哪一点不一样。小贩们的叫卖声,还有大大小小的石头的撞击声,在这个几近疯狂的巴扎上,只有这两样东西从来不会沉默。
我在一个包着头巾的邋遢妇女的玉石摊子跟前蹲了下来:她在石头摊子的一旁,正慢条斯理地给一颗红皮石头上“红灯牌”头油。
这些石头大的如拳头,小的如杏核、玉米粒儿,一个个油亮亮的,堆满了她脚下的破毡子,她的脚边还放着一瓶“红灯牌”的头油。这种“红灯牌”的头油古丽家里也有,一瓶要六毛多钱才能买到呢。好几次,我想让老爹买,可他不给,说是我还小呢。
这个妇人低着头,满不在乎地给手中的一块石头“上光”。 她脚下的旧毡子上,凡上过这种“头油”的石头,个个看起来像刚摘下来的果子那样新鲜滋润,让人忍不住猜测它的来历。可她一副很坦荡的样子,倒是很想让人享受这个来历呢。
她见我不走,还盯着看她,就慢慢地把这块“玉石”举在了我的眼前。这颗拳头大的绿石头抹了“头油”后,就像涂了层釉,体积好像大了许多,笨头笨脑的,不过也亮了许多。
我盯着它看,表情一定很专注。
最后,我挑衅似的看着她:“‘假的’,这些石头是假的。”
女人很无邪地笑了,鼻孔里的清鼻涕也一抽一伸的。
按照阿布力孜的指点,我来到玉石巴扎尽头的那个旧车库。
大铁门上的一副铁锁像我初次见它那样悬挂着。
走近一看,老旧的外壳上附着斑驳的漆,轻轻一拉,铁链绞起一阵响动。透过铁门裂隙里泄出来的光,我看见二弟果然在这里。屋子里到处都是水,好像刚下了一场雨,地面上、木桌上湿漉漉的。
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搭起了灶,还找来一些砖和卵石,对称放着,就能架锅了。锅是铁的,旧得不成样子,锅盖和锅都凹进去好几处,盖子都盖不住。他还砍柴,沿着河滩走很远,砍好的梭梭柴码好,长的短的,很干燥,拍上去会有铜的音质。这些柴是他用来烧火的。
烧火干啥 ?熬煮草药。如此,那一小堆原先看上去不起眼的玉石就这样镀上了一抹桃花斑。
桃花朵朵开,实际上不过是药液所化。一个个浑身斑斓,比真的石头还好看。
老爹告诉我,以前在和田这一带,我们那些维吾尔族匠人无论是织地毯还是染土布,都是从矿石里,还有植物中提取老式的天然染料。
用来做染料的品种有很多,有核桃皮、石榴皮、蒲公英,还有和田的戈壁滩上十分常见的黑蜀葵(染红色),以及带颜色的矿石粉。
除了这些,这些当地人还知道,水冬瓜用来染咖啡色、麻粟果染黑色、黄粟皮染红色、水马桑染黄色。
要是想染成黑色的话,家里的黑铁锅刮出来的铁灰也有人敢用。
可是,这些造假的玉石匠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流行用硫化染料代替他们以往一直在用的植物和矿物质染料了。
结果,硫化染料的腐蚀性太强,才又恢复了以往传统的用黑蜀葵(染红色)和本地产的矿石粉来熬煮石头,使其变色。
这些技艺,真是深奥。后来说是二弟跟着外地人学的,我看不像。早在老爹发觉之前,他就知道把染料放入盆内,要放多少水合适,还要与什么样的植物染料混合才能发色,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拌匀,要防止掉色应该如何处理,这些细微的事情必须面面俱到。
还有,染液的温度不能太高,否则染液里的发酵菌就会失效。
用捞沙女人的话说:染液就“死掉”了。
现在透过门缝,我远远地就闻到了一股药腥气,像在水盆里沤了好多天的衣服的味道。
我不能适应,就径直推开门走了进去。二弟被吓了一跳,眼神很是惊异。
我一把掀开墙脚堆放稻草的席子,那事先用植物和矿石粉沤好的染液,在盆子里泛着暗红色的泡沫。
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和田,当时操这种行当的人并不多,二弟算是一个,那他该算是一个艺人了吧。民间艺人。平时对于他是干什么的,当地的人们习惯不问长短。老爹也不问。也许,二弟他自己也忌讳着呢。
好在,用五花八门的方法做旧玉的这些路数和招式还是记得的,做得也像回事,便被他沿用多年谋生。
真假的玉,经他的手,也就无分真假了。
现在,二弟把皮手套摘下,眼睛并不看我,而是看了一眼在墙脚打盹的大狗。又望了望铁锅里煮着的石头,几分钟后,他想站起来,又觉得很吃力,好像眼前的那些石头在围着他旋转。
然后,他倒向车库柴房的稻草堆一侧,昏睡了过去,全然不顾我还在屋子里。肚子还饿着。
二弟在睡觉。在这样冷的天里他仍然光着脚,我可以看到他脚腕的有些地方已裂开了口子,上面还沾了些肮脏的泥巴,但是,这些在他看来是多么地无关紧要。
很快,他发出了熟睡时的鼾声,胸膛起伏着,好像里面充满了温暖的气息。大狗也像是接到了统一的指令一样,贴着他的脚睡着了,喉咙里不时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不知过了多久,我望见靠窗户的墙角有一个灰白色的蜘蛛网,随风一荡一荡的,便有些奇怪:它怎么会动呢?
可能是我弄出的响声惊扰了二弟,他“霍”地一下就坐了起来,瞪着眼睛看了看周围:周围的一切都是熟悉的,桌子,椅子,许久没擦拭的窗户,熟睡的大狗,还有身子底下花纹不明的羊毛毡上留有的他的体温。
然后,他看了看我,重又倒在了毛毡子上。
就像是天突然黑了一样,他,还有大狗——他们一起进入了睡眠的时间。睡着的也许是外表上的他,但没人看见,其实他睡得和内心里的他一样地沉。因为非凡的业绩他精疲力竭了,在此刻终于成为了同一个人。
他和大狗挤在一起的样子是多么地和谐,让我不由得相信,他丝毫没有被冬天的寒冷所伤害。
我使劲地咽了一口唾沫,小心翼翼地退出了屋子。
2
春天来了,从墙头探出头来的总是一簇杏花。
杏花最先开放。杏花青白色肥厚的花瓣散发出的清香,一阵又一阵。
然后是桃花,槐花,最后是枣花。
枣树的淡黄色的花柄只有黄豆大,小而坚硬,在月光下泛着一种纸质的光泽。但它的枝叶散发出一股湿漉漉的气味儿,在整个院落的角落里浮动如影。一股浓稠的异香从烤肉的焦香、沙石的泥腥气中分离出来,像雾一样地漫延在整个院落,又在道路的两旁逶迤而行。
每个睡着和没睡着的人都闻到了这股异香,层层叠叠,饱满而深厚。
在这样好闻的味道中度过的日夜,心里也忍不住对那些冒冒失失的外地人充满了一种善意。
然后是夏天。
夏天的早晨,如果没有雨的话,我一般很早就出门去,到河坝子的树林子里去给老爹搂一捆打好的桑树枝。
夏天是个发洪水的季节,听大人们说从今年初开始,就要沿着白水河修筑大坝了,河坝子上每天都在招人。他们都是些民工。身板都很健壮,行走在晨光中的河滩上,脚下的沙子湿而软。怪不得这些日子来,河滩上那些小孩子都一个个地不见了,替换成了大人。那些孩子,好像是经历了一个夏天之后,他们突然长大。他们每天都聚在一起,一堆一堆的。有男人也有女人,个个都显得活计很多的样子。
还有一些没被雇用上的人每天也来到这里,眼神和身体都缩在了一起,等待着下一个好运。
河坝子上,几个管事的人坐在树底下一顶绿色的帆布帐篷里打牌,让胖子库尔班监督那些民工干活。二弟和库尔班很熟,以前总是在一起“打瓜”,就叫了二弟白天给他照看下这些人,说好了照看一天给他三块钱。
二弟答应了。
二弟模仿着库尔班,在河坝子上背着手走来走去,他最爱去的地方是几个捞沙的妇女那儿,没几日,他就跟她们谈笑自如了。
别看二弟他在屋子里头闷,不说话,可他到了外边,他很善于说笑话的,有时说的笑话很深入,让做活的妇女们满脸通红,好几次把铲出来的沙子倒在了自己的脚上。特别是遇到顺眼的女人,他还给她拿来馕饼。看到馕饼,这些女人就什么也不顾了,一边嚼着饼,喘着气,一边看着他,嘴边流露出一抹讨好的笑意。
有一个捞沙女人引起了二弟的注意。她瘦瘦的,肩头很尖,穿着破旧的土布衣服,那颜色斑驳得很,一看,就是用野萝卜花,沙蒜叶子染出来的。可现在早都没人染了。
她的一双灰黄的眼睛平静地亮着,神情比别人都成熟,像个过来人似的,冷冷地看着他们在一旁调笑。
她刚来这里捞沙才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