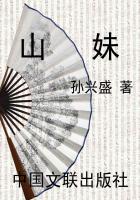他们的学校建在山上,每日从寝室往教室赶,都要经过一大段倾角超过六十度的陡坡。他每天都来接她,一起费力攀爬陡坡,最初,即使她摔倒了,鼻青脸肿,他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也依旧鼓励她继续前行,从不帮她。她是多么好强的女子,咬咬牙,竟然也坚持下来。慢慢地,他只需轻轻扶着她的胳膊,她就可以顺利走完陡坡。他们的爱,也在这一日日的攀爬中,渐渐生根、发芽、开花。
很久之后,她在一次轻松走完那段陡坡时,突然娇嗔地问身旁的他:“你当初为什么那么傻,送康乃馨给我?”他稳稳地答:“不是傻。我是故意把送母亲的花送给你,只因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所以,即使我们两个只有三只脚,也要互相扶持前行。不能倒下!”
佩特斯底魔咒
叶明初见何浅浅,是2003年春天。北京的春天,有猛烈的风。叶明照例在工人体育馆外的广场上闲逛,却很快发现今天有些不一样:广场上的人特别多,有的举着荧光棒,有的拿着大幅的明星海报,海报上的女人冷漠高傲地看着这个世界……演唱会很快就要在这里举行了。
何浅浅就是这时撞入叶明的视线的。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奔跑得太快,扑倒在广场的空地上,叶明连忙走上去扶起她,没想到却被另一双手抢了先,那是何浅浅的手。
被扶起的小女孩开心地笑了,连一点擦伤都没有,女孩的父母赶来对叶明和何浅浅道谢。叶明摆手说不用了,何浅浅却挥舞着手里的一大把荧光棒,问小女孩的父母要不要买一枝,女孩的父母立刻掏钱买了一枝。
何浅浅向叶明笑了笑,说我叫何浅浅,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叶明常常在广场散步,遇到卖荧光棒的何浅浅,就停下来聊一会儿天。直到后来,熟悉到不再称呼彼此的名字,只说“哎,你……”的时候。叶明问何浅浅为什么要那么势利,“难道扶起了别人的小孩就要人家买自己的荧光棒吗?”
何浅浅反驳说:“难道你看不出他们也要听演唱会吗?有一枝荧光棒会更有气氛。”说完她笑意盈盈地看着叶明。
“不管什么原因。你也不能这么做。”叶明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一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叶明去了何浅浅的家。
她的家在海淀区的平房里,是政府三令五申要拆迁的对象。不到40平方米的小屋,何浅浅和年迈却俏皮的祖母住在一起。看到叶明在屋外踌躇,何浅浅就笑了,问他是不是嫌自己的家太简陋了。叶明连忙说怎么会呢?我住的地方,比你的家差多了。叶明租住的小屋在市郊小小的村庄里,那里聚集了很多外地到北京复习考研的大学生。
何浅浅将叶明让进了屋,在小小的厨房忙碌起来,做了一桌子的菜:炒云豆,红烧肉……80岁的祖母依然硬朗,吸着鼻子说:“很香。”叶明说是啊是啊。老祖母又眨眨眼睛说我的孙女儿很能干,是不是?
饭菜很快端上了桌,三个人围在一起吃得津津有味,叶明的胃口在香味里张大了。多长时间,他没有吃过这样可口的饭菜了,在市郊那个所谓的状元村里,他的饭常常是饼干和泡面。不曾想,就遇到了浅浅,有了家的温暖感觉。
街头的树叶从浓绿转到微黄,仿佛只是一眨眼的事情。
秋天来了。浅浅一遍遍走在市区到状元村的路上,给叶明送去好吃的东西,帮叶明洗衣服,抄笔记。她和叶明仍旧是哥们儿,她常常想,怎么会这样呢?她明明是喜欢叶明的,她对他的爱很简单,而又难以动摇。
她不喜欢念书,只念了职高;而他却喜欢,拼了命地要考研。在她眼里,那跟收藏邮票或火花一样,是闹着玩儿的。但他喜欢,那就由着他好啦。哪怕以后真的在一起,是她养着他。
二
没想到叶明真的考上了研究生。那晚,满天的星星快乐地眨着眼睛,叶明打来电话,“浅浅我考上研究生了!”
浅浅的心就像掉进了海底,浮沉不定,一半欢喜,一半忧伤。她想状元村真是出状元啊。但是,自己和他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了吧!何况在他眼里,自己不过是他的哥们儿。
那天以后,叶明进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偶尔,他会给浅浅打电话,问她和祖母的生活,也会说起自己。他说老板要求很严的,浅浅脱口而出:你不是学生吗?怎么要看老板的脸色呢?叶明宽容地笑了。
浅浅知道自己闹了笑话,就更自卑了。那晚的月亮,特别亮,特别圆。祖母的手抚摸着浅浅的脸,什么也没有说,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夜深了。祖母问浅浅你睡了吗?祖母继续说话,仿佛是自言自语,她说在她年轻的时候,听说过一个佩特斯底的咒语,如果偷偷地爱上一个人,那么就买一块表,在他熟睡时戴在他的手腕上,告诉他你十分十分爱他。那样,他也会爱上你……第二天,浅浅起得很早。她在中粮广场旁边的钟表柜台前徘徊又徘徊,那些表闪烁着,像天边最美最亮的星星。浅浅挑了一只式样简单的男式表,请售货员很认真地包起来。表很贵,浅浅要卖很多荧光棒才能赚回来,但是她不在乎。她把那表在手腕上比画着,粗粗的表带就衬得她的手腕更纤细了,然后想象着这块表戴在叶明手腕上的样子。
三
然而,那个魔咒到底有没有用呢?叶明很忙,很少给浅浅打电话,后来,浅浅住的平房拆迁了,电话号码也改了,她没有告诉叶明。
好几次,浅浅偷偷到叶明的学校,守在研究生宿舍楼下,远远地,看到叶明回来了,心扑通扑通地跳,竟然看到他的身边有另一个女孩子。女孩不美,但有浓浓的书卷气,淡定从容。浅浅躲在研究生楼旁,突然有想流泪的感觉。她想起最后一次去状元村看望叶明时,叶明收拾东西累了,趴在桌上睡着了,自己明明是把那块表戴在他的手腕上,说出了对他的爱的啊。
祖母的咒语一点都不灵。浅浅想,不知不觉,她的眼泪流下来了。
那天以后,她再没有去过学校。再后来,在祖母的鼓励下,浅浅不再卖荧光棒了,她读书去了,还参加了成人自考。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两年后,浅浅拿到了管理本科文凭,不再是体育馆旁卖荧光棒的小妹,而是一间民营公司的办公室职员了。
她不再穿那些乱七八糟的休闲服,而是开始穿一些美丽的套装了,偶尔,她还会到体育馆附近散步,因为那是她和叶明第一次遇见的地方。
常常,她会想自己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呢?是因为她依然喜欢叶明吗?她不知道答案,只知道成人大学里,公司里,追她的男孩子很多,但他们都走不进她的心。也许,人长大了,就变得更固执了。
却没想到会再见叶明。公司想找一位法律顾问,有人建议到大学里找一位在读研究生,这样可以降低成本。浅浅主动要求去大学找人,她明明知道叶明早已经毕业了,但她想到他读过的大学看一看,看看那个埋葬了她爱情的地方。
大学里人来人往。浅浅一路走,一路望,远远地,就看到了研究生宿舍楼,爱情真的是会在心底打下烙印的,她这样想着。
小小的研究生办公室里,一位女老师接待了他们,一切进行得顺利。浅浅看着窗外的梧桐发呆。这时候一个男子走进来了,声音那么熟悉,竟然就是叶明。
四
他们又遇见了。叶明毕业后留校当了辅导员。
阳光照进来,窗户开着,有微微的风,吹着他们各自的面颊。他们谈话,隔着办公室小小的茶几,身体微曲。
浅浅以为自己会流泪,但是她没有,心里泛起淡淡的酸楚,淡淡的感动。他们说着这三年各自的生活。
叶明偷偷地注视浅浅,她24岁了,俏皮的表情不见了,笑容淡定,有温暖的光。
浅浅眼前的叶明,更高,更稳重,适度的幽默,让人如沐春风。
浅浅跟随同事离开时,叶明叫住了她,有点紧张地低声问她:“你有男朋友了吗?”浅浅说没有。叶明笑了。“我也一直是一个人。下个礼拜,我去看你和祖母吧!”
叶明和浅浅便恋爱了,在浅浅家的小屋里。偶尔,叶明还会带浅浅到他们相识的体育馆听演唱会,浅浅想,祖母的咒语原来是很灵验的啊!
后来,叶明向浅浅求婚,他告诉浅浅,自从浅浅存心失踪后,他就发现了自己爱她,并且没有停止过寻找浅浅和祖母。他说那个女同学,是偶然走到一起的。还说,浅浅把手表戴在自己手腕上时,他就醒了,他听见了她说的话。
浅浅呆住了。祖母在一旁偷偷地笑,其实哪有什么佩特斯底的魔咒呢?其实,佩特斯底魔咒的真正意思是:年轻的时候,如果喜欢上一个人,请一定要告诉他,哪怕是自言自语呢,他会听见的。
爱是生命中最美好的相逢
她认识他,是在一次朋友的茶聚上。缘分就这样在不经意间伴着袅袅茶香来到她的身边。他让她觉得每一天的生活充满了鸟语花香。
但,或许,走得最快的是最美的时光。有一天,她为他收拾杂乱的房间,发现了一件东西:
印有他和一个女孩子名字的钢笔。是放在他书桌的一个抽屉里,用一个很漂亮的锦盒装着。他说,那是初恋女友的东西,他和前女友已经没有了任何联系,但他只是保留着想做个纪念,没有其他的意思。
她不能接受他的解释,她说:“你为什么不扔了它?证明你余情未了,那么,我在你心中是什么位置呢?”
他微叹,说:“很重要的位置。”她点头,不再和他争吵。可是,她很想他把那支钢笔扔了,但他没有这样做。她的心里,从此插了一根刺,恋爱越往深处走,那根刺就插得她越疼,心里带着这根刺,让她和他的小摩擦便越多,最后一次,所有的小摩擦成为大摩擦,他们分了手。没多久,他申请调往单位在外省的办事处工作,临走前,他托人送了一个礼物给她,是一块很漂亮的玉佩,用红色的首饰盒装着。她想分手了,还要他的礼物有啥用呢?但里面的一张小纸条让她留下了它:“让它为我们曾经有过的爱做个纪念吧!”
那一年,她21岁,他22岁,他是她的初恋。后来,他渐渐是她身后的风景,而那只玉佩,她一直把它放到抽屉里。再后来,她结了婚,丈夫比她大8岁,对她体贴周到,是一个能言善语的男人,她和丈夫相亲相爱着。而他,自两人分手后一直没有再联系。婚后一年多,有一天,她和丈夫回娘家吃晚饭,顺便整理自己在娘家的旧物,发现了他送的那只玉佩。丈夫说多好的一块玉佩,怎么从来没见你戴过?她微笑不语。
聪明的丈夫猜到了,笑着对她说:“以前我和大学时的女友分手时,她也送过东西给我。”
她惊讶,问为何从来未见,还有,为何她要送。丈夫回答:“在乡下老家呢,你当然没见过。”顿了顿,丈夫又很认真地说:“爱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相逢,所以,她送了,我就收藏了。但这不会影响到我爱你!”
她想起当年她在他房间里看见的那支钢笔,还有那些青涩的初恋岁月,她才明白了他为何会保留那支钢笔。
若你如她,看见爱人仍保留着过往爱情的纪念品,请理解爱人的心:保留它,并不是爱人的心对你不忠诚,而是因为,爱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相逢,它值得我们去收藏。
做我女朋友好吗?
天大的爱
在我们年少的时候,爱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天大的事情事关勇敢。
我对许诺轻说,你敢从二楼上跳下去,我就答应做你女朋友。许诺轻翻身,站到栏杆之外,一群群的人围过来兴奋如观看马戏盛会。许诺轻看着我问,要是我残废了你可不能不要我啊!我点头。
讲情
他没跳。变成一个孬种和笑谈。我希望他能够跳下去,最好有点儿小残废,这样就不必每天等在学校门口,等着沉默不语的我经过,然后后面跟着几个神经兮兮的看热闹的男生。他带头摸我的头发,眼神邪恶,手掌却有汗水。我闪躲,他拉扯不休。去死去死去死,我在心里默念,却不敢惹他。他不止骚扰我一个女生,他沿路骚扰许多女生。但这些女生都跟我一样,并不敢当面坚定地反抗。
有人报告给老师,许诺轻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班主任说,你这是耍流氓,现在是我教训你,以后你就等着到监狱里被别人教训吧。
等到所有人都放学以后,许诺轻还没有被允许离开那里。我犹豫了一下,经过他面前的时候,多说了一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说话的语调那么老气横秋,许诺轻笑了。这发生在1997年的年底。
很快,他就又开始跟着我。
日月星辰风雨潮
1998年的秋天,他直直地看着我。他眼睛里大概有炸雷,一颗一颗丢过来,炸得人心凌乱。其实他挺帅的,我知道就因为这个原因他才骚扰了我那么久,肆无忌惮。
许诺轻呆滞了一下,然后,他忽然大喊:日月在上,天地为证!我就是喜欢你!做我的女朋友好吗?好耳熟的台词,难道男生也看琼瑶剧吗?
我被他烦得要疯了,然后,我对他说了一句话,他愣住,很多人在看他的反应。
跳楼,还是不跳?他没有跳。
1999年我高一,是全市最好的那所重点高中。澳门回归那天,我又看见了许诺轻。他被两个中年男人带着。一个很瘦,和他面目相似。一个很胖,是高中的教导主任。
许诺轻的眼睛似乎在搜寻什么。没多久,我听见许诺轻和那两个大叔说:就这个班吧!他的眼睛跳开众人,降落伞一样直接落到我的身上。我哀叹一声。关于他的家事,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在本地担任教育局副局长的爸爸,还有一个在本校担任教导主任的叔叔。
就算他初中读得再烂再不争气,一样能够来读最好的重点高中。我们两个人,居然又回到一间教室。
两个人
我们已经各自长大了两岁,许诺轻在下课后,凑过来,对我伸出右手:“你好啊,好久不见。”
我老气横秋地说:“大家都长大了,我以后是想认真念大学,现在得用功,请你不要打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