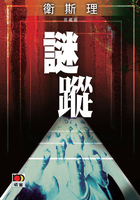保尔用尽全力纵身一跳,用一只手抓住木板的顶端,爬上了栅栏,翻身溜进花园。他回头还看了看那树群后面隐约可见的住宅,便向木凉亭走去。可是凉亭的四面没有任何遮挡物;如果在夏天还有野葡萄藤缠绕遮掩,可是在现在一片光光的。
他正想要重回到栅栏那边去,但已经太晚了:在他身后早已经传来了疯狂的狗吠声。一条大狗早已穿过那铺满落叶的小道向他冲了过来,狗的叫声在整个花园回荡。
保尔做好了全部自卫的准备。大狗扑了上来,被保尔一脚给踢了几下。但这条大狗却还要向前冲。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样下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所幸,传来了保尔熟悉的、银铃般的呦叫声:
“回来,特列佐尔!”冬妮亚在小路上匆匆忙忙地奔来,她抓住特列佐尔颈上的皮带圈拉开狗,对靠在栅栏旁的保尔说:“天啊,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是怎么进来的?你知道吗?你这样是很容易被狗咬伤的,要不是我……”突然,她看着他不说了,两眼睁得圆圆的,他怎么那么像保尔呀!栅栏旁的那个人轻轻地移动了一下,轻轻地问:“怎么,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冬妮亚高兴地叫喊一声,突然一个箭步冲到保尔面前:
“我的上帝,真的是你吗?保夫鲁沙!”然而特列佐尔这次却误会了主人的意思,它以为这是攻击的信号,所以又想向前冲了。“走开!”
特列佐尔费力不讨好地被主人给踢了几脚,心里特别委屈,留下她回庄园了。
冬妮亚紧紧地抓住保尔的双手,问:“你是不是完全自由啦?”“这一切你不都看到了吗?”冬妮亚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内心的狂跳,急促地答道:
“是的,所有的丽莎都对我讲了,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何在这儿,难道他们把你给送了回来吗?”保尔疲倦地回答说:“他们是无意之中错把我放了。现在他们大概又展开对我的搜捕了。我是不知怎得就跑到这儿来的,想在凉亭里休息一下。”接着,好像道歉似的,他又补充说:“我实在太累了。”
怜悯、炽热的柔情,恐惧和惊喜的欢乐一起涌上冬妮亚的心头,她牢牢地抓住了保尔的双手,对他看了又看,说:
“保夫鲁沙我最亲爱的保尔,我的无人可代替的好人儿……我爱你……你听到我的话了吗?……你真是个犟孩子,我不明白那次你为什么非要走呢?现在你既然要到我们家去,到我那儿去,无论如何这次我是不会再让你走了。我这没有人会来的,你要住多长时间都可以。”
保尔不能够答应的,他摇了摇头:“难道你不知道假若我在这儿被搜到,会造成什么后果?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去你家的。”冬妮亚紧抓住保尔的手指,她的睫毛在颤动着,双眼蓄满了泪水:“如果你不去,那你以后就再也不要见我了。现在,阿尔青也不在家,他被押着去开火车了,所有的铁路工人都被征用了。你说你又能去什么地方呢?”
保尔完全明白恋人的担忧,只是害怕自己会牵连了她,其实这些日子以来,他早已身心疲倦了,在心爱的人面前,他真想好好地休息一下,所以他答应了。
当保尔坐在冬妮亚房里时,冬妮亚跑向厨房对妈妈谈话去了:
“亲爱的妈妈,有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诉你。现在,保尔正在我房间里坐着,你还知道他吗?就是我过去的同学。我什么都告诉你:他在这以前,由于放走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水手而被抓进牢里了,现在他跑出来了,但却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她的嗓音颤抖了,“因此我求求妈妈,就让他住在我们这里。”
“是的,大概只需要几天的时间。他现在又累又饿,疲惫极了。好妈妈,如果你十分疼爱我,你就答应我,我恳求你了。”
冬妮亚用充满企盼、热烈的目光看着妈妈。妈妈同样用审视的目光注视着女儿的眼睛:“好的,我不反对。说说你打算如何去做?”冬妮亚的脸上飞上了一朵红彩云,她难为情地、激动地答道:“我可以把他安排在我房间里的沙发上,我们一时不用去惊动爸爸。”冬妮亚的母亲直直地看着女儿的眼睛:“告诉我,孩子,这难道就是你落泪的原因吗?”“是的。”
“可你要明白,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冬妮亚忐忑不安地扯着衬衫的袖子:“是的。可是,倘若他不逃出来,他们会不分事非而把他当作大人枪毙的。”她们谁都不曾再说什么。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的一生饱尝了很多痛苦。她的母亲是个严肃而且又很保守的女人,对她要求很严谨,每时每刻向她灌输虚伪的“礼仪”和“修养”。她的美好的青春都被旧礼教给丧失掉了,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对这永不能忘,因此在对女儿的教育问题上,她抛弃了小市民阶层的很多偏见和不良习气,让女儿自由自在任性发展。尽管如此,她仍十分关心地,有时甚至充满担忧地关注着女儿的成长,并且很有分寸地帮助她解决各种困难。
保尔的来到使冬妮亚的母亲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十分忧虑不安。他被捕过,可很明显冬妮亚又特别爱他,而她根本不了解保尔的情况,这些都令她忧虑不安。
冬妮亚却像主人一样,热情地忙碌了起来:“妈妈,他现在该好好洗个澡了,我现在就去准备,他脏得简直就像个大泥人了,他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洗过澡了。”
所以她忙着烧水,找衣服,然后不容反抗拉住保尔就把他带到了浴室。
“把衣服脱掉。换的衣服在这儿,你的衣服该洗了,你就穿这一套。”她指着椅子说,那儿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色条纹领子的蓝色海军衫和喇叭裤。
保尔好惊奇,他四下望了又望。冬妮亚笑嘻嘻地说:“这是我化装时穿的衣服,它一定合适。好了,你快洗吧,我走了。趁你洗澡,我得去为你准备点吃的了。”说完,她把门带上走了,保尔也立刻脱掉衣服,美美地去洗澡了。一小时以后,女儿、母亲和保尔三人一起围着圆桌在厨房里吃饭。当保尔在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的热情当中完全释怀之后,不觉地三大碗饭下肚了。吃完饭,他们团聚在冬妮亚的房间里。保尔在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的要求下,讲述了自己被捕与在牢里的全部过程。
“那你从今以后又有什么打算呢?”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问。保尔考虑了片刻,说:
“我想见见阿尔青就离开这里了。”
“离开这,你又去哪儿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有可能去乌曼,也有可能去基辅,但我一定得离开这里。”保尔不敢相信,这一切简直太快了:早晨还蹲在牢里,可现在却和冬妮亚坐在一起,身上穿着清清爽爽的衣服,最重要的却是——他已经彻底获得了自由。生活就是这样让人摸不着头脑,它一会充满乌云,一会又星光灿烂。如果不是还有再入狱的危险,他现在真是个幸福的小伙子了。然而,正是现在,别看他已经坐在这宽敞、安静的屋子里,但他仍可能再次被逮捕,因此一定要离开。
可是,他又是多么地留恋这里呀!该死!以前读英雄加利波第的传记时多么有意思!当时他多么羡慕这位英雄,由于他的一生坎坷,生活艰辛,在世界各地遭到搜捕。而他,保尔,却仅仅是7天磨难生活就像过了一年。
看来他的确不是英雄。
“你在想什么心事呢?”冬妮亚弯下身子,问他。保尔突然觉得她的那对暗蓝色的眼睛让人猜不透。
“冬妮亚,让我给你讲述一下赫里斯季娜的故事好吗?……”
“好的。”冬妮亚爽朗地说。“……她就再也没有回来。”保尔艰难地结束了故事。
房间里静得只有那时钟有节奏的嘀嗒声。冬妮亚低着头,她要竭尽全力,狠狠地咬住嘴唇,目的只是为了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保尔看了看她。“因此今天无论如何我得离开这里。”他坚决地说。“不行,无论如何,今天我哪里也不让你去!”
她那纤细、温暖的手指插进保尔蓬松的头发,温柔地抚摸安慰着。
……“冬妮亚,你一定要帮帮我。你替我去机务段去打听打听有关阿尔青的情况,再送张条子给谢廖扎。我有一支手枪我把它藏在了老鸦窝里,我不能去拿,但谢廖扎一定有办法把它取出来的。告诉我,你能帮我这些忙吗?”
冬妮亚立起身来。“我这就去找丽莎,再和她一起到机务段去。你写好条子交给我,我去送给谢廖扎。不过你先告诉我他住在什么地方?还有如果他提出要见你,我该怎么办呢?”
保尔想了一下,回答说:“如果那样就让他晚上到花园里来吧。”冬妮亚在天很晚了才回到家中,保尔已经睡着了。
冬妮亚的手刚碰了他一下,他就醒了。冬妮亚兴奋地笑着说:
“阿尔青马上就会来的,他刚刚回来。丽莎的父亲为他做保,才放他出来一个小时。车库里停着机车。我不能告诉他说是你在这里的,我只说有重要事要告诉他。瞧,他来了。”
冬妮亚跑去开门。阿尔青简直难以置信自己的眼睛,他惊呆在门口。阿尔青进来以后,冬妮亚把门紧紧地关上了,这样躺在书房里害伤寒病的父亲就不会听到他们的谈话了。
阿尔青张开双臂把保尔紧紧搂在怀里,弄得保尔的骨头都有点疼了。
“亲爱的保尔!”商量到最后,保尔决定次日就离开。阿尔青想办法把他送到谢廖扎的父亲老布鲁兹扎克的机车上,随车去卡扎京。
本来性情刚强的阿尔青由于兄弟不明下落,而郁郁寡欢。现在,他十分高兴。
“就这样,说好了,明天早晨五点钟你到材料库去。火车头在那儿上完木柴,你就坐上去。我是多么希望再和你多呆一会,但我该回去了。明天我送你。你不知现在我们到处受监视,就像德国鬼子在的时候一样。”
阿尔青告辞了。天色已经很晚了,谢廖扎也该来了。保尔不时地在昏暗的房间来回走动,一边等着他。冬妮亚和她的母亲呆在她父亲那儿。
在黑夜的保护中,保尔和谢廖扎终于见了面,他们非常地激动,一同来的还有瓦利亚,大家交谈着。
“保尔,我没替你把你的手枪带出来。你家院子里到处都是彼得留拉的人,此外还停着一辆马车,架起木柴生了火。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能爬上去取下枪来,真是的。”谢廖扎说到。“没关系,”保尔安慰他说,“这样也许会有好处的:万一被查出来,会被白白地给杀掉的。不过,你一定无论什么时间都行,但一定要把枪取出来。”
瓦利娅走到他的面前:“对了,你决定什么时间离开呢?”
“明天,瓦利娅,等天刚亮,我就可以走了。”
“你说说,你是怎么获得释放的?”保尔低声,简单明了地把经过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很亲热地相互告别,谢廖扎没再说什么幽默话,由于他心里很难受。瓦利娅也竭尽全力压抑住自己,悲伤地说:“保尔,一路平安!无论在什么地方,别忘了我们呀。”他们走了,很快消失在夜幕之中。房间里又恢复了宁静。保尔和冬妮亚没有丝毫困意,由于6小时之后他们就要分别了,这一别也许就是永别。就这短短的时间,无论如何也无法诉完自己对彼此热烈的爱。
青春,无限美好的青春!这时,朦胧的****刚刚萌动了,只在激烈的心跳之中才能更加感觉到它;这时,无意间碰及女友的胸脯,手会惊惶失措地颤抖并急忙移开,而友谊则拦住最后关键的举动,拦住最后一步的行动!世间再也没什么能比心爱姑娘搂着脖子的双手更使人感到温馨,感到舒畅!还有姑娘的吻,那炙热的、犹如电击般的热吻是多么令人难以释怀!
这是他们相识以来第二次接吻。除了母亲,没有人爱过保尔的,相反,他却常常挨打挨骂,因此,这种温存怎么能让他忘怀。在残酷的、备受折磨的日子里保尔不知道什么才是欢乐,而这个偶然邂逅的姑娘却让他感受到了最大的幸福。
他们紧紧相拥相抱地过了最后几小时。“你要永远记住我为你跳崖而许下的盟誓?”她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叫。他呼吸着她的发香,好像也看到了她的眼神,他永远不会忘记。“不过我不能让自己要你也向我似的许愿?冬妮亚,我真的是很爱你尊重你。你也知道我不会说话,不能对你讲那句话,但你也明白的,对吗?”
他再也讲不下去了。是的,熟悉的、狂热的热吻封住了他的嘴。她那柔软的身体是那样充满诱惑力……然而青春的友谊高于一切。要克制住这种诱惑真是太不容易了。但只要性格耿直,友谊纯真,那也可以做到。
“等到这种局面结束之后,我答应你一定去做一名电工。如果你能答应我,如果你确实真的爱我,不是闹着玩的,那我将是你的好丈夫,我一定不欺侮你。如果我欺侮你,那我就没有好结果。”
他们不敢搂着睡觉,如果被她母亲看到了就不好了,只好分开了。
他们发下了种种誓言,表示永不相忘,然后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这时,天已破晓。
清晨,保尔被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给唤醒了。他仓促地跳起身来。保尔在浴室里换上自己的衣服,装上自己的靴子,披上多林尼克的短外衣。这时,母亲也叫醒了冬妮亚。当他们踏着晨雾来到车站旁的柴堆时,阿尔青早已在那等了很久了。笨重的机车头在嗤嗤作响的蒸汽中慢慢开了过来。布鲁兹扎克在机车里向窗外眺望着。他们拥抱着告别,保尔紧握铁扶手爬上去,他回头又望了望岔道口那两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高大魁梧的阿尔青,娇小美丽的冬妮亚。
虽然她的衣服和头发被风吹起,但她还是拼命地对他挥手。
阿尔青偷偷看了眼忍住哭泣的冬妮亚,深深叹了口气:
“要不我是个大傻瓜,要不就是这两个人有毛病。嗨,保尔,真有你的,你这小子!”
列车转了个弯,不见了,阿尔青转身对冬妮亚说:“呶,怎么样?现在我们该是患难朋友了吧?”冬妮亚纤细的小手立时握在他那宽厚的手掌中。从远方不时地还传来火车加速时所发出的轰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