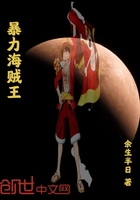霹雳一声,用一个字去回击致你死地的万钧雷霆,这才是胜利者。就用这样一个字,回答了那一夜的大雨,回答了乌古蒙的贼墙、奥安的凹路、格鲁希的晚到、布鲁塞尔的增援,把整个一个欧洲联盟淹没在这简约的音节之中,把恺撒们领教过的秽物敬献给各国君主。他把最粗俗的字眼儿与古老的法兰西的荣光相糅,锻炼了这样一个堂皇不过的词语,这是何等的宏伟啊!
这是对雷霆的辱骂。康布罗纳喊的这个字有一种崩裂之声,是满腔轻蔑之情突破胸膛的那种崩裂,是痛心过甚所导致的一种爆炸。谁是胜利者?康布罗纳,这个最后一刻出现的过客,一个不起眼的小将,大战中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深深感到,溃败荒谬至极。
以往伟大岁月体现的那种精神,在这出生入死的刹那间,启发了这位无名小卒的心灵。康布罗纳在滑铁卢找到的那个字,有一种来自上天的气息,使他产生灵感,因而发出了那骇人的怒吼。康布罗纳代表帝国将那极端蔑视的咒语唾向欧洲,还嫌不足,他且代表革命将它唾向那以往的时日。听着他的声音,我们回味起了列位先烈的遗风。
对于康布罗纳的那个字,英国人报之以“放”。一时间,火光大作,地动山摇。所有的炮口愤射出最后一批开花弹。浓烟被初升的月亮映成了乳白色。烟散之后,一切均不复存在。那小小的反抗之点被扑灭了。御林军悉数覆没。
十四、统帅的分量
滑铁卢战争是一个谜。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满腹疑团。拿破仑只见到了恐怖,布鲁塞尔只见到了炮火,威灵顿则莫名其妙。那确是一个风驰电掣的日子。军事君主政体的崩溃震撼了所有王国,君主们为之大惊失色,强权覆灭。
这样一个事件,必是上天安排好的,人力是不可及的。
英国的赫赫名声,德国的庄严肃穆,皆与滑铁卢问题无关。是上苍认定,民族的伟大在于令人悲伤的武力冒险之外。德国、英国、法国都不是区区剑匣所能代表的。就在滑铁卢剑声铮铮之时,在德国,布鲁塞尔之上有歌德,在英国,威灵顿之上有拜伦。思想的广泛传播乃是我们这一世纪的特征,在这时代的曙光之中,英国和德国都有它们辉煌的成就。只有野蛮民族才会凭一战之功而崛起。那是一种顷刻即失的虚荣,就像狂风掀起的浪花。在我们这样的时代,影响民族文明的,绝不在于一个当兵的得失。他们在人类社会中所占的地位,不取决于某场战争的具体结果。战鼓停息了,理性登了台。凡是属于机缘的,我们统统还归机缘;凡是属于上帝的,我们统统还归上帝。那么,滑铁卢是什么呢?是战争的胜败吗?不,它是一场赌局。
它是一场赌博,欧洲赢了,法国输了。滑铁卢是有史以来最奇特的遭遇。拿破仑碰上了威灵顿。
今天的滑铁卢,一片静谧,与其他地方的原野已不再有什么区别。
可是一到晚上,这里便有一种鬼魂似的薄雾散发开来,那战场的一切早已不复存在,可是鏖战并没有停止;杀气凌云;圣约翰山、乌古蒙、弗里谢蒙、帕佩洛特、普朗尚努瓦,所有这些广袤无边的高地上,都隐隐显出无数的鬼影,朦胧中,在相互厮杀。
十五、如何评价滑铁卢
假如我们站在高处观察问题,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出,滑铁卢的胜利是一次有计划的反革命行动。这是欧洲反抗法兰西,是旧制度反抗创举,是君主制度对法兰西不可遏制的运动的颠覆。总之,他们的梦想就是要剿灭这个崛起了26年之久的强大民族。神权为鬼,滑铁卢则为鬼作伥。事物发展的自然结果便是,统治不可避免地变得自由起来。于是,滑铁卢之后,立宪制度应运而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革命力量不可能真正受到挫败。滑铁卢之前,拿破仑推翻了各国老朽的王朝,滑铁卢之后,又出了个宣布服从宪章的路易十八。路易十八在圣旺会签了人权宣言。革命就是进步;进步就是明天,就是未来。进步就是这样工作着的。任何一种工具,到了这个工人手里,没有不好使的。什么也难不倒它,它利用所有的人。滑铁卢除了断然制止武力,毁灭王座之外,又从另一方面继续了革命的工作。
我们只能看得到滑铁卢存在着的东西。自觉自愿的自由这里是没有的。在这里,反革命成了不情愿的自由主义者,无独有偶,拿破仑成了不情愿的革命家。1815年6月18日,罗伯斯庇尔落了马。
十六、战场之夜
1815年6月18日正是月圆之夜。月色给布鲁塞尔的猛烈追击提供了方便。这促成了那次屠杀。
英军放过最后一炮之后,整个圣约翰山原野只剩下了一片凄凉景象。
我们对战争并不持赞美态度。因而,一有机会,便道出它的真相。战争的第二天,当旭日东升之时,展曦所照的往往是赤身露体的尸首。
6月18日到19日的那天晚上有人盗尸。威灵顿下了命令,对盗尸者当场处置,格杀勿论,但盗犯猖獗如故。战场这边枪决盗犯,战场那边盗窃照常。
惨淡的月光洒在那片原野之上。
夜半时分,有个人在奥安凹路一带徘徊,说得准确些,他其实是在那一带爬行。从外貌看去,他不是法国人,也不是英国人,三分人像,七分鬼像,尸体的腐朽味使他感到亲切。他正在滑铁卢搜刮。他用一件斗篷把他的脑袋包得严严实实。动作鬼鬼祟祟,却一身是胆。他往前爬,又向后看。他不时停下来,四面张望,怕被人注意到。他会突然弯下腰,翻动地上一些不出声的东西,随即又躬起身来,偷偷地离开。他的圆滑,他的神情,敏捷而神秘的动作,就像黄昏荒丘间出没的野鬼。
在他眼前不远的地方,在尼维尔路转向从圣约翰山去布兰拉勒的那条路旁的一栋破屋后面,正停着一辆小杂货车。驾着一匹老马。车子里有个女人,屁股下是箱匣包袱之类。也许这辆车和那边那个神出鬼没的人是一路的。
夜色明静。天空无云。月光洒下来,原野上,有些树枝挨了炮弹,皮还连着树干,挂在那里,在晚风的吹拂下微微摇动。
乌古蒙和圣拉埃,熊熊的烈火仍在燃烧。在它们中间,在远处高坡上,英军营帐中的灯火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形。
在那个曾经发生过惨不忍睹的战争的地方,现在已无声无息了。那条凹路的两壁之间已经填满了人和马,层层叠叠,颠倒,错杂,骇人魂魄。死人、死马堆得高高的,像丰收的粟米。上面是尸体,底下是血河。血一直流到尼维尔路,并在砍来阻拦道路的那堆树木前,积成一个大血泊。铁骑军遇险的地方在靠近热纳普路的地方。尸层的厚薄和凹路的深浅恰成正比。靠中间的路段,也就是德洛尔部越过的地方,路平坑浅,越近这里,尸层越薄。
那个夜行人正朝那尸堆走去。他东张西望,嗅着那条宽而长的墓地,检阅着那令人目不忍睹的堆积如山的死人的队伍。他踏着血泊往前走。
突然停了下来。在他前面,在相隔几步的地方,在凹路尸堆的尽头,有一只手从尸堆里伸出来,月光之下格外显眼。那只手的一个指头上有一个东西在闪亮,那是金戒指。
那人弯下腰去。等他站起来的时候,那只手上的戒指不在了。
他并没有真正站起来,他背向着死人堆,眼睛望着远处,好像一只惊弓的野兽,跪在那里,上身全部支在他那两只按在地上的食指上。
随后,他打定了主意,站了起来。正在这时,他被吓了一跳,因为他觉得有人正在后面抓他。
转过身去。正是那只原来张开的手,抓住了他的衣角。
换了别人一定会吓个半死,可这个人却笑了起来。
“啐,”他说,“幸好是个死家伙!总比碰到宪兵好得多。”
他正说着,拉着他的那只手松开了。死人的气力总是有限的。
他重新弯下腰去,把碍手碍脚的东西搬开,找到那只手,顺着手抓住那胳膊,搬出了脑袋,随后又拽出了身子。不一会儿,他把这个断了气的人,拖到了一个背影处。一个铁骑军的军官,并且是一个等级颇高的军官。他一条很宽的金质肩章露出了铁甲,钢盔没有了。他脸上血肉模糊,有一长条刀砍的伤口,四肢没有被折断的迹象。看样子,他十分侥幸,尸体重叠着,交叉着,在他的上方形成了一个空隙,所以他没有被压。他的眼睛始终闭着。
他的铁甲上缀着一颗银质的功勋十字章。那贼拔下那十字章,把它塞进那蒙头的斗篷下面的那些无底洞里。接着,他从军官的裤袋里摸出一块手表,从背心里搜出一个钱包,把这些东西统统塞进了自己的口袋。正在这时,那军官的眼睛睁开了。“谢谢。”从他的声音听出,他已气息奄奄。翻动他的那种急促动作,晚风的凉爽,呼吸到流畅的空气,这一切使那人从昏迷中醒了过来。贼人没有说什么。他似乎听到旷野里有脚步声,担心巡逻队过来了。“谁赢了?”那军官低声问。他刚刚喘过气来。“英国人。”那贼回答。“您掏掏我的衣袋。我有一个钱包和一只表——你都拿去!”
那贼装模作样地寻了一遍,说道:“全不在了。”
“已经有人偷了,”那军官说,“岂有此理,不然就归您了。”
巡逻队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有人来了。”偷东西的人说,他准备离开。那军官使尽力气,扬起手来,抓住他:“您救了我。您叫什么名字?”那贼连忙低声回答说:
“我和您一样,是法军的。我走了。他们抓到我,会杀了我的。”
“您有军衔吗?”“中士。”“叫什么名字?”“唐纳德。”
“我不会忘记的,”那军官说,“也请您记住我——我叫彭梅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