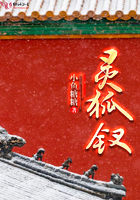巴斯同珍妮在克利夫兰的停车场见面,就跟她谈起未来的希望。“第一桩事情就是找工作,”当那城市的嘈杂声音和怪味奔凑到她身上来而使她的感觉混乱并且几乎麻木的时候,他就这样开头对她说:“找一点事情做做。不管是什么,只要有得做就行。你就算每礼拜不过三四块钱,也就够付房租了。将来等乔其来了,也总可以挣几块钱,再加上爸爸寄给我们的,我们就很容易过日子了。将来总比住在那个洞里要好些,”他最后说。
“是的,”她心不在焉地说,那时她的心已被呈现在四周围的新生活催眠起来,以致不能专注在目前讨论的题目上。“我懂得你的意思。我要去找工作。”
她现在已经老成得多了。虽然还不过那点年龄,理解力却大有提高。原来她最近经过的一番磨练,已经唤起她一种对于生活的更清晰的责任感了。她的母亲是一径在她心上的,还有那些孩子们。特别是马大和味罗尼加,都必须有一个较好的机会可以让她们努力,不要再像她自己。她们应该穿得漂亮些,应该多上几年学;应该有更多的伙伴,更多的机会可以创造她们的生活。
克利关兰,也同当时其他发达的城市一样,是挤满找工作的人的。新的企业虽然不断地兴起,但是要在各种事业中寻找职务的人总还是供过于求。从别处新到这里来的人,也许当天就可找到差不多任何种类的一个小位置,可是也可能奔走到几个礼拜或甚至于几个月仍然找不到工作。那时巴斯主张珍妮先到各种店铺和百货商店去探问。工厂和其他的出路留到第二步。
“可是你不要让一个地方漏过去,”他告诫珍妮说,“如果你想要找到工作的话。你一直进去好了。”
“我该怎么说呢?”珍妮胆怯地问。“你就告诉他们说你要事情做。说你开头无论什么事都可以。”
珍妮依照巴斯的指导,刚到的第一天就着手去找工作,而赚得的报酬只是一些令人沮丧的经验。她不管跑到哪儿,都好像没有人需要什么帮手。她曾经自我推荐到店铺里,工厂里,以及偏僻街道旁边的小店里,可是没有一处不碰一鼻子灰回来。她虽然想摆脱家庭的工作,可是到了没有选择余地了的时候,也只得转到这条路上去了;她于是把招聘的广告研究一番,选定了似乎比较有望的四处。针对这四处她就决计去尝试去了。其中有一处,等她到的时候已经有了人,但是那家出来开门的女主人颇为她的相貌所吸引,因此让她进去,问过她工作的能力。
“你为什么不来早些呢?”她说,“我现在确定的一个女人,我看没你好看,你且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再说。”珍妮受了这样的接待,笑呵呵地走出门。她那时已经没有生小孩以前那样年轻的容貌,可是那更瘦损的脸庞,更微陷的眼眶,反而增加面容的深沉和柔媚。她可以成为整洁的模范。她的衣服是家里动身时刚刚洗过烫过的,所以给她一副整洁动人的外貌。谈到她的高度,还是持续在增长,但是她的精神状态和见识,已经像个二十岁的青年女人了。尤其难得可贵的,是她天生就一种乐观的性情,所以虽然吃尽辛劳,始终是春风满面。无论谁要聘用侍女或是家庭伴侣的,总必都乐意要她。
她第二个去求事的地方,是欧克利路的一家大宅院。她看那宅院的规模非常宏大,自讨自己不配在里面做什么工作,但是既然来了,就决心尝试一下。在门口迎候她的仆人叫她等候一会儿,这才把她引到二层楼太太的房间里。太太名叫联桥夫人,是个相貌不错的黑黝黝的传统女子,对于女性的价值具有敏锐的鉴赏力,当时珍妮给她的印象很好,她跟她聊一会儿,就决计用她试作一般的女仆。
“我每礼拜给你四块钱,你如果同意的话,可以在这里睡,”联桥夫人说。
珍妮讲明她跟哥哥住一起,并且家里人很快就要来。“哦,很好,”联桥夫人回说,“这个你随意。只是盼望你别迟到。”她要她当天就留在那里,即刻开始工作,珍妮也就同意。联桥夫人供给她一顶别致的小帽,一条围裙,这才又用了一点时间指导她的工作。她的主要任务就是服侍她的女主人,替她梳头发,帮她穿衣服。她又须听铃,随时还须侍候用餐,以及听候女主人指令她做的其他任何差使。联桥夫人对于她这新女仆似乎有些严峻而拘泥,珍妮却只钦佩她的精明强干。
那天晚上八点钟,珍妮的一天工作结束,她心里疑惑,不知自己在这样的大宅子里到底能有用处没有,又见自己居然已经应付过一天,自己都觉不敢相信了。女主人第一件给她的工作,就是洗刷珍饰和闺房里的装饰品,她尽管勤勤恳恳地做着,但到她走的时候还没做完。她匆匆走到哥哥的住处,因有找到工作的消息可以报告,心里满是高兴。现在,她的母亲可以到大城市利夫兰来了。现在,她能够同孩子在一起了。现在,她们真正能够开始新生活了,而这新生活是要比从前的一切都好得多,美得多,甜蜜得多的。
按照巴斯的提议,珍妮写信给葛婆子叫她立刻就来,又过了一个礼拜左右,就已租定一所差不多的房子。葛婆子靠子女们的帮助,收拾起家中简单的财产,其中包括一小车模样的家具,差不多两星期之后,他们就动身到新家去了。
葛婆子是一向希望有一个真正舒服的家的。一套布置得很好的耐用的家具,一条颜色悦目的柔软的地毯,许多椅子,安乐椅子,和图画,一张美人榻,一架钢琴——这些美丽的东西,是她艳美了一辈子了的,却因生活条件始终不好,造成她的希望至今还只是梦想。但她仍旧不放弃。她认为自己只要能够活下去,这些东西终究会得到,所以总有一天可以如愿。现在,也许她的机会到来了。
到了克利夫兰之后,看见珍妮那副欢乐的面容,她这乐观的感情就得着一种支持。巴斯向她解释,说他们将来的一定会过得很好。出了车站,他就带他们到新住处里去,并叫乔其记着回到车站的道路,准备过一会来看管行李。白兰德送给珍妮的钱,现在葛婆子身边还剩,有了这笔钱,就可以用分期付款的办法添置几件家具。巴斯已经付过第一个月的房租,珍妮则已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把新房子的窗门和地板全部清洗干净,弄得一尘不染了。第一天晚上,他们就有两条新席子和被褥之类铺在洁净的地板上;又有一盏新的灯,从邻近一家商店买来的,一只箱子,是珍妮从一家杂货店里借来的,准备擦地板时葛婆子可以在上面休息,并且已经预备了腊肠和面包,足以支持到第二天。当夜大家聊天,商量将来的事,一直谈到九点钟,这才都去睡了,只剩珍妮和她母亲两个人。她们继续聊天,觉得一家的责任如今都落在珍妮身上,葛婆子已经感到有些要依靠她了。一个礼拜过去了,这家小小的房屋就完全布置完毕,共计添了半打新家具,一条地毯,以及几件厨房里的日用具。最困难的事就是需要一个新灶台,因为这笔费用一定会大大增加帐单上的开销。较小的孩子都已送进公立学校了,只有乔其决计叫他去找工作做。对于这主意,珍妮和她的母亲原都感到不公平,可是想不出什么法子来避免这种安排。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明年再送他上学,”珍妮说。当这新生活好像已经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收入和费用仅能相抵,就难免构成一种永远存在的威胁。巴斯本来是很慷慨的,但是不久之后,他就觉得每礼拜供给四块钱做自己的食宿费已经很多了。珍妮的收入全部都充家用,她认为只要好好替她带孩子,她是什么都不需要的。乔其到店铺里去做收迭贷款的店徒,每礼拜薪水二元五角,开始时是情愿全部充作家用的,后来才允许他五角钱留作自用,也是公平的办法。葛哈德从独自做工的地方每礼拜邮汇五元回来,常叫他们要积攒一点,预备偿还科伦坡的旧债。这样,从全家人每礼拜总计十五元的收入中,要支付吃的,穿的,房租,煤钱,并且有五十元的家具帐得每月分期支付三元。
这一个局面究竟如何应付,那得请那些侈谈社会贪图现象的适意人们自己费点心去捉摸了。单是房租煤和灯这三项,已经要花费二十元一月的巨款;吃的一项也不幸但也是必需的,又须加上每月二十五元;此外还有衣服,家具帐,零碎帐,偶然要有的医药费,以及类似的项目,都指望剩下来的十一元里支付,这其中究竟应如何处理,就请适意的读者们用力想像去猜想吧。然而他们竟然应付过去了,而且这一家满怀希望的人暂时都认为他们过得不错。
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小小家庭便是一幅值得我们观赏的诚实而忍耐的劳动的图画。葛婆子像家里雇佣的仆人一般干活,而且绝对得不到衣服,娱乐,抑或其他任何的报酬。每天是她第一个先起床生火,火生好了,就得跟着做早饭。在她拖着一双垫着报纸的破拖鞋悄悄往来工作的时候,她往往要去看看尚在酣眠的珍妮,巴斯,和乔其,心中抱着与生俱来的神圣同情,想让他们用不着起得过早,也用不着工作得过于劳苦。有时候,她得去叫醒可爱的珍妮,却先要停一会,凝视她沉睡中非常宁静的苍白脸色,心里悲痛,以为人世待她未免太不公平了。这样看过了几分钟,这才把她的手轻轻放在珍妮肩膀上低声招唤,“珍妮,珍妮,”直到那疲倦的梦中人醒来为止。
等到他们起床,早饭早已经准备好了。每天他们回家的时候,晚饭也总是准备好了的。每个孩子都分得葛婆子的一份儿注意。至于那外孙女儿,当然尤其照料得周全。她经常说,只要孩子们有人替她出外跑差使,她是不需要衣服和鞋子的。
孩子们当中,珍妮是完全了解她的母亲的;只有她具有全部的孝心,努力要减轻母亲的负担。
“妈,这个让我来做。”“现在,妈,那个交给我吧。”“你去休息一会儿,妈。”这些就是她们母女之间那种持久感情的日常表现。
原来母女之间从来就有一种彻底的谅解,日子过得愈长,这种谅解就正常的推广而加深了。珍妮看她母亲一辈子呆在家中,心里很是不忍心。她每天工作的时候,总想到母亲正在守候的那个卑微的家庭。她自己所常希求的那种种的舒服,她多么渴望母亲得能享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