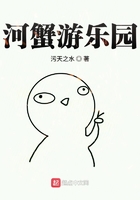自从玛丽从那个伟大的巡警的怀抱里逃走之后,他想念她比往常格外厉害,不过她的小影现在是在愤怒的宝座上:他看见她仿佛是一个立刻就有迅雷疾电的阴沉的晴天。真的,她开始将他的精神占领了,连他姑母的侍候,和那个喜悦的姑娘的殷勤都不能给他一点安慰,不能使他断绝那个朦胧的蔓延在他与他照管车辆的职务之间的默想。如果他没有发现她的出身寒微,他的进行是简单的,直爽的:在现在这样情形之下,他的问题便变成每个男子的难题了——究竟他娶这位姑娘呢,还是那位姑娘呢?但是用来解释这种问题的数学,结果总会减轻他的困难,他可以十分自由的遵行所指示的路径于他的自爱一点不会有妨碍。无论他的倾向在那方面游移,假使他心里有一种懊悔的苦痛(那是不能不有的),这样的感觉不是最后被他的理性所放弃,便是留着做一个有满足爱好的纪念。如今他既然知道玛丽的社会的卑贱,这个问题便复杂了。因为,虽然以后他要娶她作妻子这一层自然不成问题的,她最后那种恶待他的情形仿佛在他血里注射了一针病毒,这病毒的一半是要得到她身体的一种热情,一半是要报复仇恨的一种癫狂。假使一起首她就没有理他,他倒很容易抛弃她的。他在她现在的动作里看出她是不要他,这真使他恼怒,因为这是侵犯他的正当的权利——以先他只要伸出手去,她一定会像小猫似的驯服落在他的手里。现在呢,她居然会躲避他的手,真的,她会于他没有一点关系;这种情形是不能饶恕的。他一定很高兴打到她服从,一个小女孩子有什么权利可以拒绝一个男子的,况且是一个巡警的恳求?这是一种刁歪的心性,应该用一根短棍把它们打直的。但是一个小姑娘在她没有嫁我们之前,我们不能自重的甚至于安静的揪打,因此他不得不放弃那个宝贵的念头。他应该用她所该受的鄙视将她从他脑筋里驱除出去,但是,啊呀!他不能:她如同耳垂似的黏着不去,除非将她占领了或把她打一顿——两个都是可怕的办法——因为她已经变成他所憎恶的宝贝。他的感觉与他的自尊互相设法把她扶在一个高台上,而他只能惊愕的向上看——本来在他低下的那个她现在会比他高!这是可惊骇的:她一定得从她的尊高被拉下来,再用他自己的愤怒的脚底把她践踏回到她原来的低微;然后她可以被荣耀的举起来,用一只和平的,宽思的男子的手发放出饶赦与恩典,或者因为她的伤痕还赐她一种抚慰的膏药。伤痕!一膝踝,一胳膊肘子——这都不算什么;一点儿伤口只要亲一下立刻就好的。可以用男子的接吻医治的伤痕,女子会不宝贵吗?自然与先例都赌誓证明这话是对的……但是她是在他范围之外的;无论他的手伸到多高,也够不着她。他急疾的走到凤凰公园,到圣司蒂芬公园,又到郊外的树荫的地方同隐蔽的小路上,但是哪里也没有她。他甚至于到她住宅的附近去探访,也不能遇见她。有一次他看见玛丽在路上走来,他便退缩到一家门洞里。一个年轻的男子在她旁边,滔滔不绝的说着话,玛丽对他也是同样的多谈。他们俩过去的时候,玛丽看见了他,脸上便红晕起来,她挽着同伴的手臂,两人放开大步急忙的走了。……她对他从来不会大谈过。永远是他一个人说话,而她总是一个服从的,感谢的听者,他从来没有不高兴她的缄默,但是她的隐晦——这是一种假装,比假装更坏,一种欺骗,一种假面具与蒙蔽着的虚伪。她很情愿的服从他,但是她的周围罩上一个隐藏的,保护的盔甲,她躲藏在这盔甲里可以不受那种制胜的军器的伤害。一个战胜者难道没有掳掠品吗!我们要求城墙上的钥匙以及无限制的出入,不然我们的火把又要放光了。这位有说有话的玛丽是他向来没有见过的。就是在他面前她尚且将自己隐藏起来,在各方面看起来她是一个淘气的。可是她能对那个与她同在的东西说话……一个干裂瘪的贱东西,像这样的人只要男子的一口气便可以把他吹到极远,吹到四分五裂的没有了。这个男子不又是一种侮辱吗?难道她连埋葬她的死人还等不及吗?呸!她不值得他想念。一个女子这样的容易被引诱。可以随便吹到这里,吹到那里,她也看不出什么不同来。这里和那里在她那看来都是一样的地方,他和他都是一样的人。像那样的女子没有好结果的。他见识过不少了,这种样子与这种结果永远不分离的,一个人难道不能就事实预言吗?这时他眼前仿佛看见在穷人窟里的一个坏妇人,一个****女子在一个黑暗的门口徘徊,这个幻像使他忽然非常高兴,可是到了第一分钟便离开他了,这时她扑翅膀带着大嘲笑的声音挤了进来。
他的姑妈从他紧蹙的眉心里想到他职业上的重大责任,心里很为他可怜,她为他从来所没有想到过的事情瞎难过,因为使他的好脾气的最末一点也离开了他,他便张口大骂她,骂得她惊惶起来。那另一个快乐的姑娘的那种甜美的味儿上从来没有偿过,只不过摆着做样子,她会在他的面前默默的想心思:她有时候仿佛质问似的飞他一眼……她得小心点,不然他的火气要直冲到她牙齿里:大的声音吓到她的喉咙里,吓得她昏迷过去。这时应该有一个人显出一种看得见的,摸得出的痛苦可以与他做对偶。难道法律所追究的没有比偷一只手表再深的吗?有人偷了我们的自尊难道还可以逍遥法外?我们的灵魂对于他们的侵略者难道不能要求赔偿吗?总得有一个很富的人修理他的裂痕,不然天堂便没有警察署公道,也许那个姑娘的命运应该替玛丽赎罪。使别人心里像他一样的难过,虽然是痛苦的,也是痛快的事情,应该叫别人难过的;他很残忍的决心要这样做。
二十九
喀佛底太太的房客与玛丽果然渐渐的亲密了,这并不是使了什么诡计。莫须有太太自从听了那个年轻男子的食量与他不得不满足这食量所经过的苦痛,她很为他担心。她总想那个孩子从来没有吃饱过,她对她女儿说起年轻人的贫苦格外的夸大其辞。一个年轻姑娘所不能了解的那种身体孱弱都是因为营养永远不足。喀佛底太太是她的朋友,并且又是一个很好的,端正的妇人,什么谣言诬蔑她都是枉费,但是喀佛底太太乃是六个孩子的母亲,究竟不敢过于扩充她的天生的仁爱学,以致妨害她的孩子们。再者,因为她丈夫的没有事更限制了她的大度。她知道喀佛底太太家里的瘠瘦的饭锅,她又看见那个年轻男子只得到喀佛底太太敢给他的一点食物,因此他的饥饿的苦痛差不多要了她自己的生命。在这种情形之下她会找了一个机会去同他亲近,这事很容易的成功了。所以玛丽看见他坐在她们的床上大嚼她们的半块面包,初见虽然有点惊愕,但是立刻就很高兴了。她妈带着一种恬静愉快看着她们的食物的消失。虽然她的帮助不多,但是每一小块都有帮助,不但帮助了他的需要,并且他的食量满足之后连她的朋友,喀佛底太太,同她孩子们也得了帮助。不然,这样的胃口竟可以妨碍他们全家的平安。
那个少年用一种很流畅的高谈阔论报答她们的厚意,说些莫须有太太和她女儿向来不大有机会可以研究的许多问题。他说了那些与少年们有关系的很有趣的问题,他对于各种问题的见解,虽然常很糊涂的,也很够有趣的,虽然常有孩子气的错误,但是不讨厌,他善于辩论,倒也颇能承受理性;因此莫须有太太有了她向来不大得到的讨论的机会,不知不觉的她占据了给他做指导的哲学的朋友的地位。而玛丽在他的谈论里也找到了新鲜的趣味,虽然那个少年的思想与她的很不同,他也会与她所在的地位思想过,所以暗中纠缠他的问题也就是深深占据她脑筋的问题。共同的糊涂也许像共同的利益一样的互相牵制。我们对于一个比我们知识多的男子或女子仿佛是怀疑的,但是我们对于那种只凭推测代替地图,只以优游代替指导的探险家,便许他用我们的手做他自己的手,把我们的钱袋作他自己的财产。
那个少年既然不比一只猫更怕羞,不久他便与玛丽晚上一同出去散步了,他是一家大杂货店内的一个伙计,他告诉玛丽许多人都认为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在他的职业的地位内既有朋友也有仇人,这些人他可以用于他们相配的流畅的话来讲。玛丽知道,比方说,那个大老板是秃子,但是人很端正(她看不出秃子与端正之间有什么自然关系),还有那个二老板是一个既无德行又无胡子的人。(她仿佛见他像一个鳖鱼似的有一双恶毒的眼睛。)他述说许多在旁人只有一件,在他可是占全了的坏事。(这样他一定是毛茸茸的)。言语,就是那位少年的言语,不能适当的形容他。(他把男孩子当早餐吃,女孩子当茶喝。)那个少年与这个家伙永远不完的冲突(一只熊有两只小耳朵与一嘴巨牙);不是公然的冲突,因为若是公然的冲突他便立刻会辞退(一点不是毛茸茸的——一条知识很充足的黏滑的鲤鱼),而是一种暗地里的不息的战争,这种战争占据了他们所有空闲的精神。那位少年知道总有一天他不得不打那家伙,这是一定的,可是那一天那个家伙准要倒霉的,因为他的力气其实可怕。他告诉玛丽被他打后的可怕的影响,但是玛丽看了少年的肌肉只有更怀疑。她口里称赞他的肌肉,因她想这是她应该尽的义务,但是对于她们的无敌的破坏性多少有点疑惑。有一次她问他,能不能够与一个巡警决斗。他告诉她,说巡警不能单独与人决斗,只可以仗人多合伙儿打,他们那打法是又狠又丑的,往往就靠他们那大脚靴子踢,所以体面人对于他们的决斗伎俩或他们的私人行为都看不起的。他告诉她不但他能打倒一个巡警,他还可压服像这样的人的子子孙孙,并且可以一点不费力的做了。那位少年自己对于所有的巡警与大兵有一种激烈的恶感,他又把那些地主与许多劳动者的雇主也列入这些坏人的团体里。他骂这些人没有一个待人公道的。他说,一个巡警可以无缘无故的捉拿他的邻居,如果对于他们的愤怒有所反抗,那个不幸的囚犯便要在他的监牢里被极凶的拉来拉去,直到他们愤怒的威严缓和了为止。一个男子犯的要被捉拿的三种大罪就是酒醉,骚扰,或是拒绝战斗,可是这些都是青年男子所最容易犯的毛病。他对武力很有趣味,并且还要批评他们的行为。他看见一个兵丁便会烦恼,因为他看见一个战胜者昂头阔步的在他国内的都城里经过,而他的本地不能驱逐这个骄傲的人实在使他惊讶,使他羞辱。地主们的心内毫没有感情的。他们这些人没有慈善的心肠,也不愿意帮助那些将全生命牺牲于他们的利益的人。他看他们好比是些懒惰,不生产的贪夫。他们口里永远嚷着“给,给,”但是他们从来不报恩的,只是有增不已的,侮辱人们的专横。还有许多雇主也列在这坏的一类里。他们是否认人类一切义务的人,他们看自己是万事的开始,也是万事的结局,他们满足他们的贪心并不是因为可以做他们同胞的恩主,(只有这种正常的自由为我们所看得见的)只不过无聊的运用一点势力以达到财富所能得的赞美,至于给这种赞美的人实在是人类的大愚。这些人用完了他们的帮助者,便一脚把他们踢得远远的,他们利用他们的同胞,买了他们的同胞,又卖了他们的同胞,而他们的骄傲的自信,与他们为他们的安全所聚集的伟大权力,使他惊骇得仿佛这是一件不能相信的事情,虽然这是很真的。世上竟有这种事情使他烦恼得大声高呼了。他要把他们个个指出来给大众看,他看见他的邻舍堵着耳朵,只要他能够刺破那厚皮的听觉,他就是大声的喊到死也是愿意的。那些他以为极简单的,难道人人都会不懂的!他可以看得清楚而别人不能,虽然他们眼睛笔直的向前看,并且的确专心的有感觉的向四下乱转!难道他们的眼睛,耳朵,脑筋活动得与他的不同,或者他是一个特别的怪物,生下来便受了疯狂的害?有的时候他预备让人类与爱尔兰都倒他们自己的霉去,他很相信假使世上没有他,他们立刻灭亡尽了。
有的时候他说起爱尔兰用一种热烈的感情,这种感情假使说给一个妇人听未免太厉害。真的,他把她(指爱尔兰)看作一个女子,仿佛王后似的,很受苦但是很高傲,他为她提心吊胆,凡是爱她的男子都是他的骨肉弟兄。有几个字(爱尔兰的别名)的势力差不多可以催眠他——至于这几个名字稍稍念几遍使他乐得发狂了。她们有奥秘的魔术的意义,这意义深深的刺入他的心弦,震得他使他发生一阵热烈的怜悯与爱感。他很想做出一番勇敢的,激烈的,伟大的事业,这事业可以收回她的信用,可以使爱尔兰人的名字与伟大或独一这两个字有同样的意义:因为他看不清这个字的意义的差别,如同别的少年以为强暴就是英雄,怪僻就是天才一样。他说起英国来带着一种仿佛惊吓的神气——仿佛一个小孩缩在一个漆黑的树林里讲那个鬼怪杀了他的父亲,掳了他的母亲,把她带到他的用枯骨建造的城堡里的一个可怕的监狱里——他这样的说英国。他看见一个英国人一手挽着一个王妃,凛凛可畏的大脚步的向前走,而他们的弟兄们与他们的武士们都是被困在魔术里倒头熟睡,不管人家侵犯他们的妇女,也不管人家污抹他们的盾牌……
“哦,可怜可怜,那曾经一次荣耀过的班拔(即爱尔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