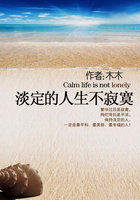姑夫的状态一直没能好起来,尽管他努力把自己装点得年轻新鲜一些,垂头丧气的表情还是改变不了。声音也有问题,电话里都是蔫蔫的,底气不足。这种状况让我担心,姑夫一直都是浪浪荡荡的,陡然严肃和愁苦,我还真有点不适应,老觉得有事。所以联系就频繁了多了。他也经常到我那边去,爷儿俩喝喝酒,说说话。在北京这么大的地方,有个人聊聊其实是听温暖的一件事。我觉得这也是姑夫没事就来我那里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是这段时间风闻又要开始严打了。
这是我从报社里得到的消息。前几天有个同事去了公安局,采访几个新被抓进去的办假证的,回来后说,那些办假证的也不容易,进去了先要挨上一顿。他又说,听局里的内部消息,最近又要开始严打,狠抓一批,因为现在社会上出示假文凭的太多了。据说,人口普查之后发现,名册上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比实际培养的人数多了五十万。听到这消息,赶紧给姑夫打电话。姑夫说,他早就知道了,正准备收一收。他们道上一些神通光大的人,早就得到了消息。
姑夫开始唉声叹气,从一进门开始,直到离开,都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像受了多少罪似的。他变得空前地沉默了,不愿意说话。我想可能是生意上有问题导致的,所以尽量避免和他聊这个话题。又不能大眼瞪小眼干坐着,我就瞎扯,找他感兴趣的话题,谈女人。没什么经验也谈。
“跟你谈什么女人?谈不来。”姑夫说,一点都激动不起来。
“我怎么不能谈?”我说,“过去不是谈了不少么?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吧。”
“不谈。”
“随便说,再上一堂理论课。”
“理论有个屁用,真刀真枪动起来,理论早不知跑哪去了。不想谈,想起女人就烦。”
“路玉离惹你了?”
“除了她还有谁?”姑夫喝过酒歪到我床上。“在北京这鸟地方,我这么没出息的,还能再找其他女人?”
姑夫自卑都出来了。这女人一定把他伤害得不轻,快半个世纪了,还没有哪个女人能把姑夫打击出自卑来。这个路玉离,竟然让他连谈女人的兴致都没有了。
一次姑夫喝多了,在我那儿睡了一觉,起来时没注意把身份证丢我床上了。我估计他差不多该到家的时候给他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声。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你是路玉离?”我说。“姑夫在吗?”
“不在。”
“他身份证丢我这了,你告诉他一声。”
“没别的事我挂了。”
“有,”我脱口而出,“我想问问你,姑夫最近情绪很不对头,是不是因为你?现在他有点困难,你就不能帮帮他,分给他几个?”
路玉离对我的话很不感冒,显然不高兴了。“谁说我没给他?我不是已经又给了他三个?他自己也知道他不是吃这碗饭的料。”
“那他怎么回事?你们吵架了?”
“我懒得和他吵。自己不行,还整天骂骂咧咧的说我有问题。”
她的口气我一下子听出来了,姑夫作为男人的合法性在路玉离那里受到了质疑。他不行了。这倒是个新鲜事,姑夫竟然也不行了。说实话,我当时真觉得有点意思。我继续问下去,丝毫没有什么顾忌。大概是在内心里,我对路玉离多少还是瞧不上眼的。
“那你不能帮帮他么?”
“我怎么没帮他?”这个老女人和我一样无所顾忌,她的确也到了无所顾忌的年龄。“我到处给他买药,他一会儿吃,一会儿又不吃,疑神疑鬼的。让他去看医生他又不去,要我怎么办?”
“怎么会这样?姑夫身体一向挺好的。”
“我怎么知道。可能是想钱想出问题来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姑夫临到真格的就羞于开口了。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他说。上班时,我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同事聊起来这事,他建议我还是找医生看看,十有八九是心理原因。我说我不好开口,开了口他也未必就答应去。同事就让我先去咨询一下有关医生,有了初步诊断他也许就同意了。
我通过朋友,找到了一位这方面的专家。我把姑夫的这几年的情况尽可能详细地告诉了那位专家,把路玉离的话也转述了一遍。专家听了,说这很简单,心理性的疾病,主要是心理压力太大。比如家庭方面给的经济压力,生意上的挣钱的压力,也可能有相互攀比之后的心理失衡的原因,比如潜意识里和路玉离、或者其他人相比较,当然性生活上的偶尔不协调带来的心理暗示,这最关键,各个因素之间相互纠缠,从而导致目前的状况。
“该怎么治疗?”
“心理问题还须从心理入手,”专家说。“安慰、理解和宽心,解除他的心理障碍。还有成就感,这大概是振奋他精神的最好药物。”专家又说,“这只是初期,心理治疗还比较容易,越拖延就越麻烦。”
从专家门诊出来之后,我就在考虑要不要直接对姑夫讲清楚。同事建议先不要挑明,挑明了反而等于给他增添新的心理暗示,最好是请路玉离来慢慢解决他的心理问题。同事的建议有道理,问题是这话我怎么和路玉离说。
“怕什么,”同事说。“都睡了这么长时间了,这几句话还扛不住?”
我想也是,关键是要为姑夫负责。我从姑夫那里找来路玉离的号码,简单地说了一下,觉得电话里说不清楚,就约她到硅谷旁边的肯德基谈。路玉离的坦诚出乎我意料,她完全接受医生和我同事的那些建议。
路玉离说:“不管你姑夫出于什么目的和我在一起,我害了他也罢,喜欢他也罢,都不说了。在一起前前后后也好几年了,说真的,即使是我老公,我也没有和他这样亲密过。我是一个女人,都半辈子了,知道该留点东西了,能不能留住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是只认钱,我还认他。我也不希望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专家说了,这时候女人比药物更有效。”
路玉离有些不好意思。“我会尽力的。其实他不适合干这个,可他不相信,”她点上我递给她的烟。“医生说的对,就是一个心理问题,他现在迫不及待地想把一辈子浪费的东西都挣回来。但是他现在一无所有。”
“他需要成就感。”
“谁都需要成就感,可最后到底有多少人能得到这个成就感?我是弄不明白了。”
“我也不明白。”
应该说,那天我们谈的很好。本来想请她吃饭,但是觉得不合适,我请姑妈的情敌吃饭算什么事。路玉离显然也理解,她随口扯了个幌子就走了。正如她所说的,这更应该是她的事。
路玉离如何对姑夫进行心理疗法,我不得而知。一周后我打电话给她,她也不避讳,直接说,效果不是很明显,不过还是有点眉目,但最后怎样,她不好说。她说她昨天刚去了见了一个医生,那医生建议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同时进行,也许那样应该好点吧。
“最近我姑夫情绪怎么样?”
“还好,因为要严打,生意都放下了,我们一直在一起。因为不太出门,心情没什么大的动荡,当然也不会有太让人高兴的事。”
“慢慢来吧,”我说,“安全是第一位的,避过这段时间最要紧。”
我们通过电话刚两天,媒体上就开始正式宣传和报道严打了。街头上,路边上,尤其是大学门口立刻少了不少闲人,那些办假证的闻风逃匿。有几个胆大的顶峰作案,一不留心就被揪住了。报社里也常有这类小道消息。我打电话告诉姑夫,千万不要乱跑,这次严打不是一般的形式文章,动真格的了。媒体上的宣传口号是:时间长,力度大,挖掘深。
姑夫说:“没事,都待在家里。我又不想死,出去干吗?”
这是六月中旬的事了。六月底,让人高兴的事情终于来了,小峰的高考成绩下来了,在我们那个县城同类考生中排名第一。按照全省的分数排名,他在前二十五名。他报考的学校是清华,这一年清华在我们那个省的招生名额是三十。也就是说,从知道分数的那一刻起,他基本上就是清华的学生了。
小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时,我和他一样激动,我听到姑妈高兴得哭了。她就站在电话旁边,听小峰给每一个亲戚和朋友说同样的一番话。姑妈真的很高兴,她觉得她终于熬出头了。
挂了电话我就给姑夫打,接电话的是路玉离。
“姑夫呢?小峰考上清华了。”
路玉离也很兴奋,说:“他知道了,刚哭得稀里哗啦,正高兴着呢。”
我对路玉离说:“这回姑夫该有成就感了吧。”
路玉离还没回答,电话接着被姑夫抢过去了,姑夫说:“高兴。高兴。今儿个真呀真高兴。”
听到姑夫的这种声音我也很高兴,感觉过去的那个放浪不羁的姑夫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