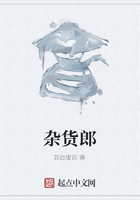禅不仅在精神指向上给高行健以影响,而且直接进入他的戏剧文本、小说文本与水墨画本中,赵毅衡先生研究高行健的着作《高行健和中国实验戏剧》中,给高行健戏剧命名为禅剧,并分析了禅如何渗透高行健的许多剧本。而小说《灵山》的许多章节更是充满禅意。但笔者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禅给高行健的启发,主要不是带给他的作品某些禅意,而是给予高行健对人生的大彻大悟,即从根本上悟到人在短暂的生涯如何得大自由,如何得大自在。禅从根本上告诉他:一切取决于自己。佛不在身外而在身内,天堂和地狱全在自己的心中。自由不是等待外在力量的恩赐,而是自己争取的结果。“写作的自由既不是恩赐的,也买不来,而首先来自你内心的需要。……说佛在你心中,不如说自由在心中,就看你用不用。”高行健:《文学的理由》。也就是说,作家一生唯一应当做的,就是打开心灵的大门,把“佛”解放出来,把自由解放出来。这就是说,禅给高行健最根本的启迪是:你必须自救!你不要仰仗外部力量,包括不仰仗上帝的权威与佛陀的权威,而要仰仗自己的肩膀和自己的内心力量。高行健全部作品的思想就立足在这一首先由禅宗点破的“自救”精神上。
最集中地体现高行健通过“自救”而得大自在精神的剧作是《八月雪》,这部以慧能为主角的戏,表面上看,写的是宗教题材,宗教故事,实际上写的是慧能在各种现实关系中如何得大自由的生命奇观。慧能是个宗教领袖,但他不崇拜宗教偶像,不膜拜任何神的权威。所以也不落入教条的牢笼之中,当然,他也无所谓以神为中介的忏悔。慧能弘扬禅宗思想而名播天下之后,又不被名号所拘,也不为权力地位所诱惑,连钦定的“大师”桂冠也不要。皇帝派了特使、带着圣旨来传他进京,说:“大师德音远扬,天人敬仰……则天太后、中宗皇帝陛下,九重延想,万里驰骋,特命微臣,征召大师进宫,内设道场供养!请能大师略作安排,即由微臣护卫,火速进京!”可是,慧能一点也不动心,一再拒绝。使者见诱惑不灵,便威胁说:“这敕书可是御笔亲书,老和尚不要不识抬举!”并按剑逼迫,慧能此时更是坦然:
慧能:(躬身)要么?
薛简:什么?
慧能:(伸头)拿去好了。
薛简:拿什么去?
慧能:老僧这脑壳!
薛简:这什么意思?
慧能:圣上要的不是老僧吗?取去便是。高行健:《八月雪》。
宁可掉了脑袋,也不接受宫廷的指令,也不要外在的名号桂冠。这些全是无。北宗神秀早已应召入京,当了两京法王,圣上门师。但慧能不走神秀的路。使者告诉慧能,当今“皇恩浩荡,广修庙宇,布施供养僧侣,功德天下”,而慧能让使者转告皇帝:“功德不在此处”,“造寺、布施、供养只是修福。功德在法身,非在福田。见性是功,平直是德,内见佛性,外行恭敬,念念平等直心,德即不轻”,又说:“自性迷,众生即是菩萨;自性悟,菩萨即是众生,慈悲即是观音,平直即是弥勒。”慧能把神的“救护”归结为“自性悟”,自性一旦大彻大悟,便生大慈悲,大正直,便是大菩萨、大观音。他透彻地了解,到宫廷里去当法王大师,不过是当皇帝的点缀品,哪里是什么菩萨弥勒,广修庙宇,不如对百姓多一点仁爱之心。慧能不仅看透世俗最高的荣华显贵,而且也看透本教中祖传的袈裟衣钵,临终前他的弟子法海问他“衣钵所付何人”时,他回答说:“持衣而不得法又有何用?本来无一物,那领袈裟也身外的东西,惹是生非,执着衣钵,反断我宗门。
我去后,邪法缭乱,也自会有人,不顾诋毁,不惜生命,竖我宗旨,光大我法。”当弟子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大师过去,后人又如何见佛?”他回答说:“后人自是后人的事,看好你们自己各下吧;……你的好生听着:自不求真外觅佛,去寻总是大痴人。”禅宗作为一种宗教,就是这种“自我求真”、“自我求善”的宗教。一切取决于“自性”,一切取决于自身的心灵状态。高行健的《八月雪》,写的是慧能,也是写他自己。慧能看穿一切身外之物,看穿偶像、王冠、桂冠、衣钵,“本来无一物”,包括这些世俗眼睛所瞻仰、所追求的宝物。他的所有行为,都在暗示一个禅宗的真理,这就是放下世俗所迷恋的一切,便得大自在、大自由。自由就在你自己的心中,大自在就在你的选择之中。也正是这一真理,构成了禅宗自救精神体系的前提。如果把慧能的名字换成基督,那么,这个东方基督与西方基督相比,其相同处,是都具有大慈悲的宗教情怀,其不同处是西方的基督告诉众生必须仰仗上帝的肩膀,走出苦难,而东方的基督则告诉众生:你必须仰仗自己的臂膀和自身内心的力量走出苦难。当你心内的力量足以抵御外部世界的压力与诱惑,放下各种地狱与牢房,你便获得救赎。
如上文所说,《灵山》作为一部内心游记,也是一个寻找“灵山”即寻找救赎、寻找解脱的过程,但是,读者发现,主人公“我”没有找到最后的目标,按照禅宗的看法,人生最后的结果是走入“空”门,是一个形而上的“无”。因此,他们只乐于过程,乐于在寻找过程中的内心体验,而不在乎外界的神的标志。这一点实际上与基督教相通。基督教并不承认人可达到神。人无论怎样努力,只能接近神,不能达到神,再伟大的人物,只能殉道,不可能成道。与禅宗不同,中国的儒家却着重思考外部秩序,也特别关心最后能否达到“内圣外王”的结果。
不能成王,就说明“内圣”有问题,“外王”与“内圣”总是互动与互相定义,因此,儒家便通过一套修养方式去追求完美的道德境界,总之,它执着于外部的礼、社会秩序与道德权威,而忽略甚至删除内心体验与内心感觉。而禅宗刚好相反,它把内心体验与内心感觉看成是最重要的东西,它的全部思考目的就在谋求内心的大解脱,以致认为上帝在内不在外,天堂地狱也在内不在外。人类得大自由,不是依靠外在的神明,而是靠内在的精神。因此,如果说,儒学是思考外部人际秩序的思想,那么,可以说,禅宗是思考内在的人类生命的思想。高行健的《八月雪》把禅宗的思想推向精彩的极致,主人公慧能把外部的秩序、制度、荣耀、权力等统统看穿。
高行健作为一个当代的思想先锋,他不仅像慧能一样看穿外部的权力、荣耀等身外之物,而且叩问由“救世”思想所派生的“社会良心”是否可能,或者说,是否可靠。与“自救”的思想相衔接,高行健只确认“个体良心”的实在性,不确认“社会良心”的实在性。他发现人类历史上的各种苦难、灾难,都是良心无法疗治的:
回顾一下人类的历史,人生存处境的一些基本问题,至今也未有多少改变。人能做的只是些细小的事,制造些新的药,弄出些新的产品,时装、氢弹或毒气,人生之痛却无法解脱。……诸如战争,种族仇恨,人对人的压迫,而人的劣根性,良知并不能医治,经验也是无法传授的,每人都得自己去经历一遍。人之生存就无法解释。人如此复杂,如此任性。现今宗教又回潮。我不信仰任何教,但有种宗教情绪,我们得承认等待我们的是如此不可知,个人的意志无法控制,我们首先得承认个人之无能为力,也许倒更为平静。高行健:《没有主义》,第56页。
上帝早已存在,所谓“社会良知”也早已存在,但是,战争依然不断发生,人对人的压迫有增无减,人的劣根性没有改变。历史携带着苦难,不断在地球上重复。面对历史,高行健对“社会良心”提出怀疑。作家是否可能成为“社会良心”?他的良心资源与尺度来自何方?一旦代表“社会良心”,这种良心会不会标准化、权威化而衍变成一种权力?毫无疑问,“社会良心”角色是“救世”精神体系所派生出来的角色,高行健从“自救”立场出发,拒绝充当这种角色。拒绝充当“社会良心”不是没有良心,而是强调“个人良心”,确认个体良心的实在性。因此,在高行健看来,所谓良知责任,乃是个体对道德责任的体验和体认,而不是拿着道德权威的名义和其他外部权威的名义去号令他人。所以他决断地说:
作家不是社会的良心,恰如文学并非社会的镜子。他只是逃亡于社会的边沿,一个局外人,一个观察家,用一双冷眼加以观照。作家不必成为社会的良心,因为社会的良心早已过剩。他只是用自己的良知,写自己的作品。他只对他自己负责,或者也并不多担多少责任,他冷眼观察,用一双超越自我的眼睛,或者从自我中派生来的意识,将其观照,借语言表达一番而已。高行健:《没有主义》,第23页。
中国近、现代作家与信奉弗洛伊德学说的一些西方作家不同,他们的写作动力不是性压抑,而是“良知压抑”。在潜意识的展面上,他们的写作不是出自感官本能,而是出自精神本能。因此,中国作家对于良心责任的问题特别敏感。但是,现代中国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人人都想充当社会良心的角色,而整个创作却缺少应有的良知水平。根深蒂固的奴性,无休止地媚上与媚俗,既迎合政治又迎合市场,该说的话说不出来,不情愿说的话又不停地说。个个高喊解放全人类,到了必须具体地援救一个人,为一个人申冤时,却个个沉默。经历了良知系统崩溃和混乱的时代之后,高行健不顾被谴责为“丧失社会良知”的危险与罪名,提出上述观念,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