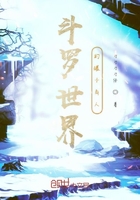“你……”祁尉听出了琦筠在哭,可是却什么都没问。这个女人这么要强,他又怎么忍心去揭穿她苦苦支撑的面具。
他略带迟疑,马上又问:“你现在在哪?站着别动,我马上去接你。”
琦筠抽噎了一下,报上地址,乖乖的坐在原地。
脚疼,腿也疼。
她懊悔今天为什么不好好的在家休假,非要学其他女人一样来当个购物狂,这下好了,购物狂当了,她也成全了别人,自己的提包彻底成了别人口里的小绵羊,可惜她却再也闻不到肉香。
自从十岁以后,除了生那对宝贝以外,琦筠再也没流过眼泪。不是她铁石心肠,而是她从很小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伤心还是难受,自己的眼泪流的真是什么价值也没有,流泪既不会减轻痛苦,更不会解决问题,所以它只不过是人自身的一种反应。她一项不做无用功,既然眼泪流的这么无价值,她就更不会浪费自己的身体热量去做这种黯然神伤的事情。
只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她真撑不住了。
“琦筠?”
没过多长时间,琦筠听到背后有人轻声唤她。她慢慢站起身,转身望着面前的人,不由得自嘲地笑了:“我太笨了是不是,出门逛个街都能被人把包抢了……”
眼泪一滴两滴地流了出来,落到她微笑的嘴角上,咸咸的,涩涩的,还有略带一丝甘苦。
祁尉沉默了好久,他说:“是,你太笨了,笨死了!”
他一把拉过琦筠紧紧地抱在怀里:“幸好你没有事,不然……”
他没有说下去,猛的像想起什么似的拉着琦筠上下打量:“你没什么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
“祁尉……”
“怎么了?”
“我脚崴了……”
祁尉撩起琦筠的裤脚,右脚已经一片黑紫,肿的已经不像样了。他倒吸了口气:“怎么会弄成这样?”
琦筠又笑:“我想去追坏蛋,可是我跑不过他……”
他慢慢蹲了下来,厉声说:“上来!”
琦筠一时没领会他的意图,愣在了原地。
“上来。让我背你还是抱你,你自己选!”
他生气了。
除了上次在她家的争吵,琦筠还从没听到过祁尉用这么大分贝的声音跟她讲过话。不过不是抑制不住的怒火,恐怕他不会这么暴躁。
琦筠趴在他的背上,摸不清他究竟为了什么发火:“对不起,还麻烦你来一趟……”
祁尉背着她的脚步停了一下:“停止你的胡思乱想。孙琦筠,你还能不能记得你是个女人?整天要强的要死要活的干就不说你什么了,遇到今天这样的事情你能不能把你自己当个女人看待?包丢了就丢了,报警就是了,大不了不要了,权当破财免灾,你说你一个女人还去追抢匪,你追上了又能怎么样?你知不知道他们手里有没有刀?你出了事情让别人怎么办?”
祁尉从来没用这么义愤填膺的语气说过话,这席话就像是他在心里憋了很久似的突然之间全被他释放了出来。他说的很快,可是很长时间却没得到背上人的回应。
渐渐地,他衬衣的肩膀上湿了。
祁尉一愣,是他说重了吗?他想开口安慰:“对不起……”
“祁尉,谢谢你,谢谢你能来,还有……我累了,能不能借我肩膀靠一下?”
他慢慢地点点头,说:“好。”
琦筠把头埋在他的肩膀上,不重,但很暖。
她闷着头唤了一声:“祁尉。”
他轻声询问:“恩?”
她说:“我脚疼。”
他答:“一会回家给你治。”
她说:“我腿也疼。”
他答:“忍一下,一会就到家了。”
她又说:“真的很疼……”
祁尉托着她的手微微紧了紧:“下次疼也好,饿也好,累也好,别闷在心里。打个电话告诉我,大不了电话费我给你出。”
在琦筠心里,这是种很压抑的发泄。今天的这种伤,其实未必会在她身体上造成多大的痛楚,可是却于无形中加剧了她内心的痛——或者,不如说是种孤单。
如果没有祁尉,她今天会不会哭?
也许会,可是绝对不会让她眼泪流的如此肆无忌惮。
她把头靠在他的肩头,她从来不觉得他是和高大魁梧沾边的男人,可今天却觉得他的肩真的很宽很宽,至少能容得下她这颗无助的头脑,架得住她这疲惫的身躯。
琦筠一路就这么胡思乱想,可她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想要理清些什么。她被祁尉背上了了楼,一路上安安静静的,什么话都没说。
“怎么不说话?脚很疼吗?”祁尉背着她站在电梯里,“两个孩子一天没看见你,不定想成什么样了。”
琦筠缓缓抬起头,她看见电梯镜子里自己红肿的眼睛不由得在内心叹了口气:“你就这么出来了也不怕家里两个孩子闹翻天。”
“没关系。”电梯门开了。祁尉一边说话一边敲了敲门:“他们都大了自己在家一段时间没什么危险的,你应该放手让他们练练,他们早晚得自己学会生活……”
“妈妈,你怎么了?”晟睿打开门看着祁尉背上的孙琦筠不由得皱了皱小眉头,“妈妈你不舒服吗?怎么让被人背回来了?”
琦筠一窘,连忙挣扎着要下来,突地听见客厅里有人在里面大喊:“小子,没看见你妈生病了吗?别搅和你爸你妈,让他们慢慢折腾,过来陪爷爷我下棋!”
琦筠和祁尉俱是一愣。
祁尉看了看里面坐着的人难得地瞪大了眼睛:“您这是……”
“我们是对门的邻居,上次孙小姐应该见过的。”祁尉的话被人打断了,她又说,“你们要是不嫌弃可以称呼我们家老头叔叔,叫我尹阿姨就可以了。”
祁尉哭笑不得。
他背着琦筠走过去,轻轻地把她放在沙发上,然后才回身说:“您什么时候来的?”
“我们昨天来的,就住对门,怎么,你小子想查户口吗?”
老爷子胡子一吹眼一瞪,盯着祁尉没有好气。
祁尉扫了一眼茶几上的棋盘,连忙整理了一下笑容:“怎么会,欢迎您二老常来这里做客,我们不胜荣幸。”
“你们?”老人笑着落下了一子,“这是你的家?丫头这是你什么人?”
“我是她先生。”祁尉抢着说。
“我没问你,注意你的涵养。”他捋了捋胡子,指着琦筠问,“丫头你说,她是不是你的老公?随便弄一个陌生人进来可是不好的生活习惯。”
祁尉紧张地看着琦筠,生怕她答出什么其他的答案。
“他就是爸爸啊,爷爷你为什么这么问啊?”可馨挤在老人身边,调皮的扽了扽他的胡子。
众目睽睽,琦筠只得说:“是,他是孩子们的父亲,也是我的先生。”
“这就好。”老人点点头,把手里的最后一步棋走了出去,将军。
“落棋无悔!”他站了起来,笑容可掬地招呼着,“老伴,和孩子们玩够了,咱们也该回家去了。”
“您的棋盘……”
老人对琦筠潇洒地挥了挥手:“放你这吧,改天我再来玩。”他又突然回头看着祁尉笑了笑:“没事多和你儿子下下棋,这东西可益智啊!”
说完背着手,哼着京剧摇头晃脑的走了。
祁尉看着两位老人离开,不由得松了口气,可是转眼看见茶几上摆着的棋盘,又不由得头皮发麻。
琦筠见他表情怪异,还以为是对两位老人有意见,只能原原本本把上午发生的事情重复了一遍。
祁尉叹了口气:“该来的躲不掉。”
“怎么?”
“没事。我来看看你的脚吧,还疼吗?”
“有点。”
祁尉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瓶红花油,滴在手心里又搓在琦筠的脚腕上。
他说:“开始会有点疼,忍着点,我搓开了就好。”
“好。没关系,我这脚以前崴过一次,所以可以忍受。”
祁尉一边揉搓一边问:“以前你也伤过?”
“恩。”琦筠点点头,“有一次放学回家,结果在学校的楼梯上崴了脚,那时候还是骑车回家,这一道上蹬一次脚就疼一次,疼到后面我也没感觉了。最搞笑的是那阵子我家还住在顶层,我搬着车子一瘸一拐的爬上六楼,心里还挺自豪……”
“六楼?你搬着车子上去?”
“别那么大惊小怪。自行车是很容易丢的东西,你要是骑车我不信你从小到大没丢过一辆车子。”
“你那时候多大?”
“我忘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可能是小学,也可能是初中吧……”
祁尉沉默了,他想象不出来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崴着脚搬着车子往上爬是副什么心情,可她居然把这事当成笑话来讲。她看起来像黄油一样软,可是内心却像钢铁一样坚强。想到这他郁卒的加大手上揉搓的劲头,无意间抬头一瞥才看见她早已疼得煞白的脸和攥紧被子的手——即便这样她也没出一点痛声。
他不由得放柔了手里的动作,原来他真的是会心疼的。
他把她抱回卧室,替她盖好了被子:“你先歇一歇,一会我给你敷一敷。”
他转身要离开。
“祁尉。”琦筠却叫住了他,“谢谢你。”
祁尉好笑地看着她:“你今天说了多少句谢谢了?”
“除了我妈妈,没有人对我这么耐心过……”她有点语无伦次,“我只是想说谢谢,这是真心的。”
祁尉俯下身,捋了捋她额边的碎发,然后温柔地亲了亲她的额头,却只开口说了几个字:
“别担心,没事,有我在。”
什么是幸福?
没有什么甜言蜜语,也没有什么海誓山盟,在自己伤心落泪的时候有个声音会在面前暗暗地予以支持,这或许就是大家所谓的幸福。
真好。
琦筠伸出双手,拦住了祁尉的额头,回应性的亲了他。
祁尉一时愣住了,待反应过来眼睛都是在笑。
他反过来紧紧抱住她,一下子就吻了上去。两个人越拥越紧,呼吸渐渐的都浓重了起来,他的气息喷在她的颈中,灼热烫人,让她痒的难受。她微微轻哼一声,祁尉就像是得到鼓励,手灵活的滑进被子里,摸到琦筠柔滑的肌肤,让她觉得所到之处都如灼伤一般火辣。
在卧室这密闭的空间里,整个氛围越来越暧昧。软玉温香,娇柔旖旎,让祁尉渐渐迷失在其中。
突地,卧室的门被人“咣咣”砸了起来。
“妈妈,有人来了。”
“臭小子,你给我开门!”
琦筠一惊,她听出是对门老爷子的声音,连忙要挣脱祁尉,一时情急她脚下一蹬,祁尉唔了一声,弯着腰闪在一旁。
她倒吸了一口凉气:“祁尉,你没事吧……”
琦筠当然知道她踢到了哪里。她脸红的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可又怕自己真把祁尉弄伤。
祁尉被她问的面红耳赤,也不好意思看她,连忙躲到窗边。他拉开窗帘,打开窗户,深吸了几口气,然后若无其事地打开房门。
“臭小子,鬼鬼祟祟磨蹭什么呢!”
祁尉一开门就被劈头盖脸的埋怨一通。他还没说话,只见自己面前的老爷子又说:“听说丫头的脚崴了,我让人拿了点药来。就你那两把刷子还敢给人看病?到时候把这么好的媳妇弄伤了我看你找谁哭去!”
祁尉看了看自己面前的老人,又望了望在一旁看热闹的晟睿,他开始后悔,以前为何没和自己的父亲搞好亲子关系。如今看着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老子统一了战线,他自己倒成了光杆司令独自奋斗,他真是无力到想哭。
他微微一笑,接过老人手里的药:“谢谢,请问您还有别的事情吗?”
老人得意的一笑:“没事,我就是来和小孙子下棋的!”
老人拉着晟睿往沙发上一座,一副教育的模样开始讲解起来:“孩子,爷爷跟你说,这可是副宝贝棋盘呢。看爷爷给你变戏法。”
晟睿乖乖地坐在对面,只见老人三下五除二,把棋盘底部的装饰一拆:“在爷爷家里,这下棋,男孩子们可是必须会的,爷爷看你也喜欢就决定把这棋盘送你了。”
晟睿举着老人刚从棋盘上拆下来的,已经磨得锃亮的装饰问:“爷爷,这是什么东西?怎么被磨得这么滑?”
老人瞥了眼背后的祁尉,笑的意味深长:“这叫戒尺,这可是专门惩罚不听话的人用的大家伙,打起人来,啧啧,那叫一个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