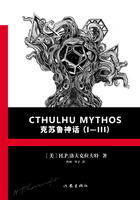我曾经爱过,笑过,哭过,/我曾经满足,也曾经失落,/现在,当泪水慢慢沉淀,我发现原来可以一笑置之。
——FrankSinatra的《我的路》。
家具都安置好了,原本空荡荡的房间看上去有了家的味道。
简雪长舒口气,指着新买的沙发对杨一道:“来,坐下歇会儿,忙了一下午,累了吧?”
“不累。”杨一笑着摇摇头,刚才帮着摆家具,累了一身汗,他想回家冲个澡,“没事了吧,那我走了。”
“别走,坐下歇会儿,等会儿请你吃饭。”
“不用了。”
简雪瞪了他一眼,“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矜持?你知不知道,成全别人也是一种美德。人家诚心诚意请你吃饭,你说OK就完了呗,哪那么多客套!”
“好好,OK。”杨一走到沙发旁坐下,环视着周围,“你打算什么时候搬家?”
“等下个月吧,刚装修完房间有味。”简雪说,也在沙发上坐下,把茶几上的矿泉水递给他,“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你要是不愿一个人吃饭,就来我们家入伙吧,我妈厨艺可好了,保你吃了这一顿,还想下一顿。”
杨一被她逗笑了,“你不会是为了想拉我入伙才买这的房子吧。”
“你别自作多情了,这个小区是真爱集团开发的,我家那片旧城区改造也是他们公司负责,旧房直接折价抵了一半房款,还给我优惠了10%,这么大房子一共才付了30万,都是天承哥的功劳,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他!”
“那还不好办,以身相许呗!”杨一打趣道。
“庸俗!”简雪愠怒道,抓起沙发上的靠垫向他掷去。
杨一伸手接住,放在身后倚靠着,笑嘻嘻道:“对,我就一俗人,你开着他的路虎,住着他的房子,让我这俗人怎么想?不把你当二奶就不做错了。”
“那他还给你介绍案子呢,照这么说你就是二爷了?”
“那不一样,我是律师,我得给他出力办案子,你做什么了呀?”
“我——”简雪噎住没话说了,有些气恼地看着他,“你给他办什么案子?”
“不知道,他说是他一个朋友,我觉得有点儿蹊跷,还没见过当事人,就付了五万元给我,他说律师费一共十万元,立案前全部付清,我还没接过这么大的案子呢。我最近霉运不断,好像要时来运转了!”
简雪也觉得有点儿蹊跷,十万元律师费不像是小案子,可那天吃饭时楚天承说案子不大,就是普通的民事案,但转而一想,也许在他眼里这点儿钱不算什么。于是道:“上帝很公平,不会让你总走霉运,你情场失意,商场得意。嘿,这回你得请我吃饭了。”
“岂止是请你吃饭,我得给你佣金。”
“你怎么这么俗啊!朋友之间谈什么佣金!”
“必须的,这是规矩。”
“必须个鬼呀!赶紧请我吃饭!现在就去,我饿了。”
“好好,说吧,去哪儿?”
“嗯,去个新地方吧,小南国都吃够了。我们边走边想。”
两人起身往外走。简雪掏出钥匙锁好门,和杨一进了电梯。
“对了,把钥匙还给你。房子装修好了,我不用再过来了。”杨一说,从包里拿出钥匙,这段时间简雪忙着策划节目,房子装修也顾不上,就把钥匙给了他一把,让他抽空过来望一眼。
“放你那吧,你早晨过来把窗户打开,放放味儿,晚上回来再关上。我大老远的来一趟不方便,反正你顺路,就麻烦你了。”
“好吧,”杨一把钥匙放回去,戏谑道,“我都快成你秘书了。”
“我可雇不起你,你一个案子就赚十万,都快成百万富翁了。”
“一百万算什么富翁?那是十年前的行情。现在物价上涨这么快,一百万顶多算个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有什么不好?富人有富人的麻烦,钱太多不是什么好事,你知道吗,现在新好男人的标准是,收入养得起一个家,养不起第二个家,这样就不能包二奶了。”
“这么说,我是新好男人了,那怎么还被人甩呢!”杨一自嘲道。
简雪不满地看了他一眼,“什么叫被人甩呀,婚姻和职业一样,需要双向选择。杨一,你不要总是这种消极心理,你应该这么想,我现在自由了,我可以重新选择更好的,”说到这,她忽然灵机一动,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道,“干脆,你上《挑女进行时》吧,我帮你物色个女嘉宾,找个80后,年轻漂亮,怎么样?”
“我看行,管她是谁,先牵手再说,免费去普罗旺斯度个假。”杨一笑呵呵道。如果是从前,简雪这么说,他不发脾气也得生闷气,但经历了逃婚风波,很多事情他都看开了,连性格和喜好也不知不觉发生变化。以前很不习惯简雪这种信口开河、口无遮拦的说话方式,觉得她是熟女扮少女——装纯,但通过这段时间相处,他发觉,她是天性如此,就是这种心直口快的脾气,好像透明人一样,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不像小柔,好像设了一道防火墙,有事总是闷在心里,让你半天捉摸不透。
人就怕比较,杨一现在越来越喜欢和简雪在一起,无论说什么她都不介意,不用赔小心,不用看脸色,嬉笑怒骂皆自然,他喜欢这种无拘无束、轻松自在的感觉。
两人来到地下停车场,杨一说:“我们开一辆车就行了,不过我的车可没你好,坐得惯吗?”
“那就开我的,有好车为什么不坐?我累了,你开吧。给你车钥匙。”简雪大大咧咧道,好像那辆路虎真是她的似的。
杨一喜欢她这股率真劲,他接过钥匙,他还是第一次驾路虎,好车就是给力,他不由得赞叹道:“真爽!”
简雪是那种你快乐、我也快乐的人,见杨一高兴,她也来了兴致。“那就让你多爽会儿,去海边兜会儿风吧。”
“你不是饿了吗?还是去吃饭吧。”
“没事,多饿一会儿,等会儿可以多吃点儿,你难得请次客,还不好好宰你一刀!”
“瞧你说的,好像我是葛朗台似的。”
“做葛朗台你还不够资格,你以为葛朗台随便就可以做的,那可是人间一绝!”
“哈哈,既然做不成葛朗台,那咱就奢侈一次!”杨一开心地道,掉头驶向滨海路。
滨海路是蓝城风景最优美的地段,一面环山,一面临海,蜿蜒的盘山路在山水的环抱中延伸开去,像一个怀春的少女恣意地舒展着美丽的玉体。时值初春,沉寂了一冬的树木发出新绿,散发出植物特有的清香,平整的海面也是蓝中透绿,涌动着一股暖暖的春意。杨一不觉放慢车速,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听着音乐。音响里播放的是简雪喜欢的FrankSinatra的《MyWay》。
……
我曾背负不能承受之重,但自始至终,就算充满疑惑,我还是克服困难战胜了它。
我挺直身躯,勇敢面对,用我自己的方式。
我曾经爱过,笑过,哭过,我曾经满足,也曾经失落,现在,当泪水慢慢沉淀,我发现原来可以一笑置之。
……
听着听着,杨一不禁被打动了,那浑厚饱含深情的声音,那朴实富有哲理的歌词,正是他此时的心情写照,从小柔弃婚而逃,到现在整整四个半月了,他背负着不能承受之重,心中仿佛压着一块石头,愤怒,痛苦,怨恨,沮丧,消沉,麻木……他经历了所有的一切,但还是挺直身躯,走过来了!是的,走过来了!走过来才发现,窗外依然有晴天!他望着碧蓝如洗的万里晴空,泪水情不自禁地涌了出来……
前面是观景台,他把车靠边停下,扭头望着窗外,静静地流泪。简雪默默地看了他一眼,把CD机音量调成最高,把播放模式选成单曲循环,然后轻轻打开车门,转身下车。
简雪走到观景台前,两手扶着栏杆,眺望远处的大海。波光粼粼的海面,光滑平整,像一张松软的地毯,把礁石和暗流埋在了下面。她多么像女人的情感,初始总是温婉柔和,妩媚动人,越往深进入,越强硬突兀,危机四伏,让男人浑然不觉翻了船。即使不溺水而亡,也是呛水求生。浮出水,已是经年。
可见,出水的未必是芙蓉,还有情场失意郎。银幕上的故事很少在现实中上演。生活不是电影,生活比电影艰难多了,正因为如此,人们才需要电影,需要各种高于生活的艺术。艺术有两大功能,满足人的意淫,或者借此疗伤。
此时,杨一坐在车里,用歌曲疗伤,开始只是听,后来就跟着唱,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嚎,就像一只受伤的狼。唱到声音嘶哑,筋疲力尽,终觉释然。
他把音响关掉,转身下车,走到观景台前。简雪回身看看他,“好了?”
“好了。”
简雪舒了口气,感叹地道:“知道吗,那张CD是我前男友的。那首歌是他最喜欢听的。”
杨一表示理解地点点头,问:“你还爱着他?”
“不!”
“那为什么还留着他送的礼物?”
“不是他送的,那是他的——”简雪回过身去,望着海面,语气低沉地道,“遗物。”
“啊!”杨一惊叹一声,想问什么,但忍着没开口。
“是车祸。”简雪语气平静、像是诉说别人的故事,“那是我刚去美国不久,我们相识才三个月,他就出事了,当时我在旅行社取机票,还有两天是我生日,听妈妈说,我出生那天下雪,四月雪,这在蓝城很少见,简直就像一个奇迹,所以给我取了这个名字。可惜后来奇迹再也没发生,我从来没在生日那天看过雪。他就说等我生日时,送我一个奇迹——陪我去挪威看雪。可惜,悲剧比奇迹先到。”
杨一叹口气,怜惜地看着她,“比起人为的分手,天为的分手更残忍!你当时一定很伤心,一个人在国外,怎么撑过来的?”
“不是伤心,是绝望!你知道什么是绝望吗,就是在死去男友的车里看到女人的高跟鞋——出事时他们在一起!”
杨一讶异地道:“怎么会?他对你那么好,他们也许只是普通朋友。”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可是他的手机里都是他们的短信,连个让我欺骗自己的机会都不给。”
“真是难以理解,你们才认识三个月,还是热恋期,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有第三者?”
简雪嘲讽地笑了,“其实我才是第三者,她是他原来的女友,因为爱上别人离开他,他很痛苦就来找我。我以为那就是爱,其实他只是用我疗伤。后来那个女人和新男友分手,又回来找他,他开车去接她,回来的路上发生车祸。她只是受了伤,反害他丢了命,自私的人总是命大,活的比别人长。”
“你就别记恨他了,原谅他吧,他已经为他的错误付出了代价。”
“我早就不恨他了。他出事后,我常常做噩梦,半夜醒来,一个人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内心充满恐惧,连空气都透着寂寞的味道,我实在受不了那种感觉,好想有一个人抱着自己,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他,也不再恨他了,因为我也做了和他同样的事——找一个人疗伤。其实人是很脆弱的,只是外表坚强而已。”
“那后来呢?”
“哪有什么后来?就像溺水的人抓一棵救命稻草,等你上岸了,也就不需要他了。”简雪带着几分惆怅,回过身来看看杨一,“那天我们在酒吧喝酒时,我不是对你说过,用新人忘记旧人,这是最好的疗伤方式。”
“可是这对新人不公平,既然不爱她,就不要去招惹她。”
“你这家伙,让我说你什么好?哪有那么多爱情呀,不过是在一起相互取暖。”简雪嗔怪道,静默了一会儿,又带着几许赞赏的口气道,“不过我还是挺敬佩你的,一个人走出来了。”
杨一笑笑,没言语。其实他不是没想过,也不是没有机会。有一次他一个人去酒吧,正好碰到吴倩,她已经喝得半醉了,满嘴喷着酒气说喜欢他,想和他在一起。他斗争了半天,还是拒绝了。她气得骂他:杨一你这个老古董,你是不是觉得和谁睡一觉,就得娶谁当老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告诉你,我不用你负责。他回答她说,你用不用我负责那是你的事,但我得对你负责。他怕她一个人在酒吧不安全,硬是拉着她出来,打车把她送回家了。
杨一不想和简雪说这段事,毕竟这涉及一个女孩儿的隐私。于是转换话题道:“对了,你快过生日了吧?”
“咦,你怎么知道?”简雪惊诧地道。
“刚才在你家,听你和莞尔打电话时说的。”
“噢,她这人心真细,还记得我生日,我自己都忘了,她说去普罗旺斯赶不回来,不能给我庆生了。”
“那正好,我给你庆祝。”
简雪撇了下嘴,“31岁,有什么可庆祝的,庆祝青春已逝?”
“31岁怎么了,我都34岁了呢。每个年龄有每个年龄的乐趣。说吧,想要什么礼物?”杨一豪爽地道,一副敢上天揽月的架式,见简雪俏皮地看着自己,赶紧补充一句,“别让我陪你去挪威看雪。”
“呵呵,放心吧,我已经过了相信奇迹的年龄,那是女孩儿玩的东西。”简雪有些伤感地道,忽的想起什么,“哦,对了,今天是他的忌日,在我生日前两天,我怎么给忘了。”
“噢,你想怎么纪念他?”
“嗯,就来一个为了忘却的纪念吧。世上没有未完的故事,只有未死的心。其实就算他不出事,我们也会分手,只是这种方式太决绝,才让我这么久放不下。现在该是忘却的时候了。”说罢,她向杨一要来车钥匙,她要把车上的CD取来,为昔日的恋情划上最后的句号。
杨一望着她的背影,犹豫了一下,快步跟了过去,拿起车上的公文包,取出一张U盘。
“这是什么?”简雪问。
“情书。”杨一苦笑了一下,“我们分手后,我把她的东西都还给她了,只有存在电脑里的情书没舍得删掉,存到U盘里了,你刚才的话提醒了我,不留它了,就在这为它举行一个海上葬礼吧!”
简雪点点头,微笑着道:“男女间的感情,都是一段一段的,起的作用也不同,有的人,是用来疗伤的,有的人,是让你成长的,有的人,是让你去爱的。爱情也有生命周期,到了无法挽留的时候,与其痛哭流涕,不如洒脱一点,优雅地告别。也许爱的时候不够完美,但结束一定要有风度。”
“你说的对,再好的东西,也有消失的一天,再深的记忆,也有淡忘的一天,再爱的人,也有远走的一天。该放手的时候,就不要挽留。该谢幕的时候,就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两个人顺着观景台一侧的阶梯,来到山角下海滩,杨一挥手把U盘扔进大海,满载着昔日情感的小小U盘,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抛物线,砰的一声落入水中,击起一片小小的水花。
简雪嗔怒地看着他,“你急什么呀?这哪是海葬,这是丢东西呢。”
杨一望着远处的大海,神色黯然道:“葬礼就是丢东西——丢了一个生命!”
“所以要搞个仪式,生命这么宝贵的东西,不能这么随便丢哇。”
杨一回头看看她,“什么仪式?这又没乐队,没法演奏《葬礼进行曲》。”
简雪其实也没想好怎么做,他这一说反倒提醒了她,“OK,我要选个曲子。”
她在手机上翻找着,“就这首吧,《Time to Say Good bye》(告别时刻)。”
在莎拉·布莱曼舒缓深情的歌声中,简雪将手中的CD轻轻放入水中,一阵海浪涌来,CD漂走了,越漂越远,渐渐消失在远处,再也看不到了。
只有莎拉·布莱曼和安德烈·波切利的歌声,回响在空荡荡的海面。
……
是时候该说再见了
我们之间不要如此再继续下去了
是时候该说再见了
你伤透了我的心,我要离开你
所以,现在是时候说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