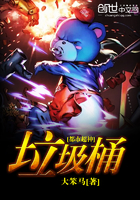嘈杂纷乱的声音不断的钻进耳朵,意识一点一点的恢复过来,一诺知道自己还活着。动动手指,又动了动脚丫,还好四肢健全,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被毁容。
懒懒的赖着,好像经历了一场马拉松一样,全身软的没有一点力气。回想起刚才的经历简直是生不如死。
早知道会有这么痛苦的一个过程,打死她都不会来。好久,体力恢复了一些才揉着眼睛坐起来,就在这时,面前居然闪过去一个——粉色身影!
一诺诧异的张大嘴,露出八颗以上洁白的牙齿。
之所以震惊不是因为那是个女人,也不是因为她年轻漂亮,而是因为她居然穿着古装从自己面前经过,好像赶着去赴约。
难道现在在横店?
一个念头闪过,自己被那两个无良青年給耍了。他们弄晕自己,再给自己换了古代的衣服丢在横店,就是想看看一个人在突发事件下有什么反应。电视里曾经制作过一档节目,就是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有的甚至給她安上另外一个名字,来测试人的承受能力。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一个人说那牛是马,它不是马。一万个人说牛是马,那它就是马。
想到这,一诺迅速爬起来寻找隐蔽在四周的摄像机。等着我混蛋,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两个!
顺着小巷找出来,没有找到一台摄像机,倒是找到一堆群众演员。他们都跪在道路的两边,想抬头又不敢抬头的样子,神情紧张又卑微。
一诺悄悄加入他们,轻声问刚才那个穿粉色衣服的女孩,“美女,你们拍的是哪部戏?”那个女孩用奇怪的眼神看了一诺一眼,低下头不说话。
一诺继续问:“你们的盒饭标准怎么样,有没有肉菜?”
估计那个美女也爱吃肉,听到这么一问再次抬起头看了一诺一眼,这次的眼神跟刚才有所不同,上上下下的打量几遍却始终没有说话。
一诺刚要继续追问,道路的尽头就传来铜锣的声音,所有人都匍匐在地上,安静的等候。
头前两个穿着衙差衣服的人敲着铜锣开道,身后有人高举着回避的牌子。队伍的中心是一顶八抬大轿,四角还垂着类似灯笼穗的东西左右摇摆。
一诺托着下巴默默猜测,轿子里会是个王爷还是个将军,要不然就是个神探知府?也不知道是请的哪个大腕,一会儿让他给我签个名,最好是能合个影。
正在臆想的时候,一只利箭嗖的一下钉在轿门上。
哇偶,还真专业。
感慨还没结束,无数支利箭就像雨点一样射过来。身边的人群惊叫着四处逃窜,一诺真儿真儿的愣住了,这导演太拼了吧!
瞬间,轿子就被射的像刺猬一样,轿子里的人绝无生路可言。四周突然窜出几个黑衣蒙面人,侍卫们动作迅速的迎上去,跟蒙面人打斗在一起。
其中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男人与众不同。他英俊的眉宇间带着千层杀气,双眸冷若冰霜。他使用的兵器也不是一般的刀枪剑戟,而是一把大号的扇子,打斗间一开一合都恰到好处。
一个蒙面人挥剑扎向紫衣人,紫衣人手中的扇子一开,宝剑从扇子的缝隙里穿过,差一点就刺到紫衣人。只见紫衣人手中的扇子一个旋转,轻松的卸了蒙面人的宝剑。
同时脚下一踢,蒙面人便以抛物线的方式远远的飞出去,正好落在一诺面前。
蒙面人的胸口不知道被什么划破,涌出大量的鲜血,艰难的扯下面巾一脸痛苦的望着一诺,刚要说话,嘴里就涌出刺眼的红色,连雪白的牙齿都染红了。
这得含多少血包才能有这种效果。
既然已经出戏,那走过去应该不会妨碍导演。这么想着,一诺已经走到他的身边,刚想夸他演技好,脚脖突然一疼。低头发现蒙面人死死的抓着自己,嘴里含糊不清的说着什么。
一诺虽然不晕血,但是这么大量刺眼的颜色还是令她不自觉的皱起眉头。
扑鼻一股腥味,很浓,浓的让人想吐。他颤颤巍巍的把什么东西塞在一诺手里,然后就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头一歪就不动了。
这个剧组还真专业,看看这服装,看看这道具,还有刺鼻的鲜血…每一样都非常精准。
“喂!你演戏上瘾啦。”一诺摇摇他,他毫无反正的倒着。看到他狰狞的五官一诺的呼吸一怔,心跳陡然加速。手下黏黏的液体怎么还有温度,而且还源源不断的涌出来,他身下的鲜血足足有2000cc了,一个正常人如果这样……
一诺慌乱起来,伸手按住他胸前的伤口。可是伤口是长条状,按住上面,下面出血。按住下面,上面又冒出血来。不管她怎么做都无法阻止热热的鲜血涌出。
鼻子发酸眼泪竟然涌出来在眼眶里打转。四处张望着求救,周围只有打斗的侍卫和蒙面人人,围观的闲人只有她一个。
那个紫衣人纵身跳到一诺面前,大号的扇子直指她的眉心,片刻,扇尖那锋利的刀片唰的一下缩了回去。
原来那个扇子上有玄机!
“快救救他,他快死了!”一诺冲着他大喊,另一只手也顾不得攥着东西,紧紧按在伤口上。
剧组出现意外是常有的事,可是演员间这么冷漠却不常见。
一把利刃突然架在一诺的脖子上,冰冷刺骨的感觉吓得她呼吸一窒,那锋利的利刃瞬间削掉一诺颈侧的一缕头发,剑锋一偏作势往下压去。
只要他压下去,一诺的脑袋就会立刻搬家。就在这时,那个紫衣人单手一立做了个停止的动作,长剑立刻离开她的脖子收回宝鞘。
一诺含泪瞪着那个紫衣男人,眼中充满怨恨。为什么他们这么冷漠,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死在他们的面前,他们竟然没有一丝怜悯。
紫衣人冷峻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淡漠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快救人呀!”一诺再次怒吼,眼泪夺眶而出。
他漠视着,不仅没有加入救援反而冷冷的说了句:“把她带走。”
刚才那个侍卫一手拿剑一手抓住一诺的胳膊,就像是拖死狗一样把她拉扯起来。
一诺不甘心的回头看去,地上的尸体渐渐僵硬冰冷。她像疯了一样连跳带叫:“你放开我,你这个滚蛋!畜生!杀人魔王!你放开我……”
她极力挣扎,使劲蹬着地面不肯配合。可是那只手好像铁钳一样,无论她怎么挣扎也逃不出被拖走的命运。
一诺突然转头,狠狠的咬在那侍卫的手背上,嘴里一股咸腥。可是那个侍卫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手劲更大的钳着她的胳膊。
她无计可施,又破口大骂,凡是记忆中最恶毒的词汇统统搬出来,诸如混蛋!流氓!蠢货………
正当她骂的过瘾的时候,前面那个紫衣人调转回头,本以为他动了恻隐之心,谁知道他手掌一立砍在一诺的脖颈上。
等一诺再次有意识的时候,竟是趴在冰冷潮湿的地上,她闭着眼睛继续‘昏迷’。脑子里把发生过的事情重新回忆了三次以上,得出以下结论。
一,发生的命案不是意外。
二,这里不是横店。
三,她到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四,自己现在被关在牢房里。
正当一诺考虑自己的人生方向时,外面响起了走路声,脚步很沉稳,不急不躁。
“爷,您怎么来了。”牢头殷勤的巴结着。
一个干练的男声冷冷的问:“醒了吗?”
那个牢头回了句‘还没’,就传来铁链的松动声。牢门吱呀一声被打开,一双黑色的靴子出现在一诺眼前。
倏的,一柄长剑抵在鼻尖,她几乎可以闻到一股冰冷的杀气,冷漠的男声吐出一个字,‘杀!’
宝剑后撤,蓄满力量,准备再次刺下来。一诺猛地睁开眼睛,一轱辘坐起来,没好气的说:“就知道打打杀杀,有没有斯文一点的招数?”
说这话的时候一诺相当的没有底气,可是现在求饶似乎也没什么意义。
眼前站着两个人:紫衣人手中拿着那把大号的扇子悠哉的扇着。他的旁边站着那个被一诺咬伤的侍卫,手里还提着一柄寒气逼人的宝剑。
紫衣人身材挺拔,气宇轩昂。就是周身上下没有一丝生气,冷冰冰的像个大冰块。
他见一诺坐起来,冷哼一声,“醒了?”
一诺惊讶的瞪着他,难道他发现自己是装‘死’了?他用脚尖点了点地上,一诺立刻明白。
刚才趴的地方,有一小块地面非常干净,是没有灰尘的。一般昏死过去的人呼吸都很微弱,是不会让地面上的灰尘改变方向。
而自己非常有力的呼吸,把地面上的树叶和灰尘都吹干净了。
想到这脸颊微烫,掩饰的咳了下,从地上站起来。仰着头看人太累了。
“你干嘛滥杀无辜,他也是人耶!”一诺边揉脖子,一边埋怨起来。
他看了看面前这个脏兮兮又满手污渍的女人,冷冷的说:“他杀我便是应该?”
这个大冰块就不能多说几个字吗?每个字都冷的要命。
杀你?一诺蓦地睁大眼睛,那个蒙面人要杀他?他不是个侍卫吗?那个轿子里……
脑子又混沌了,智商是硬伤啊!
一诺对他摆摆手,让他停顿一下,给自己思考的时间。
她一边嘀嘀咕咕,一边走来走去:“如果那个蒙面人要杀他,他就不是侍卫。如果他不是侍卫,那么他就是应该坐在轿子里的那一位。他本应该是坐在轿子里却跑到轿子外充当侍卫,那么,原因只有一个。他早就知道有人要杀他,所以用了招狸猫换太子这招,那轿子里的狸猫不是……”脚步突然停顿,心又噗通噗通的跳起来。
“轿子里没人。”大冰块听到她自言自语,冷冷补刀。
一诺长出一口气,还以为又枉死了一个呢。
咦,他也不是很没人性。有了一点点好感,又重新审视他。
白皙的肌肤上镶嵌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可惜是冰水,看上一眼就能把人給冻死。直直的鼻子下配有一副浅粉色薄唇。看面相就可以肯定是一个高傲自大冷酷无情的人。
仔细一看他的衣服跟侍卫的有很大差别,紫色的衣袍腰里系着一条金鱼袋。
纵观全体,一个字,冷。
大冰块被一诺这‘火辣辣’的视线看的很不舒服,许久才憋出一句:“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