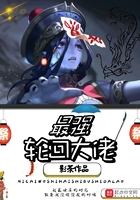这一日,孟古青正在坤宁宫中闲的发慌。前些日子还想着向云碧、怀心她们学了刺绣来比划两下。怎奈绣来绣去,连一个完整的帕子也绣不出来,还被怀璧狠狠地笑话了一通,便索性丢了女红的活计,每日不是看些书打发时间,便是闲来发呆。
坤宁宫的宫人们跟着孟古青伺候时间长了,性子便都活泼了起来,连胆怯的怀心,也不再拘谨,偶尔也会说一两句玩笑话,不时引得众人笑的肚子直疼。
宫人们里里外外的忙着,只有孟古青无趣的紧,伏在案上读了两句诗,便再也念不下去,正在昏昏欲睡,却不知道什么时候,顺治竟站在了自己的面前。
吓得孟古青花容失色,跳着起来向外面望道:“你……你什么时候来的,怎地也不见怀璧她们在外面说一声,我好准备一下。”
顺治戳穿她:“准备什么?你是想有时间擦掉你嘴角的口水吗?你是在拿着这《诗经》助眠呢吗?”
孟古青又羞又窘,通红着脸,便随手拿起旁边的帕子去擦自己的嘴角,却发现什么都没有,才知道被自己被顺治戏弄了。
顺治也是不见外,趁孟古青不备,从她手里抢过帕子,细细端详:“咦,你这帕子造型倒是别致的紧,人家都绣个出水芙蓉、鸳鸯戏水什么的,你怎么偏绣了个字,竟然还是半个字。”
孟古青欲夺了帕子回来,却奈自己的力气没有人家大,自是抢不过人家,便只能生受了人家的嘲笑道:“往好听了说,本姑娘不喜欢那些俗气的花样,准备自己绣个与众不同的;实话实说,我笨手笨脚,并不会那些繁复的花样,只能绣个字以作标识,还没绣成。”
孟古青以为依照顺治的脾气,定还有一大堆的话等着奚落自己,却没想到顺治细细看了后,认真地道:“丑是丑了些,不过还真的挺特别的,哪天你若得了空,便帮朕也绣一个带名字的,朕一定日日带着。”
孟古青不知他真假,只含糊着答应。
而后才想起来,顺治平日里在宫中各处行走,后面尽是随行伺候的,今日却怎的只身一人来了坤宁宫。便问道:“皇上你今日是怎么了,怎么这副神神秘秘的样子,吴良辅呢?怎么没有跟着伺候。”
闻言,顺治却是情急之下,捂住了孟古青的嘴,示意她不要声张道:“吴良辅已经在外面候着了,今日朕要带你出宫去见识见识。”
顺治一副哥俩好,我这有什么好事都想着你,你是不是也该夸夸我的表情,孟古青也不介意他的邀功请赏,只拼命点头,真是刚刚瞌睡,便有人送来了枕头,自己这里正闲的发慌,便有好事上门。
因怕露馅,孟古青便唤来了怀心怀璧,要怀心扮作自己的样子在寝殿里面,怀璧守在外面,若是有人来便一律挡了回去,若是太后差人来,便能拖便拖,一切等自己回来再做计较。
怀心初遇这样的事情,紧张的不得了,一个劲的劝着孟古青不能出宫,于礼不合,也容易失了一朝皇后的风范,若是出了事情,这阖宮的人更是万难承担。
怀璧却是一副心大的样子,只是遗憾主子这次不带自己出去,便嘱咐主子看见了好玩的一定要记得给自己带回来些,也好让自己开开眼,见见新鲜玩意。
顺治在一旁看两人的反应,心里暗叹,什么样的主子什么样的宫人,想必过不了多久,怀心说不定也能向孟古青、怀璧这样,全然不将祖宗礼法放在心上,只一心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终于,当孟古青安慰了怀心、答应了怀璧,便随着顺治匆匆的出了坤宁宫与吴良辅会和,都换了寻常装扮,只是孟古青此次却再不是男装打扮。
孟古青问起吴良辅,为什么这次没有像往常一样,给自己备了女子的衣服,吴良辅却是看了顺治一眼后,支吾不言。
顺治打着哈哈道:“你这面皮忒为白净清秀,每次与你走在一起,别人总疑心了朕有断袖之癖。”
孟古青闻言,只当他是矫情,也不深究。却不知道,顺治却是藏了自己的小心思,他希望有一日,她能以女儿家的身份站在自己身边,再没了那些身份牵绊,没了那些簇拥的宫人与吵嚷的妃嫔。
出了宫门,孟古青却全然没了往日那无精打采的模样,开心地直转圈。
顺治见她这般没心没肺地大笑,突然没来由地心痛起来,自己想日日都能见到这样笑靥如花的孟古青、想时时都能见到此刻这个天真明媚的孟古青,可是只要自己有一日还坐在那龙椅之上,只要自己有一日还是这天下之主,孟古青就要同自己一样,被困在紫禁城的方寸之间,穿上华服、戴上面具,成为没有七情六欲的皇后,被仰望、被供奉,却失了血肉,失了最简单的快乐。
可是,如果让自己放手呢?如果让自己在此后的余生里,日日不得见孟古青;如果山高水远,自由的孟古青却再与自己无一丝一毫的牵绊与瓜葛;如果长路漫漫,陪在孟古青身侧,守在他身边,见她如此笑颜的是另一个;如果他日,自己再像以前一样,偷偷地立在坤宁宫的墙外,却再也听不到里面的嬉戏打闹,想到这些,顺治便有说不出的难过与心痛,就像自己最宝贝的东西,却碎成粉齑,再难复原。
孟古青自是不知道顺治心里的这一番计较,只一个劲的催着吴良辅将马车驾的快一些,再快一些。
孟古青原以为顺治会带她往热闹的地方去。不曾想,吴良辅驾着马车,径直向前,竟一路来到了城外。
当马车停下来,眼见的眼前竟热闹非凡,人群蜿蜒,有序的向着前面缓缓行进,孟古青站在队伍最后面,向前望着,好奇地问道:“这是什么地方?我们怎地来了这里?”
顺治见到眼前场景,却是颇为矛盾,黯然地道,“这是望月楼在京中设的善堂,听说平日里便总是给贫苦百姓施粥赠药,如今逢了大旱,这望月楼的东家竟然在城内城外,都搭了赈济的棚子,让难民们能够填饱肚子,也亏得这望月楼的老板,这京中才不致闹出什么乱子,朕枉为天子,朕的子民,竟要靠一个商贾去赈济。朕的户部,竟然买不起粥药。”
顺治越说越激动:“亏得那些大臣们,还要朕厚着脸皮下旨,要望月楼出银子,好在春耕之时从南方运些种子过来。”
其实这些事情,去望月阁中买醉的达官贵人们早已议论了起来,还有人将这些消息作为人情,卖与莫愁莫苦。自然,孟古青也知道,顺治已在朝堂上将出了这混账主意的大臣骂了个狗血淋头,并警告大臣们,望月楼虽为一介商贾,但赈济百姓、疗治民众,已是善心仁举,若是有人起了那不该有的心思,定严惩不贷。这才息了某些人的心思。
只是,望月楼是孟古青最后的退路,自不可能轻易的便向顺治和盘托出。况且顺治说的这些,自己早已尽皆知晓。此刻,却只能装作第一次听说的样子。又想着如今已有人打起了望月楼的主意,须得想一个一劳永逸的法子,便斟酌着、状似无意地对顺治道:“皇上若是想保了望月楼,大可赐个牌匾,虽是抬举了他们商户,却也算是赏了他们为国为民的一片心意。至于那点散碎银子,凭着皇上您的宏韬伟略,户部定有钱粮充盈之时。”
这一番吹捧,孟古青可真是使劲了全身的气力。
顺治听罢,回头看了孟古青一眼。孟古青顿时心虚地道:“我知道祖训,后宫不得干政,我这就是随便一说,你也是那么随便一听,咱们都当不得真的。不作数……不作数的……”
顺治却开口道:“你这主意出的好,望月楼了了朕的一桩心事,朕还正在愁拿什么赏他们呢,你便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主意。”
孟古青与顺治正在这般闲聊着,猛然听到旁边起了争执,原来一个壮汉,欺前面排队领粥的一妇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想要排到人家前面去。那妇人欲忍让,那壮汉却愈加的嚣张,推搡间,竟将那妇人的幼子推倒了去,稚子年幼,却是除了哭泣,别无他法。
孟古青不忍见得如此情景,更不忿那壮汉恃强凌弱,便上前将那壮汉推开,将那幼儿扶起。
壮汉见有人打抱不平,原还有些犹疑,待见孟古青却是女子,便嘴上不干不净地道:“呦,原来是位小美人啊,怎么地,想要哥哥好好疼疼你吗?”
孟古青自来也不是好惹的,冷冷道:“望月楼的粥药,是要舍给那些老幼病弱之人,你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却也来这里白吃白喝不说,竟还无耻地欺凌妇人与幼儿,你真是……真是无耻地紧。”
孟古青到底是不习惯怕人,憋了许久,才憋出了一句无耻。
那地痞壮汉却是全不在意,更大了胆子,涎着脸道:“爷还就喜欢你这带刺的花儿,有味道。”这般说着,那双眼睛就更加不安分的朝着孟古青的身上打量。
顺治见不得孟古青被人如此调戏,欺身上前,便将那地痞的下巴卸了,只呜呜着不能说话。
吴良辅眼见如此,还在一旁风凉道:“主子,这可怎么是好,这些事,原是奴才做惯了的,这次却要主子亲自出手,若是脏了主子的手,奴才万死难辞其咎。”这般说着,吴良辅竟还一本正经的向自家主子请罪。
顺治也不答话,只示意吴良辅将这壮汉扔出人群去。孟古青也深究,只心里想着,回去了便要传信给怀仁,万不能让这等无形无状之人混了进来,且下次见到这地痞一次便要打一次。
这边主仆三人解决了地痞,人群里一声一声的叫好,让顺治的心情颇佳。
孟古青上前扶起哭泣的妇人与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倒还懂礼,都怯生生的向孟古青道谢。“谢谢少爷小姐救命之恩。”
孟古青却是心疼他们如此早慧,“这点子事,不值得放在心上的,你们可还好,有没有受伤?”
孟古青不问还好,这一问,两个孩子就都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原来,她们母子三人都是京郊的百姓,只因大旱,地也种不了,粮食也早没了,不得已便出来逃难,直至到了京城,遇到了望月楼,才日日得了一口饱饭。而这妇人,因为旧疾发作,两个腿已是勉强撑着,走不了多远的路。刚刚却又被那壮汉欺凌,腿脚便更为不便。
顺治与孟古青便要送妇人与孩子回家,妇人却是想着还要领取粥药,不肯离开。顺治无奈,便将吴良辅留下,为她们领取粥药,自己与孟古青送她们母子三人回到稍远的住处去。
待离了那施粥处,人便越来越少。孟古青觉得哪里不对,却又说不出来,只想着顺治却是千万不能出事,否则要有多少人遭殃。
正是这一分神,才猛地听到一声哨响,定睛一看,才发现那病弱的妇人竟不知从哪里变出了把刀,挥刀便向顺治砍去。
而四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竟埋伏了许多人,妇人的这一声哨响,却是都将他们唤了来。
那妇人口中道:“鞑子皇帝,我今儿非杀了你,为这天下的汉人报仇不可。”
顺治险险避过,敌人众多,还要分神看顾孟古青,只剩下了招架之力。顺治心里还想着,自己这天下之主,名正言顺,便忍不住出言反驳道:“如今满人入关已有数年,朕也重用汉臣,将来满汉终会成为一家。”
孟古青却是顾不得许多,只一心想着护着顺治,便也不知从哪里生出来了许多气力,只站在顺治身后,谁若是靠近,便疯了般的砍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