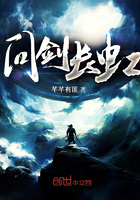每一次即将过年的时候,总能在朋友圈里体会到各种兴奋,大家对即将到来的新年满是憧憬。无论是生活中的还是QQ里的好友,都快乐地计划着要买些什么、做些什么。左邻右舍的一见面,总要相互问候一下过年如何乐,一打开电脑,屏幕上也满是好友们恣意吐槽的口水,似乎人生一切的快乐就指望着过年了。盼望着,盼望着,年来了。可是耳朵里听到的不是高兴,反而却是埋怨,埋怨现在这年过得没意思,没年味了。
大家既期盼着过年,又觉得过年味同嚼蜡,没有年味。这种期盼与现实的反差,着实有些奇怪。不过,扪心自问,我确实也有同感。我是个爱问为什么的人,于是突发奇问,什么是年味呢?我试图努力地从众人的评说中得出一个概念来,在今天的这个时候,算是有了一个总结。
年味首先是吃。
二十多年前,也就是在我刚记事的时候,对于普通的农村人家,虽说温饱问题已不成问题,但一年到头也就是混个基本的温饱,谈不上有什么讲究。
就吃而言,早餐总是稀饭,红薯稀饭、南瓜稀饭或者就直接是白米稀饭。菜呢,一律都是腌制的咸菜,腌豇豆,腌白菜,腌萝卜等等。腌白菜、腌萝卜还可以,唯有生腌的豇豆很难吃,因为是生的,所以有一股植物的清气,是小孩子最讨厌的那种味道。最好吃的要算是腌菱角了,在菱角没有长成熟的时候,把它从池塘里捞回来,用清水反复浸泡洗若干遍。因为菱角会吸附池塘里的淤泥,所以特别脏,洗头几遍的时候,总是把一盆水洗得和墨水一样。
反复洗几遍之后,水的颜色才会渐渐淡下来,直洗到清水不变色才算是洗干净了。若不洗净,便会碜牙。这时候的菱角还没成形,两头细中间粗,看上去有点像鸡大腿,我们都称之为“癞蛤蟆腿”。不仅看起来像肉,吃起来也有肉的感觉,软软的还带点脆,所以一到菱角初长成的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下河去摘。在没有肉的日子里,它给了我们美好的感觉。如果长期的吃,牙齿就会被菱角的浆染得发黑,像是抽了十几年的香烟。但那个时候的人想到的不是美容,而是美味。
而且,就这样一道算不得美味的美味,也不是家家户户常年都有的。有些人家农忙时节菜都吃完了,餐桌上只有豆腐渣和豆腐乳了。午餐和晚餐吃点干饭,自然是不成问题,有时候农活太重,下午在田间地头还要加一餐。只是下饭菜多数也是沿用早餐的,最多摘些屋前屋后的扁豆、丝瓜凑凑数。
在这样的饮食规格下,大家对吃都有一种期盼。早晨牛奶鸡蛋,晚上点心水果,天天鱼肉荤腥,偶尔牛排西餐,这样的条件自然是想象不出来的。不仅见所未见,而且闻所未闻。大家所期盼的只是能吃到肉,哪怕一点点也好,小孩子尤其是这样想。农闲的时候,这种想法更强烈了。因为那个时候,做卤鸭的、做豆干的都有空摆弄一下手艺,将做好的烤鸭、香干放在担子里,然后挑着走村串巷的叫卖。当串到我们村子的时候,只要我听见那吆喝声,便飞也似地贴上去。
我喜欢闻那卤鸭的味道、香干的味道,我想吃,又怕被人家耻笑为“好吃包”,于是跟着担子后面偷偷地深呼吸,我觉得那样就相当于吃过了。有时候也走在担子前面,给卤鸭师傅做向导。当然这个向导是有意图的,是希望把卤鸭师傅引到自己家门口。即便动了这么深的心机,吃上卤鸭的机会也只有四分之一。因为有时候卤鸭师傅不听我的话,就算他听了我的话,跟我走到家门口,父亲也不一定买。相对于父亲的薪水来说,一餐卤鸭已是比较奢侈了,煮熟的鸭子常常就是这样飞走的。
看着我面对青菜扁豆的那种不高兴,父亲有时候是训斥我挑食,有时候也用他当年吃草根野菜的经历来安慰我,证明我是生活在天堂里。但我毕竟不是阿Q,这种相对论的幸福观,是不能扑灭我心中对卤鸭的向往之火。其实不但是我,举世皆然。有一次,村里的小伙伴们在讨论肉有多好吃,一人说:“肉多好吃啊,就算是稻草炖肉都好吃。我长大了挣钱天天吃肉。”然而,现实总是很骨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丰满起来。
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在忙吃,磨豆腐,磨辣酱,做米酒,做挂面,炸麻花,炸肉丸,杀猪杀鸡熬糖浆,腌鱼腌肉灌香肠。这些吃活,多数在除夕之前十天半月左右就开忙了。磨豆腐、炸麻花、做挂面都是技术活。其中挂面最好吃,挂面有点像西北的拉面,但比拉面细,二者口味迥异,且做法不同。挂面是用盐水和出来的,面条也不是平拉出来的,而是挂在架子上竖着拉。挂面是个神奇的面,如果面和得不好,粗粗的面条挂在架子上拉不动,等到你不拉了,一会儿它又全都断了,所以做挂面要请内行才能做。
家家户户都做挂面,正月里早餐吃挂面,拌上猪油,加个鸡蛋,感觉实在太美了。做米酒熬糖浆,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由于做得多,大家都相互帮忙做。至于腌肉腌鱼,更是司空见惯,就算是没有养猪的人家,也会买上半缸肉腌起来,上面放块石板压着。大约估摸着腌得差不多了,就用绳子串着,一块块地挂在屋檐下风干,家家户户的墙上都挂得琳琅满目。这个时候,空气里充满了美食的味道,弥漫在整个年里。这种味道,令人难以忘怀,朋友每每与我谈起,总有一番慨叹:“那时候的年可真叫个年啊!”我想这就是他说的年味吧。
除了吃,还有穿。
母亲常给我总结他们那个时代的穿着: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是老三,破破烂烂是老四。兄弟姊妹多的家庭,一件新衣服总要在大小不等的几个孩子之间全穿了一遍之后,才能退役。之后要么被改成婴儿尿布,要么被做成布鞋的鞋底,最终要做到物尽所能才算完事。我的时代,破破烂烂自然是没有了,但弟弟妹妹穿哥哥姐姐的衣服,也不是新鲜事。甚至弟弟穿姐姐的,妹妹穿哥哥的,也是有的。我是没有哥哥的,但我穿过表叔的衣服,那是母亲去城里表叔家走亲戚时带回来的。虽然有些旧,但没有破。当时看到母亲给我背回来这么多衣服时,简直有些欣喜若狂的感觉。其时并没有想过穿起来有多帅,只为衣服数量之多而兴奋。只要拥有,不在乎美丑,是那个时候全村的小朋友对着装的普遍态度。那些衣服,足足供我从四年级一直穿到初二。
要说新衣服,一般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有。也有条件好些的人家,在平常日子里会给家里人买几件新衣服,但过年的时候也是必须买的。尤其是对小孩子,过年的那件衣服显得意义非凡。如果过年都不买件新衣服,似乎这年就白过了。准备过年的新衣服,过年之前是一定不穿的,总要等到大年三十吃完年夜饭出来串门才穿上,然后故意在人多的地方挤来挤去。会哄孩子的长辈,总是在这个时候表示出震惊的脸色,“哟,某某,你这新衣服真好看,刮刮叫,刮刮叫!”得到夸奖的孩子假装不好意思地跑走了,再找个人多的地方,以同样的方式赚夸奖去了。新衣服和美食一样,总是年味的象征,无论大人小孩,总要在这两项上找出年的味道来。
那个时候的年味是具体,明确的,无非就是吃穿二字。人们对过年的期盼,就是对吃穿的期盼。过年了,就是要吃得好,穿得好。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谚语中也总是吃穿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然而,斗转星移,世事变化。时至今日,吃与穿这两个问题,在大家生活中的地位忽然有了颠覆性的变化。鱼肉荤腥这类菜,不仅在酒宴、聚会中频频登场,一日三餐中也属常见菜谱,甚至已被打入不健康食品之列。原来天天馋肉,现在却苦思如何减肥。天天过喉的红薯稀饭,还有吃得舌头发麻的咸菜,反倒成了难得之货。在粥店里喝粥,店家只在小孩巴掌大的碟子里放上颗粒可数的一点咸豇豆,再要加些便有一百个不情愿,似乎吃了他的黄金食品。
衣服也是随时可买,年关新衣服也没有什么象征意义,我下一辈的孩子里,也没有一个挤着我求夸奖。即便再穷的人家,一年买上几套新衣服也不成问题的。大家关注的不是买得起还是买不起,关注的是地摊货还是商场货,品牌货还是水货。当年对吃穿迫切期盼的心情,在如今的年里已经荡然无存了。朋友们慨叹年味不再,也是自然。
只是大家依然期盼着过年,春运现象的存在完全并且深刻地证明了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只不过大家不再期望过年时的“锦衣玉食”,而是期望一家团圆。无论身在何方,无论有钱没钱,人人心里都想着回家过年,想着回家团圆。期望虽然不同,但都是期望。
因此可以说,年味,就是一种期望,一种对生活的期望。大家都想在过年的时节里,放松自己,享受生活,与家人团聚。想团圆的人此时可以团圆,想放假的人此时可以放假,想玩的人可以玩,想乐的人可以乐。劳累的人可以在这个时候放松,挣钱的人可以在这个时候数钱,过年就是这一切的理由。和家人一起,回味四时的冷暖,收获一年的期望,这就是年味。
只要在年里实现了愿望,年就充满了味道。年味是永恒的,有所变化的只是表现的形式。朋友虽然多慨叹以往的年味不再,却不知不觉地在享受着如今的年味。尽管年味变了,也不会有人拒绝过年。只是过完了年,又要面对生活了。
生活每天都是多事之秋,我多希望天天过年,然而生活却不允许。年是如此的短暂,我眼睁睁地看着除夕,看着初三,看着初五,一个个在我面前一闪而过,却又抓不住,只有在爆竹的余音中咀嚼曾经的年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