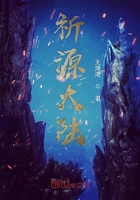莫问君端着一个小药箱到我房间,我道是事情因他而起他为表歉意亲自给我上药,虽然我从他脸上看不出一点抱歉的意思。
可以说他的动作比他人看起来要温柔细致得多,他轻轻揭开我的面具,拿一根火柴似的小棍沾着药瓶里绿色的凝露似的东西轻轻的涂在我脸上的巴掌印上,眼神特别专注认真。
我对所有带着认真态度做事的人抱有说不出的好感,我认为认真是一种特别有魅力的品质,每当这时候我都会安安静静的观察他们,说观察其实并不准确,应该说是我总会不自觉的被他们认真的神态吸引住。
“这块衣服需要剪掉,别动。”他拿出一个小剪刀说到。
“等等!我都没几件衣服,剪了就没穿的了。要不你先出去一下,我脱好了再叫你。”我按住他。
他看着我,神情有一些怪异,但是什么都没说,放下剪刀出去,关好门。
我也不管他是不是想歪了,费劲的把自己脱成蒙古人的装扮,露出左边一块光膀子,伤口牵动疼得我歪牙咧嘴,“嘶嘶”吸气。
肩头被血染红,伤口的地方快要凝血,脱衣服的时候又裂开了一些,费力吧唧脱衣服时我似乎明白莫问君刚才的表情是什么意思,这衣服染血比我想象的严重,就算洗破了也未必能洗得干净,说白了不剪掉也差不多报废了,我心里又问候了东方若华一声。
莫问君进来看见我的模样似乎不是很高兴,他拿起一块布蘸水把染血的地方擦了。
“你不具备保护自己的能力,应该回家。”他说。
“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并不想和他讨论家的话题,我的灵魂在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家,但是谁又明白呢?
“会有一些痛。”他熟练的拿起药瓶说到。
“嗯。”
“你是不是拿错了,这是药还是硫酸啊?”药粉刚沾到伤口就痛得我直叫。
莫问君一点停顿都没有,极快地上好药给我包扎起来。我咬牙抵住肩头药力产生的疼痛,一度以为我左半臂膀都会废掉,额头上涔出细细密密的冷汗,真心怀疑这家伙拿错了药。
“莫问君。”我按住他正在收拾药箱的手,问他道:“你是大夫吗?”
“不是。”
“这些药哪儿来的,你都认识吗?会不会搞错了?”
他似乎有些不悦,转头看见我痛的快要扭曲的脸却也没有发火,他淡淡的说了一句:都是我用过的。
我竟然忘记了自己疼痛为他这句话感到心酸,他们这种混迹江湖的人大伤小伤绝对不少,我这个伤完全不值一提,我现在的疼痛他们也感受过,多半还不如他们痛的厉害。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医疗事业不发达,我暗想。
“此药药力好,”他顿了一下,有点生硬的说:“很快就不痛了。”
“你这是在安慰我吗?说的硬邦邦的,看来需要多多练习啊。”看见他的样子我觉得有些好笑,我抬手像老干部一样的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肆!”他怒喝一声站起来,药箱也不收了,大步扬长而去。
真是个善变的男人,比天气还变得快。
不一会儿云儿拿了一堆衣服进来让我换上,只说是程瑜给她的。
这丫头千好万好就是晕血这一点不好,我和阿木走到她面前的时候她一句话没说完就晕过去了,只好让阿木费力抱她回来。现在看见我衣服上的血迹,她似乎又要站不住脚了。
“云儿,你挺住!就把这些当做你每个月都会来的葵水。没什么可怕的。”
我知道晕血是一种精神疾病,多半是她小时候经历过一些与血有关的恐怖场景,所以每次看到血都会联想到不好的事情产生恐惧心理,幸好这姑娘还没到大姨妈不能自理的地步,她说白婷婷和张心遥以前引导了她很久,她才能把大姨妈当作正常现象不那么晕了。
我觉得有必要让她把晕血这个毛病克服,免得以后哪天出现意外都没人帮我打理。
“小、小蒙姐……这不一样。”云儿忍着恶心帮我换衣服。
“有什么不一样,你就是想得太多。大姨妈是正常现象,那割破了皮流血也是正常的,血就是血,你别联想一些乱七八糟的恐怖镜头就好了,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都是血肉之躯,你要去接受它的存在,你要试着去爱它,因为有它我们的生命才是完整的……咦?”
我听到“咚”的一声闷响,转身一看云儿又晕了过去。
血衣都换下来了啊,难道我说的太恐怖了?不至于吧,我用马克思辩证唯物的态度开导她的啊。
幸好这丫头坚持帮我把衣服穿好,我叫了一声,阿木闻声赶来,看到地上的云儿憨厚地笑了笑说小姑娘又晕了啊?
我无奈的点点头,麻烦阿木把她抱到床上,我问阿木知道什么治晕血的办法不,阿木摇头说不知道,程瑜是大夫这要问他。
程瑜是大夫?程瑜是大夫!
那为什么不是程瑜来给我换药,莫问君搞什么鬼?我又开始怀疑他把药拿错了。不过现在药劲过去只有伤口的隐痛,想到之前莫问君的表现,我又觉得怀疑他显得不近人情,人家好心帮忙上药我还不信任,也难怪他会生气。
程瑜也跟着进来,他笑嘻嘻的收拾桌上的药箱,我问他知道什么治疗晕血的办法,他说云儿是肝气郁结、气血不足、心理恐惧,他可以开几服药调理,让她身体好一点辅之引导,适当的让她接触一下血,假以时日就能痊愈。
我估摸着程瑜说的应该是膳食药理加系统脱敏疗法,觉得可行,就拜托他帮忙治一下。
程瑜笑得有些尴尬,他似乎还有什么想说。
“怎么了?”我问他。
“有些难以启齿,也并非我的本意,这一路吃喝用度的费用公子说是时候结清了。”他拿出扇子扇了两扇。
我心想他们这样完全没错,不过说得这么急多半是之前把莫问君得罪了,但是这一下我也拿不出钱财来,肩膀受了伤不能出去找工作做,焦头烂额。
“多少?”我问。
“吃喝不贵,那张面具花了我半年时间做成,就算回收也需要多种药物修复,加上到观水城后你借的那些,看在这几日的交情,就收个六百两吧。”
“六百两!你怎么不去抢!”
程瑜呵呵笑也不答话,阿木在旁边默不吭声,神情却是我赚大了的样子。
“那、缓我几天行吗?”我软下声音来。
“其实要银子并不难,过两日张成义会来观水城,你只需和他打个招呼即可。”
张成义?
我的天!那不是张心遥同父异母的弟弟吗?我给他打招呼不就是自投罗网吗?现今到处都在悬赏我,多半是张家搞得,我怎么能往枪口上撞呢?
“银子你们缓几天,我会想办法,到时候连本带利还你们。那个张成义,你们别找他,我不想被抓回去。”
“何苦呢?明明一个千金大小姐。”
“你们不会明白的。这样,我自己给莫问公子说,也不好让你为难。”
程瑜答应着提走了药箱,同时他带走的还有那张面皮,这就意味着我不能再抛头露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