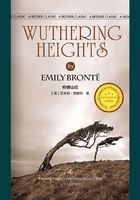她走进了楼道,自行车横七竖八地挡在信箱前边,她一架一架拉了开来,终于开辟出一条曲折的小路,她挤身进去,终于走到了信箱跟前,她举起钥匙去开锁,钥匙激动地摸索着锁眼,她止不住地有点气急,好像行将去赴一个约会,一个她等待已久的约会。信箱开了,只有一份忠实的晚报。她几乎浑身瘫软下来,身后的道路忽然闭合了,又让自行车封锁了起来,她再也无法退出去了。她将晚报夹在胳膊底下,关上信箱,重新上锁。然后艰难地转过身子,撤了出来。自行车被她拉得乱七八糟,挡住了楼梯入口,她再记不起原先它们是如何排列的了。她尽着她最后的力气,推着自行车,留出一个狭窄的入口,便再也管不得许多,拖了沉重的步子迈上楼去。她不得不用手去扶那生了铁锈的扶手,扶手粗糙地锉着手心,她感觉到锈烂的铁屑被她抚落了。她上了一层,走进了黑魆魆的楼道,什么都看不见了,没有一点光明的照耀。她慢慢地挪着步子,凭着感觉与习惯,摸到了自家门口。
家里是黑沉沉的一团,她拉亮了电灯,房里的家具倚墙立着,流露出一种寂寂的情绪。她不知不觉湿润了眼眶,她再没有一点儿体力与精力,她只能躺倒在床上,她只有睡觉这一条路了。可是,多年来的生活早已形成了一种惯性,这惯性不露行迹地推动着她,她连坐都没有坐,放下挎包和晚报,就系上了围裙。这一套操作早已形成了机械的程序,不用动一点儿头脑,不用下一点儿决心。从她开信箱到进门,她几乎是没有浪费一分钟的时间,她几乎没有休止一个动作,她连贯地、不间歇地走了上来,而在她漠漠的心里,是早已倒下了数次,又挣扎了数次,是早已经过了长长的跌倒爬起的历程。她是很累很累了。她心里是又荒凉又骚乱,又虚空又紧张,这乱七八糟的心情最后便归宿于一团怨气。
她再不必矜持了,她再不必保护自己形象了,她已经失了好性子,她是失了一切指望的。于是,她开始等丈夫回家。再过五分钟,如丈夫还不进门,便算是迟到了,便有了她抱怨与发怒的理由。她盼着丈夫给她一个发怒的理由,可是丈夫的钥匙总是准时摸索着锁眼,他是不让她挑出一点碴儿的,总是在水沸腾了饭,水又干了,闷上锅盖的那一秒钟推开了门,她是抓不住他一点儿把柄的。可是她多么难熬啊!他一到了面前,她便再不需要理由,她的坏性子,她的无由的怒火,全失了约束,全被怂恿起来,她简直是怒气冲天,她对着他,劈头盖脸地发作了。这一顿饭是在她的絮叨中烧熟,吃完,直到收拾完毕。她絮叨得累了,再说不出新的埋怨,便愤愤地住了口,紧接着,心里便涌起了一阵委屈与辛酸。她开始怜悯自己,她懊恼自己又失控了,她是再没指望重新做人了,她便流泪了。丈夫对她的眼泪和对她的絮烦一样地习惯了,早已不以为怪,便只默默地对着她看,问她是累了,还是怎么了。她则又开始絮叨,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他。他想上前安慰她,却被她怒冲冲地一把搡开,他只得走到一边去看晚报了,顺手拧开了电视。电视里正播放着新闻。她大嚷着要他将声音拧低一点儿,说头脑都要炸开,话没落音,丈夫已将声音拧得没有了,只有人形鬼影般地活动。她又觉着了无聊。她对这一切厌烦得透不过气来,熟惯到了极点的生活,犹如一片种老了的熟地,新鲜的养料与水分已被汲尽,再也生长不出茁壮的青苗,然后便撂荒了。撂荒了的土地,天长日久,又再产生着养分,可是再不会吸引人注意了。她又不是勇敢的拓荒者,她生性厌恶荒地,而喜爱青草葱茏的花园,她是再不会去留心一块荒地,再不会去开拓一块荒地。她将她的土地种熟了,以她充沛的精力和好奇心加紧地种熟了一块土地,加速汲尽了一份养料,她的土地不是一年四季地轮回,而是一年八季地轮回,然后便失望下来,将土地撂荒在那里了。她现在,守着这一块荒地,为着荒凉哭着,恼着,怨着。
银幕上的形象在无声地行动,她的啜泣充满了小小的房间。她满可以走出房间,换一下空气,调节一下心情,可她不愿,她非得坐在这里,找碴儿似的守着她的丈夫,非要将她的心情和他的心情,弄得糟透糟透,否则,这一个晚上她便过不去了。
这一个夜晚是糟透糟透了,然后她才觉着舒服了一些,静静地缩在床角里,等着丈夫来抚慰。丈夫是准时无误地来到她身边,抚慰她也抚慰自己,如不是这抚慰,他们的整个生活都将不堪忍受,或许双方都会考虑出一个绝断的方法。可他们总是悬崖勒马,他们总不致真正的决裂。在这一瞬间,他们暂时忘却了方才的败兴和即将到来的明日的败性。他们学会了忘记,学会了苟且偷生,学会了得过且过。他们便这样维系着,维系着度过了无数个昼昼夜夜。
她的希望与早晨的太阳一起升起,早晨新鲜的阳光带来了他的照应。他是与她一同醒来的,她觉得,这一日,是不会再让她落空了的,她伸着懒腰,懒懒地想到。每一日的早晨,她都有无穷的希望,希望与体力精神一起培养,一起恢复到她的肌体里。早晨的一切于她都是吉兆,假如晴天,她便想,是很好的一天啊,假如阴天,她则想,是很不一样的一天啊!她都是兴致勃勃地赴约似的出门和回家。可是,她的希望却总是落空,她没有一天实现这希望的。他是在渐渐地、不可阻挡地远去,他形象变得模糊,行踪飘移,她再也感觉不到他目光的跟踪与照耀,她努力回想着与他的一切,一个细节都不曾遗漏,可是每一个细节都像是由她编造出来似的。似乎太过虚渺,没有一点儿实据;却又太过具体,与整个虚渺的他不相符合。连她自己都不相信会有那样的事发生,连她自己都怀疑了。她甚至希望能有流言飞语,她甚至后悔当时掩饰得过紧过严,如若泄露了一星半点,这一切便有了旁证,她真想有一个旁证,可是没有。他好像整个儿地消失了,没有了,不复存在了,他在哪里呀!他,在哪里呀!她焦灼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她怎么找不着他了,没了他,她便失了管束与督促,她简直有点自暴自弃了。
可是,日常生活已经形成了一套机械的系统,她犹如进入了轨道的一个小小的行星,只有随着轨道运行了,她是想停也停不了,想坠落也坠落不了,她只有这么身不由己地向前进了。早晨,她起床,先在床沿上坐着,睡思昏昏,口里发涩,呵欠涌上来,泪水糊住了眼睛,她一腿蜷在床边,一腿垂下脚尖点着了地,眼角觑着丈夫,丈夫在床上躺成一个“大”字,身上盖了一床薄被,阳光很难穿透平绒的窗帘,屋里很暗,钟的指针在嚓嚓地走。然后,丈夫陡地一动,好像有人捅了他一下,他四肢缩紧,拥被而起,坐在床上,先是垂着眼皮。然后慢慢地抬起,茫然地四顾,渐渐与她的眼睛相对。他们的眼睛茫茫地走过半个幽暗的房间,茫茫地相对着,什么也没看见地看着,犹如路两边的两座对峙了百年的老屋。他们过于性急的探究,早已将对方拆得瓦无全瓦,砖无整砖,他们互相拆除得太过彻底又太过迅速,早已成了两处废墟断垣,而他们既没有重建的勇敢与精神,也没有弃下它走出去的决断,便只有空漠漠地相对着,或者就是更甚的相互糟践。
然后,他伸出手茫茫地摸去,正摸到一个耳扒,便将耳扒伸进耳朵,眼睛眯了起来,脸上渐渐有了表情。她心里旷远得很,眼光早已从他身体里穿透过去,他也穿透了她,他们互相穿透了。他们互相穿透地留在自己的位置上,做着自己的事情。她渐渐地平静下来,她早已是灭了希望,心里只有一片咝咝的雾气,雾障遮断了一切。她似乎是在这一个早晨里想通了一切,这种漠漠的相对是她婚姻的宿命,是她的宿命。因此,她宁可将他埋葬在雾障后面,她宁可将他的她随他一同埋葬在雾障后面。她绝不愿将他带入这漠漠的荒原上,与他一起消磨成残砖碎瓦,与他一同夷为平地。他们将互相怀着一个灿灿烂烂的印象,埋葬在雾障后面,埋葬在山的褶皱里,埋葬在锦绣谷的深谷里,让白云将它们美丽地覆盖。从哪里来的,还回到哪里去吧!她在同所有的普普通通的早晨一样的一个早晨里,想通了这桩事情。想通之后,她冷静了下来,方才发现自己也并没有给他去信,他同样也留给了她一个地址,她也是可以给他去信的,他们本应该同时去信的,那才是真正的两心相通啊!
她忽然想到,其实,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是,有一串闲话,如同谶语一般跳到她脑子里,放大在她眼前,那便是——
算了。
你要走了。
我不和你吵了。
屋里挺闷的。
还不如出去走走——
——再说吧。
走吧,
时间到了,
要回去了!
她将它们横过来,连成一条,发现,这便是全过程了,这便是全过程了。
她觉得,其实,确实,千真万确,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不过,窗外梧桐的叶子落尽了。
一个什么故事也没发生的故事,讲完了。
我的故事讲完了,我却不甘心,还想跟随着她,也许,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她穿了一身浅灰色的秋装,未出阁的女儿家似的,翩翩地下了肮脏的楼梯,阳光透明似的,她在透明似的阳光里穿行,她仰起脸,让风把头发吹向后边,心情开朗起来。在锁上的两道门:一道房门,一道阳台门的后面,阳台上停了两只麻雀,并脚跳着,跳着,嘟一声,从栏杆中间飞了出去。
她看见了路上的枯叶,在行道树间沙沙地溜着。阳光重新将它们照成金黄色的,它们炫耀地翻卷着,亮闪闪了一路。树叶几乎落尽,树枝萧条了。这是最后的秋叶了。
我看着她调皮地用脚尖追索那些金黄的卷片,然后恶作剧地“咕滋滋”一脚踩下,我想起她从小就有一个癖性,那便是一件心爱的东西,如果坏了一点儿,她便将它完全地摧毁了,越是心爱的东西,她越是这样。除此以外,我再也想不起别的,我只得放开了她,随她一个人没有故事地远去了。
1986年9月12日一稿
1986年9月27日二稿 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