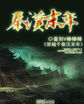“这件事要是捅开了,学校肯定处分欧文珮。”我说。
“所以啊,我们得慎重。”梅丹冰说出了她一直的顾虑。
“但这事儿让人别扭。”白灵灵很生气,“都在一个宿舍,你明知道她偷了你的东西,还得装不知道,人家不该骂我傻×啊。”
“这样吧,”梅丹冰说,“白灵灵,以后你管好卖东西的钱物,不要放在明处。还有你,闹闹,也总爱把钱四处乱丢,以后也不要这样。咱们先不在客观上促使欧文珮继续犯错误,再观察一段时间,好吗?”
白灵灵做了一个“操”的口形,点头同意。梅丹冰又叮嘱我们保密,包括贺兰也不要讲,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三人便回到宿舍。
但我还是把这件事跟穆晨锺说了。小时候,我们大院里的孩子把爱传话的人叫做“电报嘴”。我不做“电报嘴”已经很久了,但见了穆晨锺,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对穆晨锺说:“谁能想到,梅丹冰要我们先从自己做起,不给别人犯错误的机会?”
“你这位同学确实不错,心地善良,又有思想。不过,我倒有另一个问题:那位偷窃的同学,她的动机是什么?”
“梅丹冰从侧面问过欧文珮,是否家里遇到困难,可欧文珮说没有。”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平时表现好吗?”
“欧文珮家里虽然穷,但她一点儿都不自私、也不贪婪,还热心助人。”
“如果是这样就有问题了。你想想,一个平素端正自律的人忽然行窃,她背后一定另有隐情。”穆晨锺思考了一下,说,“舒展,你能介绍我认识你那位丢钱的同学吗?”
“干吗?”我奇怪。
“我想见一见她。”穆晨锺说。
“您终于想见她啦?”我笑道。
“怎么?”穆晨锺问。
“她曾经要我介绍她认识您,被您拒绝了。”
“哦?你是说……”
“对啊,白灵灵就是贾鸿图的研究生。”
穆晨锺说服了白灵灵收下了他的100元钱。穆晨锺要白灵灵仍像以往一样,将它们断断续续放在欧文珮触手可及的地方。白灵灵除了取笑穆晨锺有一些迂,倒也乐于从命。梅丹冰却表示反对,她认为凡事要坚持是非和原则,如果明知偷盗是不对的,就不应该鼓励。穆晨鍾否认他在鼓励偷盗,他甚至不承认他拿出的是金钱,他说它们是上帝呼唤迷途羔羊的“青草”。
只是,这只羔羊似乎没有回头的意思,白灵灵床铺上的钱仍然不紧不慢地丢失着。中间,穆晨鍾又补充过一回。梅丹冰几次想开诚布公找欧文珮谈谈,但因错过了第一时间,谈话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白灵灵不躲避欧文珮。白灵灵觉得她在“施舍”一个窃贼,因而经常指使欧文珮干这干那,对她的态度非常恶劣。只有贺兰,因为毫不知情,对欧文珮一如既往,甚而更加体贴。
欧文珮的一次意外晕倒,提前结束了这一切。
校医院急诊科医生只稍微一看就诊断欧文珮严重贫血。随后出来的化验报告显示,欧文珮的血色素竟然低到难以想象的5克!在医生严厉的盘问下,欧文珮承认了频繁卖血的事实。医生气愤地说:“你身为医学研究生,难道不知道这样会毁了你自己的身体吗?而且,这对那些受血者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化验报告还显示:欧文珮患上了严重的肝炎。
欧文珮一句话也不说,就哭了。
出院后,欧文珮向学校递交了退学申请。她在报告中交代了理由:半年前,欧文珮的母亲进山偷砍林木,失足跌进山谷摔成高位截瘫。欧文珮的家庭完全失去了劳动力和经济来源,无以为计的欧文珮只有去卖血。欧文珮每周末都乘长途车到郊县卖给非法的小采血站,因为他们不会体检和要求献血间隔时间。日久天长,欧文珮的健康透支,身体终于垮掉。
欧文珮的遭遇在博雅掀起波澜。学校考虑减免欧文珮的学费,梅丹冰又发动全系同学为欧文珮捐款。这个倡议得到校学生会的支持,捐得的款项不但够欧文珮完成学业,还有相当富余接济她的家庭。欧文珮却坚持退学。她说对于她,到北京上大学已经是一个梦,念博雅英语系就不应该了。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分等级的,这个道理以前她不认,现在认了。这就是命运。命运把她降生在彩云之南的那个闭塞山沟,她就要服从。
6月是一个毕业的季节,一个分离的季节,一个凭空伤感的季节。
毕业生离校的前一天晚上,北京高校校园民谣乐队到博雅巡演。舞台搭在学校门口内的中央草坪上,白天,这里刚刚举行了毕业典礼。我和梅丹冰白灵灵贺兰簇拥着欧文珮,站在舞台下面。张静去美国后,315宿舍的同学还是头一次聚在一起。一个高个子长头发,脖子上扎一条小丝巾的漂亮男生走上舞台,演唱了《同桌的你》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接着,一个梳披肩发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学生自弹自唱了罗大佑的《闪亮的日子》。女学生身后,细小的飞虫在射灯的照耀下,幻化成无数个亡命的精灵,于夜空中绝望地起舞。
欧文珮在人群里显得十分渺小。我站在欧文珮右侧稍后一点的地方,看她不时低头揉擦眼睛。我也低下头,乘人不备飞快抹去流到脸上的泪水。以往,在315宿舍除了我和梅丹冰,就数跟欧文珮关系最好。欧文珮性格开朗、随和,北京话讲叫“吃玩”,我常拿她开心。不久,发生了“失窃事件”。我像因为窥视了别人的隐私而感到不自在,怀疑使信任也没有了。欧文珮也变得格外沉默寡言忧心忡忡,她总是来去匆匆,越发像一条影子,毫无防备地投下没有温度和质感的存在。
现在回想,我们是多么的粗心啊。
曲终人散。露水已经开始下来。大学生们还像一群游魂,流浪在夜风渐凉的校园里。白灵灵说:“反正睡不着,不如去酒吧坐坐。”
学校对面是一条酒吧街,每一间里都挤满了分离在即的学生。白灵灵熟悉情况,拣了“樱花时节”进去,在一个角落里坐下。白灵灵做主点了饮料和零食。大家默默啜饮着,彼此都不说话,连碰杯都不。梅丹冰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欧文珮。欧文珮疑惑地看了看梅丹冰,拾起信封,打开往里望了一眼,立即推了回来,说不能要。
“这是宿舍同学的一点心意,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些了。”
“不,你们的心意我领了,钱我坚决不要。”
“我们都是真心诚意想帮助你啊!”我说。
“你们已经帮我许多了。”欧文珮说,“以往,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你们把自己的菜拨给我,说你们不爱吃。你们把崭新的衣服送给我,说你们不想穿了。这些,我嘴上不谢,心里都是明白的。说实话,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助,这个大学我早读不下去了,但我不能接受你们的钱。那样的话,我就真的太‘贫穷’了。”
梅丹冰和欧文珮推来推去。这情形让白灵灵不耐烦,她突然高声道:“得啦,欧文珮,你就收下吧。以往你不都‘接受’了嘛。”
欧文珮愣住了,说:“以往我接受什么了?”
白灵灵自知说走了嘴,索性摊牌,说:“实话告诉你吧,你偷拿我的钱,我们早就知道。那些钱不是我的,是闹闹的导师穆晨锺的。”
欧文珮大瞪着迷茫的眼睛,说:“我什么时候拿过你的钱?我从没有拿过别人一分钱!”
几个人都蒙了。我们茫然地面面相觑,然后又将目光投回到欧文珮脸上。欧文珮因为气愤而苍白的脸孔让我们相信了她。——可是,那些失窃的钱是怎么回事呢?它们去了哪里?
那个由来已久的窃贼,又是谁呢?
突然,坐在阴影里一直沉默的贺兰跳起来,蝙蝠一样冲了出去。
并蒂之爱
直到第二天离开学校,欧文珮再也没有触及“失窃事件”。前一晚,欧文珮和衣在光板床上躺了一夜。她的行李下午已经交办托运,原本说晚上借同学的卧具凑合一下。但欧文珮拒绝了。梅丹冰和我都拿出自己的干净床单和毛巾被,欧文珮笑着摇头,说谢谢。她那笑里,透着分明的寒心。
第二天,欧文珮背着她死去父亲的旧军挎,一个人去了火车站。欧文珮走时没有哭。她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也没有回头。我和梅丹冰白灵灵一齐站在欧文珮身后,我们全都没有哭。
我们没有资格哭。因为我们全都伤害了欧文珮。这个从云南边境大山里走出来的女孩,在由她的同学们的爱心、仁慈、道德和财富组成陪审团的法庭上接受了错误的缺席审判。我们的善良使我们长时间将她视为“罪犯”,却长时间地宽容着她,这比将她误判有罪并予以惩罚更令她感到伤害。梅丹冰后悔没有在一开始就杜绝事件的继续。我的沮丧更无以复加,如果不是我将事情告诉给穆晨锺,后来的发展无论如何不会这样。白灵灵的悔恨是用摔摔打打来表达的。与其说白灵灵懊恼自己对欧文珮的骄横和蛮不讲理,不如说她更埋怨欧文珮当时的那种逆来顺受。
心情最复杂的是贺兰。欧文珮的猝然离去让贺兰成了一个谜,没有人知道这个漂亮文静的姑娘为什么要做一个长期的贼。贺兰只如数退还了300多元“赃款”,却什么也不肯交代。——人们发现,贺兰偷去了这些钱,一分也没有花。白灵灵当初做了记号的那几张钱,还依然健在。
如果不是为了挥霍,贺兰为什么偷钱呢?
贺兰的冷漠被视为顽固,她一向的美丽也变得面目可疑。同学们都不理贺兰,贺兰则用沉默为自己垒起一座高墙,她整天躲在蚊帐里,给她那个叫姜健雄的人写信。
这个世界上,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阻止贺兰做这件事。
“我恐怕害了那个叫做贺兰的孩子。我一定是害了她。”当所有的人都认为欧文珮是“失窃事件”的最大受害者,穆晨锺却偏偏对贺兰牵挂不已。穆晨锺从未有过如此颓唐,他忽然间苍老了,头发比以前更加花白,背也更加驼起,整个人像遭受意外霜冻袭击的茄科植物,拼命地萎缩下去。
一天深夜,我正在暗房洗印实验标本显微照片,穆晨锺突然来找我。
“舒展,你有空吗?”穆晨锺敲击暗房的门,我告诉穆晨锺我刚刚开始。
“有件事,我想跟你谈一谈。”穆晨锺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医学实验中,同一批结果的照片最好使用相同的洗印条件一次完成,所以洗照片的活儿中途不好停下,我猜不出穆晨锺有什么事非要在这个时候告诉我。
“主任,要不,您进来好吗?”穆晨锺小心掀开厚重的门帘,踅身进到暗房。穆晨锺环顾四周,有一些局促。我搬来一只转椅给穆晨锺,自己坐在对面,说:
“主任,您想说什么?”
“是关于我女儿,”穆晨锺说,“我的‘另一个’女儿。”
我没想到穆晨锺要谈的是这件事。刚上研究生不久,罗艺兵就告诉我穆晨锺有一个女儿,两年前投湖死了。这件事成了穆晨锺的心中之痛,罗艺兵提醒我千万不要在穆晨锺面前碰触这个话题。
而穆晨锺此刻的语气,似乎要揭开这个秘密。
青莲是穆晨锺的另一个女儿,大青荷5岁,是她的姐姐。
跟青荷的性格相反,青莲从小文静内向、善解人意。穆晨锺留学英国那年,青荷刚出生不久,青莲承当起姐姐的责任,替母亲分担家务。11年后,穆晨锺回国,青莲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美丽、娟秀,含情脉脉。不久,穆晨锺发现青莲的生活里一些难以解决的麻烦。青莲从小患有严重的牛皮癣,这使她放学后常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从不结交朋友。一次,青莲对穆晨锺说:“爸爸,您是医学专家,您研究我的病,帮我治好它,好吗?”
穆晨锺深感对不起女儿。这些年,世界上许多可怕的顽症都一一被攻克,连癌症也不再被视为“不治之症”,但人们对一些看似简单的疾病却仍束手无策。
后来的一天,刘苏娜突然痛打了青莲。刘苏娜对穆晨锺说,她提前下班回来,撞见青莲在房间里吻青荷。刘苏娜确信,那绝不是普通的姐妹之吻,而是羞耻的肮脏的举动。穆晨锺把女儿带到办公室。穆晨锺让青莲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他在她面前跪下,抚摸着女儿说:“青莲,爸爸对不起你。爸爸不应该出国,应该留在家里,陪着你的。”
一直承受着刘苏娜的暴打而没有吭声的青莲突然哭了。青莲说,班上一个男孩子诅咒她,说永远没有人会爱她,因为她有牛皮癣,会传染。青莲委屈地说她只是想在妹妹身上试一试,看看能不能传染。
穆晨锺放心了,他对女儿说:“等你长大了,一定会有男孩子来爱你的。因为你是一个好姑娘。”
穆青莲点了点头。她看着父亲。露出诚恳的羞涩。
然而,穆晨锺并不知道,貌似纯洁的女儿欺骗了自己。
青莲真的喜欢她的妹妹,她很“爱”她。一天,穆晨锺意外透过浴室门缝,窥见到一幅画面:喷水的莲蓬下,他沐浴的女儿们像一对天使,正赤裸地拥抱在一起。青莲无比陶醉地亲吻着妹妹的头发,一只手抚摸着妹妹刚刚发育起来的小粽子一样幼稚的乳房。另一只手,滑向了青荷的下体。
穆晨锺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感觉到他的心脏在致命地绞痛。西方统计研究表明,在普通人群中,完全的异性恋和完全的同性恋只各占人口比例的3%,中间94%的人则具有双性恋倾向。穆晨锺相信,自己的女儿只是性趣味的暂时异常,绝不会是那令人绝望的3%!穆晨锺对青莲付出了全部的耐心和努力。他给青莲详细讲解人体的构造和性的细节。为了培养青莲对异性的兴趣,穆晨锺甚至给青莲拿来一些他从国外带回的堪称色情的画册读本。
可是,这样过了一年,穆沉重发现他失败了:他的女儿是一个100%的HOMO。穆晨锺难过极了,他想这是上帝对自己的惩罚,一定是他哪里做错了。穆晨锺一如既往地爱着青莲,希望能帮助她。可是,刘苏娜却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件事,她对青莲殴打、谩骂、隔离,疯狂和歇斯底里。
结果,青莲在她18岁那一年,把自己投进了翠湖。
“青莲和你同岁,她要是活着也该你这么大了。”穆晨锺忧伤地说,“看到你,我常常想起青莲。那次你昏倒在雨里,醒来后哭诉你的一只大白鼠死了,我几乎就把你当成了青莲。青莲也像你这么善良,她的心里全是爱。”
我默默地听着,不知该说什么。
“青莲的死是我的责任。”穆晨锺疲倦地说,“我不应该出国,并且那么长时间没有回来,使女儿在成长的最关键时期缺少父爱,缺少来自男性的赞美和鼓励。——噢,还有那致命的牛皮癣。即使只是一个诱因,也与我有关。我一直有神经性皮炎,情绪紧张的时候会掉头发和有头皮屑。最主要的是,我不了解青莲。我以为我了解她,我按照我的想法帮助她、导引她,其实我根本不了解她。”
“主任,您担心的是贺兰?”我忽然明白了穆晨锺为什么告诉我青莲的秘密。
“是的。”穆晨锺喟叹道,“我发现,我一点儿都不了解这个孩子。就像一种奇怪的病症,我在不了解的情况下给病人开了药,这些药可能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也许没那么严重。”我安慰说,“我觉得贺兰的情况并不是心理上的问题,也许就是简单的见财起意也说不定,您用不着太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