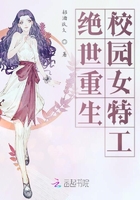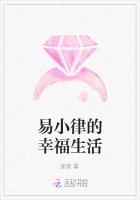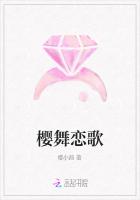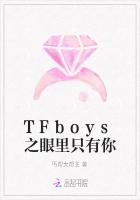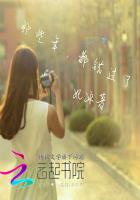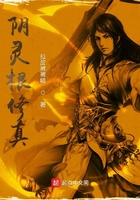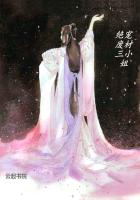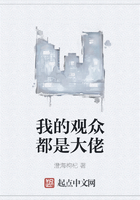第三十章英年早逝
(一)
时光荏苒,光阴如梭,转眼间,时令已是1935年农历二月。
阳春三月,唐河两岸,阳坡的茵陈、蛤蟆草已经渐露头角,一层毛茸茸的、尖尖的、嫩嫩的草芽从土地里争先恐后地往外窜,像是调皮的孩子在和大自然捉着秘藏,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到处是疯长着的一块连着一块绿油油的麦田和一片片金灿灿、黄艳艳的油菜花。
听老年人说,蛤蟆草泡茶喝可以医治哮喘病,茵陈也有止咳的疗效。但是,茵陈是一种有时令性的中草药,都知道有“三月茵陈治黄痨,四月青蒿当柴烧”之说。
司氏一大早就起来,给五岁的李兴民胡乱弄碗饭吃,嘴一抹,母子两就手拉着手,拎个小竹篮,篮子里放把小铁铲子,出了半坡村,一路有问有答地来到了唐河东南岸。
此刻的唐河水,泛着一层暖的色彩,映着两岸的点点新绿,让人恨不得伸手捞一把才称心。根本不象冬天的河水,远远看到,就要瑟缩了手,从心里溢出寒来。
河面上,还飘着冬天落下的树叶。那些叶子不再是畏缩着的愁苦样子,而是舒展开来,象杯中泡开的茶叶,一副重生的欢天喜地。原来,生命的枯死只是一种形式,它内在隐藏着的生命,一直都在。
“妈妈,你说俺爹喝了这蛤蟆草、茵陈泡的茶,是不是病就好了,也就不会整晚上再咳嗽了呢?”
“是的,自从你爹在淮阳师院染上哮喘病,医生和你奶奶他们这些年都是用蛤蟆草、茵陈等中草药给你爹熬茶喝,炕擀饼吃的。”
“妈,要是这蛤蟆草、茵陈真能治好我爹的哮喘病,那,咱们就天天来,把唐河沿岸的这些中草药全挖出来给我爹治病,你说好不好?”
“好,咱两天天来唐河岸边给你爹挖这些中草药。”
望着一脸天真,纯洁无邪的儿子李兴民,听着他那一连串发自肺腑的幼稚心声,一脸胎气的司氏忍不住心酸难过起来。一想起丈夫的哮喘病,她的心口就像猫抓一样乱糟糟的,心里那个痛楚劲,只想躲到一个无人能看得见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结婚以来,这么多年,哮喘病如影随形,象藤蔓一样一圈一圈把丈夫的身体缠紧。他们一家人曾访遍方圆百十里地的老中医,药引子无非都是罗汉果,鱼腥草,白茅根,紫苏梗,桑白皮,百合,野菊花,板蓝根,甘草等中草药熬制的苦药汤子,中药也喝过不止成千上万付,可是咳嗽根本也医治不除根,病情也没见减轻多少。尤其是季节交替的时日里,他咳嗽的特别厉害,几乎到了窒息的地步。
过年的时候,在源潭镇开卷烟厂的六叔——李华亭回半坡来祭祖,当他无意间看见自己当校长的侄子李泽南因哮喘而浑身冒虚汗,痛苦不堪的样子时,二话没说,立即回卷烟厂库房,毫不吝啬地把私藏多年的大烟取了回来,塞给到处跑着收税的二爷抽,让二爷用嘴里喷云吐雾的大烟圈麻醉被病痛折磨得痛不欲生的侄子,减轻他的病痛。
一大家子人都围在李泽南的身边唏嘘叹息,眼泪丝丝。作为朝夕相处,风雨同舟的妻子,司氏心里的疼痛更是难以描述。她一边伏在儿子李兴民的小肩膀上偷偷流眼泪,一边抚摸着肚子里已经孕育了快三个月的新生命暗自祈祷:老天爷啊!求求你了,别再折磨我们家这个与世无争的白面书生了,祈求你开恩减轻他的病痛吧,因为他身上的担子太重了,他不仅要抚养大儿子李兴民长大成人,而且还有一个孩子尚未出世,这个家离不了他呀!况且,源潭县立小学那二百多号学生娃娃也需要他啊!
可是,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她除了千方百计给丈夫寻医问诊外,就是尽自己所能每年这个时候到野地里挖这些中草药,用偏方给丈夫治病。除此之外,她不知道她该如何做才能尽可能的帮助丈夫,哪怕只能减轻他一星半点的病痛。
日子就在这样的循环往复里一天一天地走过。李泽南本来就单薄的身子越发的消瘦了,苍白的脸上尽是病容。但是,他依旧带病坚持到校工作,一天时间也没舍得歇过。
(二)
春去秋来,转眼又到来1935年冬天。
这天,一夜大风。清晨起来,踩着此伏彼起的鸡叫声,走在去源潭县立小学的乡间小路上,气温很低,伴随大风降临的寒流使地面上一切看见或看不见的东西上都蒙上了一层白霜,四野白茫茫一片雾气很重。树上的枯叶在寒风中瑟抖,飘落。一群乌鸦在唐河两岸的老树林里“呱、呱、呱”地仰着头乱叫,也许是听到由远而近的脚步声和剧烈的咳嗽声吧,它们拉下一层白色的粪便后,盘旋着朝另一片树林的方向飞去。
李泽南一路蹒跚,走着喘息着,他浑身疲乏无力,费尽全身力气,花费了比以往多一倍的时间和体力,晨曦微露的时候,才披着一身浓霜和从四面八方一起涌向学校的学生一起进了校园。
今天是新周一,又有新的教学任务要布置,上课铃声响过后,学生们都坐进了教室,老师也布置了自习的课程,这时,他又一次召集全体教师到教研室开会。
老师们都坐齐了,会议还没切入正题,李泽南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他连忙掏出手帕,还没来得及捂住嘴,忽然,一口鲜血喷涌而出,洒到教研室的桌子上。老师们一阵惊呼,李泽南感到天旋地转,胸口一阵窒息,苍白的脸瞬间憋的青紫,呜呜啦啦想说话,但是,嘴巴张了几张,嗓音暗哑,已经说不出话来,随即就瞪着一双几乎爆裂的眼睛,很快歪倒在教研室的地面上去了。
“李校长,李校长,你怎么啦?李校长,你快醒醒,你快醒醒啊!”教研室瞬间乱成了一窝麻,掐鼻子的,捏人中的,哭声,喊声响成一片。
有人慌乱中不失理智,见眼睛的瞳孔已经扩散,赶忙将校长舍不得闭合上的眼给慢慢闭上,他悲哀地摇摇头说:
“已经不行了,瞳孔已经扩散了。人活一辈子,是不能死在外面的,趁身体还有余热,咱们赶快弄副担架来,立刻把李校长送回半坡去。快,孙老师,你腿脚快,先去半坡送信,刘老师,你去源潭镇通知李校长的哥哥李步云。谁去泰和寨,通知李子炎?咱们赶紧分头行动。”
听到哭喊声,学生们都从教室里走出来,见教师们都跟着躺在担架上的校长的遗体痛哭流涕,一时间,校园里哭声一片,学生们以班为单位,自发地组织起来,排成一条长龙似的送行队伍,一路蜿蜒着跟随抬担架的老师出了源潭镇县立小学的校门,他们要去半坡送英年早逝的李校长最后一程。
这样的声势浩大的送行阵容,招引了一群又一群围观的老百姓,他们忍不住驻足观看,议论纷纷起来。
“这是咋啦?谁死了呀?怎么源潭县立小学的全体老师和学生都去送行?”
“听说是他们的校长,今年才29岁。”
“哎,太可惜啦,这么年轻,又是个难得的人才。好好的,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听说是痨病,人都瘦成一根麻杆棍了,死的时候还在教研室里开会呢。”
“这年月,还有这样敬业的人啊!哎,老天爷,这样的人才对祖孙后代都有好处,怎么不找那些年老的人去替他死呢?这么年经轻轻的,是个死不下的人啊!”
闻听李泽南断气的噩耗,半坡村的整座四合院里早已是哭声震天。老祖母哭哑了嗓子:“我的宝贝孙子,祥云啊,你咋说走就走了呢?让我们这些白发人送你个黑发人,你于心何忍啊!你撇下他们孤儿寡母,这一家子人的天可是塌陷了呀、、、”
司氏早已哭得休克过去,五岁的李兴民吓得浑身发抖,见一家人哭的昏天地暗,四合院里乱糟糟的一片狼藉,有人在搭灵棚,有人张罗着撕白布做寿衣,几个木匠正在锯木头,说是给老八做棺木。老八不是自己的父亲李泽南吗?难道是父亲出事了。五岁的李兴民,模模糊糊,思维一片空白,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哪里知道失去父亲意味着什么,他还不能真切地体会这种家里忽然塌了半拉子天的局势!
管事的二爷带几个族人飞快去唐河接李泽南的担架去了。站在唐河东南岸,望着长龙似的送行队伍,二爷忍不住眼泪纵横不止,心里默念着说:“泽南啊!你还年青,走的太早了啊!司氏肚子里还怀着小宝宝,你怎么忍心撇下他们孤儿寡母自己就先走了啊!不过,你看,有这么二百多号师生来给你送行,二哥我感觉你活的值了!你会活在这些娃娃们的心里的,这也是我们一家人的荣耀啊!不过,泽南呀,你看,这么多人去半坡,过河要淌水,淹着孩子们可不得了,另外,招待他们,光地锅烧水这一项就够我们喝一壶了,还是让他们送到这里为止吧。”
这样一阵子思索过后,二爷站在唐河东南岸,含着热泪对矗立在唐河岸边的源潭镇县立小学的二百多号师生发表简短的致谢演说:
尊敬的源潭镇县立小学的全体师生们,你们辛苦了!
感谢你们冒着严寒,跑十八里路来为你们的李校长——李泽南先生送行,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他在天之灵也看到了,他会感到安慰的。
河水太深,也太冷了,学生们就不用再趟水过河了,就送到这里为止吧,留下几个抬担架的老师和正班主任,其余的老师照顾好各班的学生们,都回学校去继续上课吧。
副校长接着说:“来,全校师生听我的口令,面对唐河,向担架上躺着的李校长的遗体三鞠躬,预备,开始:一鞠躬,二鞠躬,再鞠躬。好,礼毕,让我们一起祝愿,祝愿我们的李校长一路走好!”
“祝李校长一路走好!”
“李校长一路走好!”师生们拖着长腔一起大声哭喊。
呼呼嘶叫着的寒风,师生们发自肺腑的哭啼声,夹裹着潺潺的唐河水流声,仿佛天地都动容了,它们都在呜咽悲啼、、、、、、。
几天后的一个单头日子,司氏因为将近临盆,她浑身瘫软几度晕厥被迫被两个女人搀扶着站在远处为丈夫送行,泪眼模糊中看着自己五岁的儿子——李兴民披麻戴孝由老舅爷抱在怀里,扛着藩杆子,跟随父亲的灵柩和送葬的队伍,一路撒着冥纸,哭喊着把李泽南的遗体安葬在半坡村村北头的一片空旷野地里,从此,她便与心爱的丈夫阴阳两隔了。
不久,司氏产下一男婴,他就是我爱人(李豫)的爸爸,儿子(李明轩)的爷爷——李兴证。
我宁愿相信,人去后,会变成草,变成花,变成一切可爱的植物。
那么,生命还再继续,怀念就会变得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