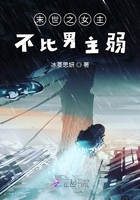到波士顿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去看哈佛大学,但因为是晚上,只能等天亮。一早起来,啃着面包上车。
雨雪霏霏,天空和街道都灰蒙蒙阴沉沉的。车子在一条窄小的鹅卵石路上停下来,两边是一些旧房子和低矮的门面,车子停靠的位置,临着一扇极普通的铁栅门,门两边的红砖垛已经灰黑,里边贴着一间在国内常见的简易房。我以为车子出了故障,却听说:“到了。”也就是哈佛大学到了。那扇门里就是,陪同说,我们现在去正门,一会从这里出来。
原来这是偏门。即便如此,也足让我惊讶:毕竟让世界各国的求知者那么向往的哈佛大学啊。这样的偏门,好像还不如我所在的那个无足轻重的社团多年没有维修的偏门呢。可是拐个弯,到了正门,我的感觉更不止是惊讶,完全就是疑惑了。以为陪同是敷衍塞责,把我们带到了另一扇偏门。结果人家倒很惊讶,反问:“这就是正门呀,怎么会不是呢?”
依旧是已经灰黑的红砖垛,依旧是黑色的铁栅门,只是比先前的那个偏门稍宽,红砖垛上嵌了刻着校名的石头。进门便是穿过楼群的林荫道,远远的尽头,是那座由一个学生作模特的约翰哈佛的著名雕塑。我不能不相信,这就是哈佛大学的大门。
我的惊讶和疑惑,源于我对国内大学校门的见闻。我有一次因为偶然的机会路过一所省级大学的新校区,被其孤零零地突兀屹立于一片广阔旷野上的校门抓住了视线。这几年教育产业化,大学扩招,收费猛增,银行也把大学当作了投资热点,有求必应。同行的人中有个知情的介绍说,该校为建新校区,一口气贷款二十个亿。规划尚未全部完成,但这座宏伟堂皇、傲然雄视、耗资千余万的校门,及其所表现出的主事者的手笔与气魄,已令无数观者咂舌惊叹。
我因为所受教育的主要部分是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日新月异的教育现状几乎没有发言权,我能作的只是事实的对比:
资料表明,哈佛大学自1636年在此马萨诸塞州查尔斯河畔建立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学府——哈佛学院始,370年来,就是从这扇简朴的校门,走出了无数的政治家、科学家和文学家。其中有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几乎所有的革命先驱;有7位美国总统、40位诺贝尔奖得主和30位普利策奖获奖者;微软、IBM一个个商业神话的缔造者;沟通中美关系的基辛格,奠基中国近代人文和自然学科的林语堂、竺可桢、梁实秋、梁思成。美国“总经理摇篮”、美国政府思想库,就是这样一扇门。在这扇门下进出的许多人的一举一动决定着美国的政治走向与经济命脉,乃至世界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的开始和结束。
而国内那所大学,尽管矗立起了足以令哈佛惭愧的新校门,但如何把真正的教育人才引入这扇门依然是最大的苦恼。与此同时,那扇门也依然没有阻止住现有可用师资的流失。
这些年来,国内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其中包括那所大学的负责人,参观过哈佛大学的,肯定不在少数。他们应该都摸过那个已经被无数人摸得锃亮的哈佛先生的铜皮鞋,也都知道当了20年哈佛校长的科南特说的“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知道“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的哈佛校训;知道这些文字所昭示的立校兴学的宗旨:求是崇真;知道哈佛大学在上世纪最后十年平均每年得到十亿美元的社会捐赠,却只是一味致力于世界第一流学府的学术发展而没有重建校门;他们自然更不会不知道我在乡下插队时就听农民教诲过的包子有肉不在折子上的粗浅道理,不会不知道多数纳税人的钱来得并不容易,贫困人群中的学生交的学费更是血汗钱,但是他们依然在校建工程之始毫不犹豫地为一个校门一掷千金,以求政绩之显。并且仿效一时蔚成风气。如果不从经济、法律的角度去作深究,仅仅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看,我们也不能不叹息:我国传统的门面观是怎样的根深蒂固,其现实基础又是怎样的巨大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