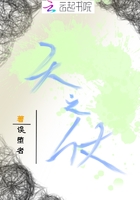一戒非分
跟上世纪80年代初期比,文学的景象和处境都有了极大的改观。但有些同行对此似乎并无意识。常有人觉得只要自己严肃地写了书,出版社就有严肃的出版责任。出版企业化了,责任就转到政府和社会。政府拨款或企业赞助出书被视做天经地义的事情。我在文学社团工作多年,设法找钱帮助作者出书竟成了例行工作之一。常让我想起在乡下插队时的那句老话:“吃粮靠回供,用钱靠贷款。”(那“贷款”其实等于拨款,因为事实上不可能归还)
在社会转型的今天,事情终于遇到了麻烦。
事实上,这类信念从一开始就没有多少合理性。一种产品如果不能经过流通成为商品,就不具有使用价值,也就不具有生产价值,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精神产品或许有些特殊性,也同样绕不过投入和产出的效益法则。倘把出版看做网络,终端在读者,而不在书本身。尤其是小说,成书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有人读。没人读,出版就没有价值;出版没有价值,对出版的投入就是浪费。个人的劳动即便不记入成本,浪费社会的财富却是对纳税人的侵害。
常接到一些基层作家来信,很高兴地告诉当地领导支持他们的情形,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拨专款给他们出长篇小说或小说集。我一面为该地的官员对文化的看重感动,一面却又想,作家辛苦写出,又动用了并不宽裕的地方财政,印出的著作只能是送人或设法摊派,还不知被送或被摊派的人会不会翻开,心里总有些苦涩。如果说,社会为支持受众面较窄的理论研究、扶植有潜质的文学青年或保留有价值的文化遗存适当投入、或业余作者出于爱好自费出书自娱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对于以写作立身的作家来说,写了书不能卖钱反而必须花钱并以此维持甚至壮大职业门面,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打一个也许不恰当的比方,这有点像是残疾人对轮椅的依赖。据我所知,许多真正轮椅上的作家有着极好的市场效应,而一个身体健全的作家却必须依赖资助这把“轮椅”才能在文坛走动,细想起来,总是有点汗颜的吧。
在京开会,听过一位社团分管出版业务的负责人教导,针对有些人以各种吓人的理由强迫出版社出自己的注定赔本的大作,这位负责人很激动地说:“我们党和政府并没有求你当作家,我们有什么义务必须给你出书?”除了“党和政府”是否委托了“我们”代表这一点可以存疑,他的意思是没有错的。
市场很无情,市场也很公平。尽管走俏的不一定都是好书,但好书都一定走俏。关键是作者的实力。一个人本来就不具备某一方面的能力,或者创造力枯竭,明智的做法只能是另择为社会服务的途径,而不是增加社会的消耗。有鉴于此,我给自己立下一条原则,就是决不花钱出小说。这并非是因为我的小说好出,而是恰恰相反。日前一位朋友公干来敝省,便中到舍下小坐。他将近二十年前因为组稿与我相识,而今在京城的一家大出版社担任一个有发稿权的职务,见到我正在电脑上敲着一部就要杀青的长篇,表情竟有些尴尬。我立刻看出,他是在担心我会向他投稿,赶紧说明:因为清楚自己缺乏市场影响力,从不会为难任何出版社,当然更不会为难朋友。每次即便有出版社愿意给我出书,我也总是要反复问人家“会不会赔钱”,请他们三思而后行。要不,赔了钱,首先我本人就会十分地过意不去。
二戒充能
1986年我在洞庭湖北的一所大学读书,湖南的岳阳市文联请我们几个去作讲座。事先广泛张贴了海报,但开场后听众寥寥。错出在岳阳的朋友那儿——他们对我们几个的知名度估计过高。事后他们很过意不去,就安排我们登岳阳楼。接下来的错,就是我自己的了。
岳阳楼一楼和二楼的中堂上都镶着檀木镌刻的《岳阳楼记》,字是世称“行书大妙”的清代大书法家张照写的。二楼那块是真迹,一楼那块是无名氏临摹的赝品。我一面听着介绍,一面很深沉地点头。登楼完毕回到一楼大堂,我一本正经地再次注视那块赝品,感叹说:这真迹比楼上的赝品就是强多了!说完周围一片寂静,我以为众人大有同感,不料同行的一位北京作家忍不住说:你瞎掰什么,这块是赝品,真迹是楼上那块!
当时的感觉真正是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岳阳的朋友赶紧打圆场,说书法是个专业,而且道行很深,许多人都搞不清的。我马上就轻松多了,心里跟着就自宽自解:谁都会有知识盲点的,今天搞不清明天搞得清。
得了这个教训,我决心认字。我下的工夫不小,常常把古人的字帖放大复印,把家里和办公室的一整面墙壁贴满,不时面壁。不过也就是为多认些字而已,对那教训始终没有更深的认识。
不久前,一位由朋友介绍的来客造访,见面奉送其刚编辑出版的一大本画册,上面每一面是他与一位艺坛精英的合影,许多名字都是日常间如雷贯耳的。其中书画界的名人几乎个个是泰斗级,中国大小城市的各类牌匾上一不小心就能看到他们的落款。这来客的来头也就可想而知。他似乎也因此为人就极痛快。见了我办公室那一整面墙上的字,毫不犹豫就指点我说,你这行书写得可不怎么样,不妨学学草书试试。我刚要说明什么,他以为我怀疑他的权威性,立刻就打断说:我是整天在大师门里进出的,他们一人扔我一句我也早饱了。那“饱”自然是饱学之饱。
其实我要说明的是,那面墙上的字乃是张旭、怀素、黄庭坚之后的草书圣手祝允明的手迹。内容是杜甫的《秋兴八首》,为祝允明平生得意之作,是草书艺术的经典之一,所谓“怒龙喷水,奇鬼搏人”,使后来不知多少书家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如此窃誉。但我终没有说破,以免有失厚道,因为当时有第三者在。
这件事像一面镜子,照出我当年在岳阳楼的出丑。这一次因为处于旁观的位置,也就把那丑态看得格外真切,不由又一次全身燥热。忽然明白,我当年的问题并不在于搞不搞得清,而在于根本搞不清而冒充搞得清。形容这类冒充,我先前插队的九江乡下有一句村言,说是“手捏鸡巴充六指儿”,话是粗了些,满是那么回事。
也许我至今没有避免、将来也不能保证不会因为充能而出丑,但我肯定会努力把不充能作为为人行事的一种必修的课程。
三戒凑趣
上世纪80年代,出国是一件很风光的事。尤其作家出国,更是成就和影响的一个标志。作家们凑到一块,一个少不了的话题就是出国,没出的总是忌妒出了的,或是抱怨主办者的不公。但我从不这样看。只要听说谁出国或出过国,我马上就崇拜得不得了,哪怕那作家的作品我从未拜读过。1985年,我也非常意外地得到一个公派出国的机会。我所在的省根据与当时的马其顿共和国签订的文化协定,派我去参加他们举办的“斯特鲁嘎国际诗歌节”。对我这样一个刚从乡镇调到省里来的文学青年,这无疑是莫大的荣幸。我真是兴奋得很。虽说是地方粮票,买的粮是一样的,不都是出国么!到了地方,我又知道,国家作协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参加这个诗歌节,当地接待单位让我跟这代表团一块活动,使我一下子身价陡涨,从地方级升为国家级。明知是滥竽充数,还是不免窃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