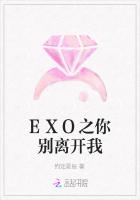1
你请等着,有一天我非和你离了不可!
返乡回到坡头村插队的时候,我就听孙天欢这么说了。他是说给他的女人乌采芹的,对自己的女人说这样的话,他该是个绝情的人呢,他的女人听了,却一点都不以为意,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连和他顶个嘴的表示都不会有。事隔三十多年,我再次回到坡头村来,再听孙天欢这么说,我就像听一个老掉牙的笑话,觉得既无聊又无趣,抽身在一边,向孙天欢挥着手就要离开。孙天欢却没有放过我,他拉住我的衣角,退到他家的苦楝树下,再一次给我强调了他要离婚的决心。
孙天欢说:你不相信我?
我有意调侃他,说: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今年你五十八岁了吧!
孙天欢说:我心想,你是知道我的。
我说:我当然知道你,知道你有多大的年纪了。
孙天欢是敏感的,他敏感到我话中有话,就又带着些强调的意味说:这和年纪没有关系。
我和孙天欢就没有办法说话了。回到返乡插队的坡头村,我有许多要拜访的人。当然,孙天欢也是我计划中拜访的故交,但他节外生枝,把我截住在他家门前的苦楝树下,开口就说他要离婚的事,我就不愿意听了。想来不只是我,一个神经正常的人,多少年没回旧村子,回来了,谁愿意听别人说他离婚的事?这有违人性的,同样又有违世情。但我能有啥办法呢?孙天欢把我扯在他手里,我没有办法,就只有硬着头皮听他往下说了。
我听着,觉得孙天欢这一次不像过去,只是吊在嘴皮上说一说,看来他是真要和他过了大半辈子的女人乌采芹离婚了。
他有什么资格离婚呢?
在坡头村,孙天欢实在算不上个人物,甚至连农夫们与生俱来的质朴勤快、吃苦耐劳的品质,他都十分缺乏,嘴馋身懒、油腔滑调,没有多少人待见他。当然,这只是地道农夫的看法,到了他的女人乌采芹眼里,就都不是缺点了,而是一种优势。孙天欢爱好戏曲,向往一种体面的生活,对有文化的人,他无条件地喜爱和尊重。
坡头村有个下放回村的右派,原在陈仓师范学院教国语,在村里接受劳动改造。孙天欢不管这些,以为他是大文化人,这就对他亲得不得了,有事没事,都愿意和他粘在一起。运动来了,老右派不可避免地要被拉出来游行,孙天欢看不过眼,在别人斗争老右派时,他随在老右派一边,陪着老右派一块走。
村上人说他了,说他凭什么来陪人家老右派?他理直气壮地和他们争辩,说他怎么就不能陪?村上人说老右派有文化,有文化的人反动!孙天欢就很自豪地说了,我也有文化呀!
村里人奈何不了他,就由着他去了。
每一次都是这样,他陪着老右派游斗结束后,别人一哄而散,唯有他不走,小心照顾着老右派,搀着扶着把老右派往家里送。也是老右派的年纪大,有一次,挨斗的时间长了,脚不能挪,手不能动,一下子瘫在台子上。孙天欢见状,就爬到台子上背起老右派,一只手里拿着老右派戴在头上的高帽子,一只手里提着老右派挂在脖子上的大木牌,一脸的无怨无悔,很是愉快地送着老右派往他的家里去。
我那时年轻,不懂得人情世故,看着孙天欢又要负重背着老右派,还要拿着老右派挨批斗时必不可少的高帽子和木牌子,只觉手忙脚乱,很是好笑。我便突发奇想,跑到孙天欢和老右派身边,把高帽子和木牌子从孙天欢的手里接过来,嘻嘻哈哈乐着,给孙天欢戴在头和脖子上。
纸糊的高帽子可是不好戴呢!粗粗拉拉几根竹片,胡乱扎个样子,糊上纸,写上字,戴在头上是极不舒服的!何况木板钉制的大牌子,系在一根细细的铁丝上,挂在人的脖子上,还不像刀子一样,直往人的肉里割。
这是我的恶作剧了,孙天欢没有因此而恼我,他坚持背着老右派,从坡头村的街巷里走……好像是,把高帽子和木牌子从他的手里解放出来,他不仅能把老右派背得扎实稳妥,而且又还很享受头戴高帽子、胸佩大木牌的待遇,感觉那是一种多大的荣誉似的。
刚刚开过老右派的批斗会,村子里的人,无分男女,无分老少,其时也都在街巷上散散地走着,孙天欢的举动,让大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投向他的目光,也便十分茫然,直到我把老右派的高帽子和木牌子戴在孙天欢的头和脖子上,让茫然的人群,才不知所以地爆发出一阵哄笑来。
哄笑声是我期望的,但是来得突然,去得亦很突然,都在一瞬之间,便又安静下来,相互招呼着,为孙天欢让出一条道,使他顺顺当当背着老右派,从大家的眼皮底下走过。
我敏锐地感觉到村里人对于这件事的变化,那绝对是发自于情感深处的变化呢!大家乐意孙天欢帮助老右派,并为此而敬重他。
在那一刻,我有一种良心发现般的羞愧,于是,我再次跑到孙天欢的身边,想要从他的头和脖子上摘下高帽子和木牌子,却被孙天欢强硬地拒绝了。
我为此悔恨而难堪,在以后的日子里,都不敢再见孙天欢,偶然地相遇,我也是低着头,匆匆地走过。
孙天欢不想我难堪,找着机会与我接近。
这个机会在一个晚霞灿烂的傍黑毫无预兆地来了。那天,在他家门前的苦楝树下,他扎势坐在苦楝树裸在地面上的一条大根上,扯着他的胡琴,自娱自乐地唱他深爱的一折秦腔。
孙天欢唱的那折秦腔,我至今记得其中的几句:
陈老大我不怕腰痛腿酸,
为只为小兄弟能把书念。
虽受苦也觉得心中喜欢,
急忙儿担柴担赶回家园。
我后来查了孙天欢那晚唱的这几句戏词,知道来自《打柴劝弟》的一折戏。
那个傍黑天,孙天欢很努力地哼唱着,身边围了许多人,我从他们的身边过,原想默默地躲过去,不承想,人圈子里的孙天欢,用秦腔白口叫住了我,而且还用秦腔白口劝了我几句。原话被他的秦腔白口说得抑扬顿挫,极富感性色彩,要我放宽心,天下的事都别往心上挂,他相信知识,知识不是喂猪,吃饱了只知道睡觉,有一天是会醒来的,醒来在有准备的人身上。
我把孙天欢劝我的话,一字不落地记在了心里。回味他的秦腔白口,忍不住抬头看天,我看见了头顶上的苦楝子花,蓝莹莹的,微微地散发着一种苦涩的芬芳;透过繁盛的花色,我还看见遥远的银河,正有无数的星光,闪闪烁烁,似乎也微微地散发着一种苦涩的芬芳。
因此,我和孙天欢成了好朋友。
我不仅和孙天欢成了好朋友,通过他,还和老右派交起了朋友。我是好读书的,有一些学习上的困难,就去找老右派请教。后来右派平反,我参加高考,老右派重回陈仓师范的教堂,我进入陈仓师范读书,获得了老右派非常多的帮助。每每想起这些往事,我都对孙天欢有种无以报答的感动。不过,这不能掩盖孙天欢其他方面的问题,譬如他好赌博,还好钻别人家女人的热被窝。
让我怎么说他呢?
他孙天欢老了,还闹什么离婚?
如果真要闹离婚,倒是他的老婆乌采芹比他更有资格。
2
乌采芹按照坡头村的话来说,没出嫁时乖爽,嫁给孙天欢后干淑,有孙娃后齐整。
怎么就是乖爽?怎么就是干淑?怎么就是齐整?我以为是要作些解释的。返乡插队在坡头村的日子,我注意到,在他们的语言体系里,没有漂亮、美丽那种挂在人们嘴上的形容词,有的是他们习惯了的说法,很家常,也很得体。村里人夸奖乌采芹乖爽,是说她做姑娘时,是懂事听话的,是单纯爽快的。嫁给了孙天欢,她身份一变,既为人妻,又为人母,进了家门,要养孩子要做饭,还要侍候老人和男人,喂猪喂鸡,脚不闲、手不闲,出了家门,下地务弄庄稼,与亲戚邻人交往,有做不完的活,说不完的话,却还能保证自身的整洁与淑仪,实在不易。而到她怀里抱上了孙娃,眼见儿孙绕膝,不论他们对错,她都一脸的包容与愉悦,不愠不火,可就更是不容易了。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乌采芹不操心治国的事,更不操心平天下的事,可以齐家就是她最大的理想了。
乌采芹的一生,于坡头村的女人来说,是绝少的、体验了这三种境界的。
她这样一个身子勤快、心眼儿活泼的人,却是那么奇怪,倒像对身懒嘴馋,而且好赌花心的孙天欢很有感觉。在别人的眼里,孙天欢是不怎么受待见,但在她的眼里,却怎么看怎么舒服。譬如她就十分欣赏孙天欢身上的那种读书人的做派。
说来有趣,坡头村的开创者,原来就是一个读书人,明朝末年的时候,还有幸考取了使其家族荣耀不已的功名,做过州府一类的官员,具体的政绩史无记载,只是传说他愤恨政权的变易,而且又深蕴一股子强烈的乡土情结,这便回身故里,隐居不出,过着耕读传家的那种日子。这让后来的坡头村人,对他们的这位老祖宗颇多微词,说是城市多好啊!他咋就不喜欢城市,而喜欢农村呢?微词奈何不得躺在坟墓里的老祖宗,大家就还遗憾地在坡头村讨生活了。可是,后辈儿孙不懂得老祖宗的深刻理想,他们不断地退化着,退化到后来,就只剩下了一个耕,而没有了读。返乡插队在坡头村里,我没少听人讲那位远去的老祖宗,我虽然听出了坡头村人叙说中的微词,却也听出微词背后的骄傲。不过,我也看得出来,这个时候的坡头村,读书是件多么奢侈的事情,既奢侈又无用。出现一个孙天欢这样的人,实在是一个例外。不知谁说的,称呼孙天欢是村里的一只马犄角。
马长犄角吗?没有。
这充分说明了孙天欢的稀有,不仅如此,他在十多岁的时候,有位游方道士到坡头村来,向村里讨了口食吃,吃的时候,看见了蹦跳戏耍的孙天欢,把游方道士惊讶得放下碗,喊孙天欢到他跟前来,双手捧着孙天欢的脸,嘴里念念有词,说了一堆“天庭饱满,地角方圆”的话,最后很是恭敬地称呼了孙天欢一声:县长。
县长……啊啊,孙天欢有县长的命吗?
有没有这么贵气的命相?不到最后,谁能料得准呢?但他县长的外号,从此吊在了坡头村人的嘴上,很是叫了一段时间,直到“文化大革命”,孙天欢不畏造反派,而善待一个老右派的事不断被演绎着,他“县长”的外号被人渐渐地淡忘了,以至现在,几乎没有谁再说起,他还有那样一个绰号。
乌采芹之所以嫁给孙天欢,不知可与游方道士的预言有关?但她处心积虑地嫁给孙天欢,肯定与他的做派关系甚大。
乌采芹说过,她喜欢有文化的读书人,而孙天欢正好具有乌采芹所喜欢的那种潜质。在坡头村,孙天欢是继老祖宗之后,很少有的一位读书人,他像模像样地读着,都已读了初中,升到县城高中,一路读着书,几乎只差一次高考,就能顺利跳出“农”门,却被突然爆发的“文革”,断送了他的前程。不过,他读书人的习惯没有变,从头到脚,都时刻注意,唯恐沾染上别的什么……那时,坡头村叫坡头大队,村民叫社员,社员们都穿自己家里纳底子上帮的布鞋,想都不去想皮鞋。孙天欢却不,他下地时穿布鞋,回到家里,就换了布鞋穿皮鞋了。
老祖宗是个读书人。老祖宗开创了坡头村。孙天欢是读书人,孙天欢穿皮鞋无可争议,而且是开天辟地第一人。
在坡头村,孙天欢创造的第一多了去了,刷牙是一项,理发又是一项,而且在穿衣上,也是一定要出新的。
村里人都还包裹在棒棒袄儿粗布衣之中,他却时刻穿得与公社的干部一模一样。那时的公社干部,都流行四个兜儿的中山装,孙天欢上了三次北山,砍来柴火,用架子车拉了,卖给周村镇上的国营食堂,换来钱票子,数都不数,捏在手指尖上,一刻不停地去街上的裁缝铺,给自己制作一身中山装回来。
每日清晨的时候,坡头村人睁眼就会看见,孙天欢在他家门前的苦楝树下,满嘴白沫地刷牙,然后又涂上肥皂,用专业的剃须刀,小心仔细地来回刮脸……孙天欢的做派,坡头村还有谁吗?没有了,他是唯一的,他理所当然地成了坡头村难得一见的风景。
刷了牙,剃了须,回到家里,孙天欢就对着家里那面破了两道裂线的镜子来穿中山装了,仿佛一个神圣庄严的程序,他穿得很谨慎,很慢,先把一个袖子穿上,抻一抻袖口,再穿另一个,再抻一抻,然后就是系扣子了。系扣子时依然神圣庄严,每系好一颗扣子,他都要侧脸这样一瞧,侧脸那样一瞧,瞧好了,还不忘用手把扣子拍一拍……总之,他穿中山装要用去很长时间,那些时间里,消耗给自我欣赏的部分似乎更多一些。
孙天欢本身确有自我欣赏的条件,正如游方道士所说,他五官端正,脸型方正,加之不间断的田间劳动,又给他涂抹了一层黑里透红的太阳色,这便显得更有气质。
喜欢有文化的读书人,乌采芹没有不被孙天欢折服的理由。
孙天欢的形象和做派,不只乌采芹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还有一些如乌采芹一般的女子,喜欢有文化的读书人,也都昼有所思、夜有所想地喜欢着孙天欢。
乌采芹感觉到了那样的危险,她比那些觊觎孙天欢的女子,多了一个心眼,早来了一手,抢先把孙天欢拉进她的怀里,让孙天欢别无选择地成了她的人。
机会来自于一场电影,周村镇放映一部从朝鲜引进的电影《卖花姑娘》,孙天欢去了。他去得不算很早,但也一定不晚,差不多刚好赶在快开映时,出现在人山人海的电影场上。他不往人群里靠,更不往人群里挤,他就那么孤傲地站在一边,离着人群两三步的样子,举目去看高杆上的银幕……正是他的这一姿态,引起许多女子的青睐,他鹤立鸡群地注目于前头的银幕,青睐他的女子,则你偷看他一眼,她偷看他一眼,他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他笔挺的中山装上,挂满了女孩子偷看他的眼睛……也是《卖花姑娘》的剧情太悲惨,现场观看的人群里,就有了一阵一阵的抽泣声,孙天欢知道自己眼睛也湿了。恰在其时,有一只雪白的小手,拈着一方同样雪白的手帕,移到了他的脸上,替他来擦扑出眼眶的眼泪。孙天欢愣了一下,他抬起手来,猛地捉住那只手,低头从手上看起,这就看见了也在流泪的乌采芹。
乌采芹想把她的手从孙天欢的手里抽出来,抽了几下没有抽动,也就不抽了,任凭孙天欢抓着,双双退出抽泣声一片的电影场,去了周村镇外的一片芦苇地。
在那里,他俩抱在了一起,抱得很紧很紧,都快抱成了一个人。
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两人在周村镇看一部名叫《南海儿女》的国产电影,看了没有多长时间,看不进去,就一前一后地出了电影场,一前一后地又去了镇外的那片芦苇地……头一次去芦苇地,还是酷热的夏季,他俩相拥在芦苇地里,总有一种青草生长的气息,浓一股、淡一股地往他俩的鼻孔里钻,这一次再来,就已到了秋天,芦苇生得很高,他俩钻在里边,就如埋身在一片碧翠的湖水里,而他俩看不清楚的湖面上,正有白色的芦苇花,在风的鼓动下,起起伏伏,泛滥出一波一波的雪浪……钻进芦苇地的孙天欢和乌采芹能干什么呢?像头一次一样,紧紧地,搂抱成了一个人。
孙天欢给乌采芹说:你别不是眼瞎了?
乌采芹抱着孙天欢不出声。
孙天欢就还说:我会叫你吃苦的!
乌采芹把孙天欢往紧里又抱了抱,还是抿着嘴不出声。
孙天欢就又说:你难道乐意吃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