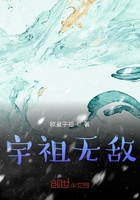茯若只在殿中静静出神,却是宝带道了句:“皇后娘娘在想些什么?可是在忧心皇上的身子?”
安尚仪给茯若上了一壶茶,只是道:“娘娘忧心也是无法,但好歹皇上还有太医照料着,但这话原是不该奴婢说的,乾元宫的人都说皇上的身子丝毫不见起色。”安尚仪停顿一二,往下的话,自然也是不敢再说了。
茯若闻了,神色却是恍惚而又凄凉。冷冷道:“便是皇上如今去了,本宫又如之奈何。且说如今本宫的叔父与兄长虽说在朝中官居高位,但到底势单力薄了些,不似得昭惠太后的族人,都是一品大官的位子上。且若是此刻皇上没了,在朝中垂帘听政的人又是昭惠太后,本宫往后的日子越发难过了。”
安尚仪淡淡笑道:“皇后娘娘多虑了,饶是垂帘听政之事交由昭惠太后,但若是娘娘乃是正宫皇后,若是太子登基,自然便是独一无二的皇太后了。难道娘娘还担心什么?”
茯若蹙眉道:“话虽如此,但依着昭惠太后的性子,若是她一手掌握了朝政,那么本宫的父兄的仕途便会生出波折了,且说如今太子妃与薛良娣的母家都与上官氏走得近些,本宫费尽心机挑唆皇上打压了澄儿,就是不欲让昭惠太后身边的人再度占据了后位,如今瞧着,本宫的心思算是白费了。”
漏液时分,因着茯若乃是皇后,且又下旨不许嫔妃随意往乾元宫去,生怕打扰了询养病,故侍疾的担子便由茯若一力承担。
入了内殿,微酸的药气扑入茯若的鼻息,她瞧着病体沉珂的询,只是淡淡笑道:“皇上服药了可好些了么?”
询只是清冷笑道:“朕的身子一日不如一日,兴许皇后如今已在盼着皇太后的位置了。又何必再来担忧皇上的身子呢?”
茯若神色平静,只是笑道:“皇上说笑了,臣妾乃是皇上的妻子,怎会有这般大逆不道的念头,且说若是皇上没了,臣妾即便成了皇太后,也不过是一介孀寡。那又有什么意思。”
询的神色稍稍释然,只是缓声道:“是啊,皇后说的在理,这后宫四堵高墙,在里头困着着实无趣,但皇后这些年不也都已经这般过来了,当了皇太后也是一样,亦没有什么分别。”
茯若只是温顺笑道:“臣妾有一事想着,只是想起,以往皇上身子康健之时,倒是时常和臣妾一齐商议朝政,臣妾虽说是妇人,但对于朝政之事倒是知道的不少了。”
询闻了,只是淡然笑道:“你乃是皇后,朕在后宫里头又没有旁的人可以商议,玉璃虽说与朕亲近,但这些政事叫她知道朕只觉得不妥,但叫皇后知道,这却是无妨了。”
茯若徐徐道:“既是这般,皇上又为何不让臣妾垂帘听政,既然皇上让臣妾好生照顾溶儿,若是来日溶儿登基,臣妾在他成年之前,只替他打理朝政,且说昭惠太后到底年长了,倒不如将此事托给了臣妾,且臣妾到底是溶儿的嫡母,我朝昔日有宣顺太后孙氏垂帘听政的旧历,若是新君年幼,自是由太后听政,哪有太皇太后来擅理朝政的道理,皇上到底要三思。”
询迟疑片刻,只是冷笑道:“说了半日,皇后原来还是惦记着执掌天下的权柄。朕原还以为,在皇后心中最最看重便是朕这个夫君。”
茯若亦是冷笑相对,道:“皇上说臣妾恋栈权位,但皇上又何曾看重过臣妾这个皇后,臣妾在后位上如履薄冰多年,都是因为皇上对臣妾的猜疑与淡漠。”
询怅然只笑出声,道:“说到底,皇后的心里到底是恨毒了朕的。”
茯若平声道:“臣妾不恨皇上,只是自己这一生到底身不由已罢了。”
询道:“朕为了顾全你与昭惠太后,亲口下旨赐死了玉璃,只是她死前,一直在说自己是冤枉的,如今,朕只想问问皇后,那些事难道是皇后算计的。”
茯若微微含笑,缓缓靠近询,只是笑道:“皇上说笑了,且不说昔日张氏借由戕害肃悯太子来污蔑臣妾,累的臣妾被废黜出宫三年,如今这件事也只当是臣妾以眼还眼罢了。”
询只是茫然道:“是了,原来竟是朕冤了她。”
茯若冷冷笑道:“是了,再者,昭惠太后说一定要赐死皇贵妃,不单单是因为她放巫蛊诅咒臣妾与太后,也还有她暗中谋害了淑贵嫔萧氏的缘故,只是因为她的歹心,累的四皇子涵生下来便没了母亲。到底也是作孽。”
询显然为此事有些惊惧了,只是喘气道:“什么,清漪乃是玉璃害死的?怎会这样。”
茯若明艳一笑,道:“不是皇贵妃害了淑贵嫔,而是臣妾做的,只是由皇贵妃担了这虚名罢了。”
询闻了,只是如摧枯拉朽一般倒了下去。只是咳出了几口血,无力道:“毒妇,你当真是用心歹毒,朕当初真该废了你,把你打入冷宫,叫你永不超生。”
茯若只是明艳冷笑道:“皇上若是思念皇贵妃,只是早早去了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不好,也省的皇贵妃在十八层地狱等你等的太过于凄苦了。”
询显然是气急了,只是咳出一大摊血来,殿外风声簌簌,戍守的侍卫太监早早的被茯若遣走了。且询也没了力气来叫喊。只是大口大口的喘气。他连日来身子的薄弱让他再也不能承受丝毫的惊惧,而他许是气极了,只想着坐起来扯住茯若,谁知竟是半点气力也无。只是又倒在了床上,胸口起伏。挣扎片刻,终于没了声息。茯若缓步靠近他,只见他鼻息已无,双目紧闭,茯若只松了一口气。缓步出了乾元宫。
行到外头,高柱早早的就在外头候着,只是上前问道:“皇后娘娘,皇上怎么样了。可好些了。”
茯若神色静静的,语气淡淡:“皇上驾崩了。”
茯若伫立在凤仪宫漆黑的内殿,心里的悲凉一丝丝泛起,她爱的,爱她的,都在手里一手葬送了。眼角的泪水缓缓落下,仿佛还记得昔年在永和宫那些时光,茯若思索良久才回过神,不论如何,她最深爱的,还只是询罢了,只是如今这个男人已经永远离开自己了。
宣和二十三年,夏侯询逝于乾元宫,追谥于“宣和帝”,庙号宣宗。同元后徐氏同葬安陵。太子溶继位,尊嫡母宋氏为仁穆皇太后,祖母上官氏为和敬太皇太后。并立太子妃傅氏为皇后,良娣薛氏为昭仪。四皇子涵册为英顺王。
过了三月,待得询的丧仪完了,仁贵妃闵氏晋为仁德贵太妃,宜贵妃晋为宜安贵太妃。黎昭仪晋为丽太妃,蒋昭仪晋为敏太妃。低位分的嫔妃都一律迁到西京行宫里头去安度晚年。除了仁贵妃与宜贵妃,亦或是黎昭仪这些个一品位分的嫔妃,亦是改居了后宫北苑的颐宁宫。
茯若正在凤仪宫中微微出神,安尚仪进来,低语道:“太后娘娘,太皇太后来了。”
茯若冷笑片刻,道:“此刻她来做什么,难道垂帘听政了过后,竟还有闲情来哀家的凤仪宫这儿?怕是又生出什么别的事。”
正在言语间,太皇太后进来笑语道:“皇太后这几日是怎么啦,怎的哀家来了,也不出来迎接,越发没了规矩。”
茯若淡然起身行礼,随即推到下首的座位上,只是淡淡道:“臣妾眼下成了寡妇,到底心里感伤,一时间疏忽了也是有的。”
太皇太后冷冷一笑,道:“左右太后往日和先帝也没有什么情分,先帝在世的时候那般的冷落你,便是你的后位也是坐得不稳,如今他去了,你便是后宫不可动摇的太后。你该高兴才是,何来感伤一说呢?”
茯若端然道:“是啊,先帝在世的时候,厌弃了臣妾,便如同明宗皇帝厌弃太皇太后一般。左不过都这么过来的。”
太皇太后道:“哀家今日前来,无非是想着让皇太后移宫罢了。眼下皇后已立,但皇太后还是牢牢占着凤仪宫,皇后在翊坤宫住了许久,哀家思量着倒也不妥。因此还请皇太后早些搬离了此处才是。”
“臣妾原想着入寿康宫居住,但内务府的人说寿康宫年久失修,还望臣妾再多多等候数月,这才耽搁了下来。”
太皇太后冷冷瞧她一眼,只是道:“这原是哀家的意思,哀家却是想着,那寿康宫原是仁惠太后的居所,虽说她殁了许久,但眼下皇太后便住进去到底不妥,依着哀家的意思,还不如请皇太后往寿安宫去住吧。且左右也是个清净地儿,且皇太后在后宫操劳了数十年,如今是该寻个清净地好生颐养天年的时候了。”
茯若缓缓吸一口气,沉稳道:“太皇太后不可欺臣妾至此,臣妾到底先帝的正宫,乃是先帝的嫡母,怎可让臣妾去屈居于那妾妃所居的宫室。”
太皇太后沉吟道:“你自然是皇太后了,但那寿安宫也自然是供皇太后所居的宫室,你且也不必先搬出昔年孝武太后和宣顺太后的旧历来,哀家让你居寿安宫,就是为了让皇太后明白一件事。在这前朝后宫,做主永远都是哀家这个太皇太后,这个理儿,还望皇太后牢牢记着。”
正在言语间,太皇太后拿出一道谕旨,只是交由茯若,缓缓道:“皇太后且亲眼瞧瞧。”
茯若只是缓缓打开,只见上头写着“如宋氏于后宫前朝生事,可凭此谕旨废黜之。”上头乃是询的亲笔,再附有他的朱印。
绝望的气息迅速淹没了茯若,她只是软软的瘫了下去,再无力气。
太皇太后睨了茯若一眼,冷声道:“先帝让哀家垂帘听政之事,便料到你会不安分,所以哀家让他写了这样一道遗诏。眼下皇太后的性命,可是被哀家攥在手上了。”言毕,她只是扶着洪尚仪走了出去。
次日,茯若迁居寿安宫。茯若住进这里的第一晚,心里只是想着昔年到仁惠太后的宫室来问安,如今自己竟也住到了这里,但心境早已是大大的不同了。
深夜醒转,只吩咐宝带端茶来,宝带宽慰道:“太后娘娘,眼下虽说是在寿安宫,但好歹娘娘已是皇太后了,且皇上皇后每日都是按时来给皇太后问安。依着奴婢瞧着,皇太后也不必过于忧心。好歹你膝下还有英顺王呢。”
茯若眸光如利剑般倏地一亮,恨恨道:“这个自然,无论如何哀家都是皇太后,上官氏权势再大,终有薨逝的那一日。”
宝带道:“眼下皇太后还是好生休息一段时间才是。好不容易才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茯若阴沉道:“哀家自入宫后,这日子哪有一日是安稳的,若要哀家真真高忱无忧,且让涵儿坐上了帝位,哀家在帘后训政才算。”
后宫茯若传第五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