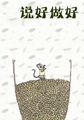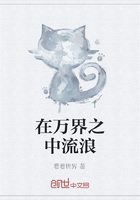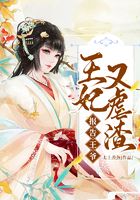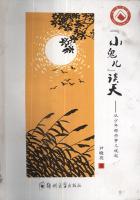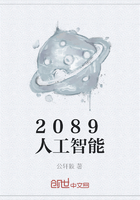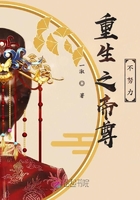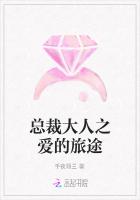所以,我深深地为她而感动,她走过来了,赢得了这场胜利。我也为我自己感动,因为,直到今天,我会听到越来越多的人说,从没见过像你这么快乐的四号。我说,是的,我很快乐,但是,更多的时候应该说是平静,我找到了内心的平静。
内在事与外在的事
内在的事与外在的事是有些不同的,它们有时候还会带来很大的矛盾,它们甚至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标准,同时经验内在与外在,有时候会让人产生严重的分裂感。不要完全的拿内在的标准来做外在的事情。
有人问:我很愿意修炼内心,能找到宁静完整的感觉,但感觉自己还是对修炼的思想和方法比较有依赖性(比如网上的文章,你的博客等等),对修炼时间的要求越来越多,有时就像上瘾一样。可我的面包怎么办?我过去是个心气很足的人,现在却感觉失去了奋斗的动力。我该怎么找回来(可别告诉我我生来就是完满的,我需要面包)?怎么平衡修炼和奋斗的时间?
我听说有一种鸟,它们生活在水边的悬崖上,生存条件非常艰苦,常常不得不挤在一小块岩石上,还没有学会飞行的幼鸟一不小心就会被挤落到水里淹死。最悲惨的是,这些鸟儿的寿命非常之短,短到只有一天,从出生到老死,只有一天。但是,在这一天的时间里,这种鸟不仅要学会飞行,还要觅食、求偶、交配、繁衍下一代,并为了自己的立碓之地而与其它的同类打得你死我活......恶劣的生存环境让它们变得很好斗,也很顽强,但是,无论它们如何顽强如何奋斗,它们的寿命都只有一天!
人类听到这样的故事,第一反应就是,何必呢?才一天!是呀,何必呢?对于平均寿命已经有七十岁的人类来说,一天,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啊,那些争斗值得吗?它们甚至显得非常可笑。
是的,在我们的眼里,那些鸟儿是既可悲又可笑的。可是,我们人类不就是这种鸟吗?七十年,相对于鸟儿来说,显得多么阔绰而漫长啊,可是,当你站在宇宙的高度,七十年也就是一瞬间而已,而人类现在所做的一切,不就是和那些鸟儿一样吗?很多人无数世的时间都浪费在那些无谓的奋斗上了。
当然,我们谁也要面包,要在这个世间生存下去,这其实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的生命被这些外在的事务所完全的掌控了,你跟你的内在的心失去了联系,你变得六神无主。一旦你丢失了自己,你就会有一个强烈的向外的驱力,不停的想要奋斗,想要抓住一些什么,可是这个向外的驱力会让你越来越远离自己,也就是,你向外走的越远,你就会离自己越远,你的恐惧与失落感也就会随之加深,一定是这样的,它不会有第二种结局。前不久,有一个金融大锷魏东自杀了,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极度向外求,而没有向内的例子。
一个真正向内走的人是不可能选择自杀的。他只会越来越喜悦,越来越宁静,越来越享受生命,他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充满着祝福的。他的内在会满溢着爱与幸福,他只需要获得一定的生存条件就可以了,他不会无休止的不断的想要更多更好,以至于这种追求更多更好的习惯变成了他的强迫症。一个向内走的人会在他的内在找到那无穷尽的宝藏,海洋太大,他只取他所需的一瓢水就够了,他不会贪得无厌,因为他知道,他其实就是大海。只有内在匮乏的人才会不停的去奋斗屯积,他们总是会担心,只要一不奋斗,他就会挨饿受冻。
亲爱的,请不要误解我,我并没有教你不要外在的世界。我们生活在红尘,只要我们没有出家,至少就得为自己的衣食住行负责。但是,要小心我们的贪念。欲望本身没有错,我们饿了就要吃饭,冷了就要穿衣服,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我们总是想要更多的贪婪上,它的背后就是恐惧,害怕自己活不下去,而我们从小的教育很多也是基于此的,“现在不好好读书,将来只能穿草鞋”,所以,很多人从小就害怕活不下去或活得不好,而因为这样的恐惧也对自己深怀自责,有的人不停的工作,不让自己休息与娱乐,一歇下来就有内疚感,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仿佛自己的生命如果不“做”点什么,“生产”点什么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但实际上,他们都错过了最根本的,你来到这个世界所需要做的最大的功课就是,找到自己,做你自己,这才是你真正的“工作”。然而,你却因为自己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而感到不安了!就算我们每个人都能活到八九十岁,可是我们的前三四十年都已经真正的“浪费”掉了——浪费在那些无谓的事情上了。事实上,五千年来,看似人类创造了外在的文明与进步,但是,人们却从来没有在他们的内在世界里移动过半步。现在,你已经开始向内移动了,这多好!向内走吧,你将收获整个世界!
当然,内在的事与外在的事是有些不同的,它们有时候还会带来很大的矛盾,它们甚至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标准,同时经验内在与外在,有时候会让人产生严重的分裂感。不要完全的拿内在的标准来做外在的事情。比如说,在内在的过程中,我们说不要用头脑,只要用你的心,可是往往在外在的世界中,我们是需要用我们的头脑的。否则的话,我们连办公室的门在哪里都会找不着。当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同时兼顾内在与外在会创造出一些矛盾,会引起内在的冲突,我的经验是,去经验那些矛盾与冲突,换着法儿的去经验它们,直到有一刻,它们全都消弥了,你会发现,其实没有内外之别。外在的世界就是你内在世界的反映。如果你的内在是统一的、和谐的,充满宁静的,你会发现,外在的世界也开始变得和谐与美好了。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我所主张的向内走,它不是脱离日常生活的弃俗的行为,恰恰相反,它是浸入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的,浸入到我们的谋生过程中。带着觉察,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中,你甚至根本就不需要专门花时间坐在那里打坐。对于初学者来说,每天早晚花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来静心是很有帮助的。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培养我们在日常言行中的觉察力,也即是活在当下的能力。当我们可以带着这种静心的品质去谋求生活的时候,庸常的生活也变得充满了神性的美好,这才是它的奥秘。
我们都是神投手
我们每个人都像一个功能强大的投影仪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忙着将自己内心的负疚和不安投射到别人的身上,极少有人能够面对真相。
投射(project),是心理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主体将自己不希望具有的特征归咎于他人。说的形象一点,就是把自己不喜欢的思想观念以及情绪等,扔给别人,认为是对方的错。
有一个故事最能说明投射的含义。话说苏东坡和佛印是一对好友,有一天,苏东坡与佛印一起打坐,他们从定中出来以后,苏东坡告诉佛印,你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吗?佛印摇头说不知,苏东坡说,你在我心中是一坨屎。佛印笑而不语,苏东坡忙问,那我在你心中是什么?佛印说,你在我心目中是一尊佛。苏东坡十分得意,啊,原来我是一尊佛!回家后急忙告诉他那个出了名的才女妹妹苏小小,小小一听就乐了:心中有佛自然见谁都是佛,心中有屎自然见谁都是屎了!
我们常常说,别人是自己的镜子,也就是说,我们从别人身上所能看见的,其实都是自己内心的东西,除此之外,我们不可能看见其它任何东西。实际上,心理学中所说的投射也有两种,一种是向外的投射,即:都是你的错!另外一种就是向内的投射,即,我们把外在环境中出现的不好的事情归咎于自己,都是我的错。孩子们天生具有一种向内投射的本领,爸爸妈妈吵架或者离婚,几乎每一个孩子都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内疚感,觉得是“我不好”而导致的。慢慢地,这种深刻的“我不好”积累得够多了之后,内心无力承受了就把它扔出去,说是对方的错。
因为投射的以上特性,所以,不难发现,投射的世界其实和真相无关。而投射所能带给当事人最大利益就是,我不需要为我自己负责任。我生气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对待我,我不能好好工作是因为坐在我身边的人老打电话影响我,我伤心是因为我说话总是没人听……总之,我们的不幸都是由外面造成的,这个外面可能是你的家人,同事,老板,朋友或者市场卖菜的大妈,也可能是政府,是社会,是疯狂的世界,再往前推一步就是自己的命不好,运气不好。
就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像一个功能强大的投影仪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忙着将自己内心的负疚和不安投射到别人的身上,极少有人能够面对真相。想像一下,当整个世界都在忙着相互投射的时候,这是一场多么大的幻灯秀啊,难怪佛学中说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梦幻泡影”。但是,我们却深谙此道,我们总是目光如电,一下子就能看出别人的错来,而且总是能够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而这些常常被我们自认为是很有思想,很有品味,对生活或者对工作有很严格的要求。
还有一种投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与归咎于他人无关,而是恰恰相反,它会将对方无限地美化甚至神化。想一想,我们青少年时期对于某个偶像的崇拜吧,在他们的身上有着多少令我们心驰神往的特质啊;还有,当我们开始爱上某一个人的时候,哇,对方简直完美无缺,让我们惊为天人;如今,我们长大一点了,那些小儿科的东西我们不玩了,我们要心灵成长,于是,我们的投射就转移到某个大师,某个师父的身上,他身上一定有着我们没有的东西……看起来,完全没有归咎于人的不负责任,相反,我们看起来如此虔诚而谦虚。但是,只要你再稍微往下探索,你就会发现那个自惭形秽,那下面藏着一些巨大的黑洞的,那就是“我不够好”,于是,我们把那个理想中的足够好的自己投射出去,无论他是一个明星,恋人,还是师父。
投射的另一个副作用是,它不断地强化了好坏、对错、是非、自他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因为必须要有一个投射者和被投射的对象,哪怕这个被投射的对象是自己,那也是因为你内在存在分裂与矛盾,你的“超我”(即内化的母亲)对你内在恐慌孩童进行着监督和批判。因此,要想修成“无分别心”,不觉察我们内在的投射是不可能的。
觉察到我们长期以来累积的“投射”的心理模式,并收回它,学习对我们的思想、情绪及行为负完全的责任。我的办法是,当我觉察到内在的批判升起的时候(无论这个批判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的),我首先是看到它,允许它,并对自己以及被投射者进行宽恕,给它们爱。有时候我也许会更深地探究一下深层次的原因,有时候我只是直接宽恕,总之,效果非常神奇,那个批判以及由此而升起的自责很快就化解了。
慈悲与真相
真正的慈悲不是让人们减轻一时的身体或心理的痛苦,而是要让人觉醒于实相,要解决人类最根本的痛苦——灵性之苦。
有朋友问我要如何看待患白血病的儿童。我想,他的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有关什么是慈悲。
关于慈悲,我们有太多的误解。首先,我们常常把慈悲与同情混淆。奥修说的更极端,他说“同情”是把别人看作低人一等的,而自己是高人一等的,我同意他的说法,在最深的层次,同情确实是含有这样一层心理因素。但是,我仍然不怀疑有些富有同情心的人的爱心。
阿玛斯在《钻石途径》中说,“人们通常会把慈悲视为减轻别人痛苦的一份欲望,或是把慈悲体认成一份助人的欲望。当我们看到别人受伤时,我们往往会生起慈悲心。如果别人不感觉痛苦,我们很少会感到同情,因此,我们通常会把慈悲、痛苦和受伤联想到一块儿。然而,这只是慈悲最初阶的层次,一种情绪上的同情。”
如果,你总是陷于同情别人的眼泪或悲伤中,你要学会的是去向内看,是什么让你陷入其中,不要只回答说:“同情啊!”,而是要透过这一层再往里看。终于在某一刻你会发现,如果在你的内心没有怕受伤怕受害,或者说曾经受苦受伤的伤痛在,你看到某人很痛苦,你的内在并不会痛苦。你可能会很真心的想要帮助他,但你的内在却是平静的,无染的。你可能帮助他,但你不会期望对方记住你的帮助,连一丝一毫这样的念头都没有。那个帮助就会变成不是发自同情的,而是发自慈悲的。同情有一份执著的热度(也就是我们说的激情),而慈悲是客观的,是有点冷的。而且,慈悲的作用并不一定是减轻痛苦(包括身体的痛苦与心理的痛苦),有时候它可能会让你更深的进入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