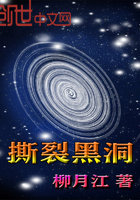(二)我们的出发点还是“镶嵌在活的东西上面的机械的东西”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滑稽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活的身体僵化成了机器。在我们看来,活的身体应该是充分灵活的,应该是那工作不已的本体的永远清醒的活动。然而这种活动与其说是属于身体的,毋宁说是属于心灵的活动。它应该是一个更高的本体在我们心中点燃的,由于透明而能在体外窥见的那个生命的火焰。当我们在这个活的身体上只看到优美和灵活时,那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在这个身体上还有笨重凝滞,总之是物质的东西。我们忘了身体的物质性,只想到它的活力,而我们的想象力也把这个活力归功于精神和智力生活的本体。然而假设我们把注意力放到身体的物质性上,假设身体不具有给它注入生命的那个本体的轻盈性质,而在我们心目中只不过是一块沉重可厌的覆盖物,一个把那迫不及待地想离开人间的灵魂羁绊起来的皮囊,那么,身体与精神的关系就将和前面所说的衣服与身体的关系一样,它就将成为叠置在生动的活力之上的毫无生气的一团物质了。一旦我们清楚地感觉到这种叠置,滑稽感马上就会产生。特别是当我们看到精神受到身体的需要愚弄的时候,这种叠置关系就更清楚了——一方面是具有多种多样的智能的精神人格,另一方面是以机械的固执性来干预并阻挠一切的单调而笨拙的身体。身体的要求越是琐碎,越是周期地反复,滑稽效果也就越显著。然而这不过是个程度的问题,而这些现象的一般规律可以表述如下:凡与精神有关而结果却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人的身体上去的事情都是滑稽的。
一个演说家,正当说到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忽然打了一个喷嚏,为什么我们就要笑他?有一位德国哲学家引用别人在悼词中所说的“死者德高望重,身体肥硕”这句话,滑稽在什么地方?那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忽然从精神方面转到身体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如果你不愿费神去收集,只消把拉毕史的作品随便翻翻就行了。你随时都会看到诸如此类的效果。这里是一个演说家,说到最紧要的关头忽然牙痛发作;那里是一个人,每次说话总要停下来抱怨鞋子太紧了,裤带勒着肚子等等。这些例子暗示我们的形象都是为身体所困扰的人。肥胖过度的人之所以可笑,显然是因为他唤起我们这样的形象。有时腼腆也有些可笑,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别人眼里,腼腆的人仿佛是被身体所困扰,想在身边找个地方把身体存放起来似的。
因此之故,悲剧作家总是小心避免任何足以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主人公的物质方面的东西。一旦引入了对身体方面的关注,那么滑稽因素就有渗入的可能。所以悲剧的主人公不吃不喝,也不烤火。如果可能,他们甚至也不坐下来。正在念着台词之际坐下来,就会提醒观众,使他们意识到主人公有个身体。拿破仑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位心理学家,他就曾注意到,单是坐下来这么一个事实,就足以把悲剧转成喜剧。在古尔哥男爵的《未发表的日记》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说的是在耶拿之战后,拿破仑和普鲁士王后的一次谈话。拿破仑这样说:“她跟希梅娜那样,以悲剧中的口吻对我说:‘陛下,要公道!要公道!马格德堡!’她继续用这使我十分困恼的口吻说话。后来,为了使她换个语调,我就请她坐下来。要打断一个悲剧性的场面,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因为你一坐下来,那就成了喜剧了。”
现在让我们把身体支配精神这个形象扩大一下,我们就将得到更普遍的东西:形式想支配实质,文字和精神抬杠。当喜剧取笑某一职业时,它不正是设法把这种观念暗示给我们吗?喜剧让律师、法官、医生说话的时候,仿佛健康和司法没有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要有医生、律师和法官,重要的是职业的外部形式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这样,手段代替了目的,形式代替了实质,不是为了公众才有某一职业,而是为了某一职业才有公众了。对形式的经常关注,对规则的机械运用,在这里就产生了一种职业性的机械动作。
这种职业性的机械动作可以与身体的习惯强加于精神的那种机械动作相比拟,也和它同样可笑。戏剧当中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现在我们不去深入研究这个从主题发展出来的变奏曲的细节,且引用两三段文字,在那里面,这个主题本身表现得非常简单明了。《无病呻吟》里的贾法如说:“我们给人治病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医生的爱情》里的巴希斯说:“与其违反规则而病愈,不如遵照规则而死去。”在同一出喜剧里,戴丰南德雷斯也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总得遵照一定的手续。”他的同行托梅斯点出这句话的道理:“死一个人不过是死一个人罢了,然而要是忽略一道手续,那就给全体医生的名誉带来莫大的损害。”比利多阿生的话虽然涵义稍有不同,但同样意味深长:“形——形式,您明白吗?形——形式!有人嘲笑穿常服的法官,但是,看——看见了穿袍子的检察官就会发抖。形——形式,形——形式呀!”
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研究下去,有一条规律就越来越明显了。现在我们先来举个实例。当音乐家在一件乐器上奏出一个音,其他一些音也就自动跟着来了。这些音没有那个音响亮,但和它保持一定的关系。它们丰富这个音,使它具有一定的音品。在物理学上,这些音叫做基音的陪音。滑稽味,即使在它最胆大的创造当中,难道不是遵照类似的规律吗?譬如说,让我们来看看“形式想支配实质”这一个滑稽音符吧。如果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音符就应该有下列这个陪音:身体捉弄精神,身体支配精神。因此,当喜剧诗人奏出了第一个音符,第二个音符就会本能地、不由自主地添上去。换句话说,喜剧诗人将以身体的可笨加强职业性的可笑。
当比利多阿生法官一面口吃一面上场的时候,难道他不正是通过口吃本身,让我们理解到他就要演示的那种思想的僵化吗?到底是什么秘密的关系能把这种身体的缺陷和精神的狭隘联系起来的呢?也许应该是这样一个原因:我们总觉得这个思维的机器同时也是一个语言的机器。不管怎样,反正没有任何其他陪音可以更好地充实这个基音的了。
当莫里哀在《医生的爱情》里让那两个可笑的大夫巴希斯和马克洛东上场的时候,他让一个讲话讲得很慢,一个一个音节抑扬顿挫地吐出来,而另一个却口吃得说不出话来。《浦尔叟雅克先生》中的两个律师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对比。通常总是把说话的节奏用来作为补充职业性的可笑的身体上特点的手段。当剧作家没有指出这样的缺陷的时候,演员也必然会出于本能地添上去的。
因此,在我们进行比较的两个形象(以某些形式固定下来的精神以及由于某些缺陷而僵化的身体)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也自然能被我们认出的联系。当我们的注意力无论是从实质转到形式,还是从精神转到身体,在那两种情况中,传到我们的想象当中去的都是同一个印象;在那两种情况中,都是同一类型的滑稽。在这里,我们也还是试图忠实地遵循想象活动的一个自然方向。我们记得,这个方向是从中心形象出发而呈现出来的第二个方向。现在我们就要踏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最后一条道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