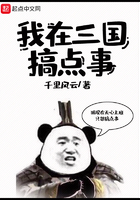(也称豳公、燹公。“”是用来盛黍稷的礼器,从簋变化而来,西周中期偏晚的时候开始流行。据李学勤的释读,铭文内容为:“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沫唯德,民好明德,寡顾在天下。用厥邵绍好,益干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讦明经齐,好祀无。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铭“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可对照《尚书》中的《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还可对照《尚书序》:“禹别九州岛,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众所周知,关于《禹贡》这篇文字,近世学者多认为是晚近之作,《尚书序》更是被人怀疑。现在证明,其文句与铭铭文相符,特别是“随山浚川”一句,与《尚书序》一字不差。
一般认为,大禹治水,采用疏川导滞的办法,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终于制伏了洪水;而他的父亲鲧,采取堵塞的方法,治水九年而无成,被舜殛于羽山以死。其实,大禹治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两大因素:一是大禹获得了“中”,二是气候好转。
先说大禹获得了“中”。何谓“中”?这得从《保训》谈起。
(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被称为清华简。2008年10月14日,清华大学邀请李伯谦、裘锡圭等11位专家对这批竹简进行观察鉴定,专家一致认为,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2009年4月,清华大学公布:周文王临终遗言《保训》面世。这是一批战国中期偏晚的竹简,被称为“清华简”。《光明日报》2009年4月27日刊文称:“清华简目前发现的一些内容珍秘,在历史上久已失传,堪称惊人。当天,清华大学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由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担任中心主任。”
李学勤等学者从这批简牍中整理出来的第一篇简书,即是《保训》,它是周文王临终前对武王的遗训;原文并无篇名,李学勤等学者命名为“保训”。
《保训》简文如下:
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历,恐坠宝训。戊子,自靧。己丑,昧爽……王若曰:“发,昔前夗传宝,必受之以。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隆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昔微矵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传贻子孙,至于成汤。”曰:“不足,惟宿不羕。”
这个“训”讲述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是“昔前夗传宝,必受之以”。它是说从前前夗传宝训,必定把传下去。这是文王为自己传宝训提供历史依据,显示他是效法先贤所为。第二个故事说的是舜“求中”和“得中”。“舜亲耕于鬲茅”,由“郭店简”(即1993年10月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一处墓地中发现的一批竹简,学术界称之为“郭店楚墓竹简”,简称“郭店简”)之《穷达以时》的“舜耕于鬲山,陶拍于河浦,立而为天子”,以及“上博简”(即上海博物馆1994年从香港购回的一批竹简,共1200余枚,均为战国竹简,内容涉及儒家、道家、兵家以及杂家等,共八十种古籍)之《子羔》的“尧之取舜也,从诸草茅之中,与之言礼”,可知,“鬲”指鬲山,即历山。“鬲茅”,是说历山之荒野。当时,舜求“中”而得“中”之后,“帝尧嘉之,用受厥绪”。第三个故事讲的是上甲微“矵中于河”,又“追中于河”,阐明了求“中”、得“中”、保“中”与“践天子位”的关系。
这里的关键词为“中”。“昔微矵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由此可见,这个“中”至关重要,借了它,就能消灭有易。而为什么还给了“河”?显然,因为“中”是保存在“河”那里的。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中”,恐非李学勤等学者所谓的“中道”,而是一种器具。“中”的甲骨文写法包括:。王国维在《释史》《观堂集林》卷六12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考证认为,“中”是一种器物。
我赞同王国维的观点。“中”与“鼎”大致相若,或者二者就是一回事。当时的“中”,是刊载河图、洛书(与而今所见的河图洛书不是一回事)等重要内容的器物(当时,最重要的东西,一般刻录在坚固的器物上)。“中”由“河”保管,“河”就是“河伯”,专管水利整治。(也有观点认为,河伯为氏族名,是由于这个氏族居住在河水附近并且擅长于行船或者治河而得名。)
什么是河图、洛书?南宋人薛季宣的《河图洛书辨》中推测“洛书”是古地图,“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这是正确的看法。
地图在与洪涝灾害和军事的抗争中的意义,不言而喻。《史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可见,治水很重要,而河图、洛书更显得重要。
黄帝之时,就有河图洛书。《水经注》载,“黄帝东巡过洛,修坛沉壁,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字。”当然,这里有演绎的成分,其实,黄帝时期,河图洛书已经形成,并归于河伯保管。
此后,掌握了河图洛书,就意味着掌握大统。从“清华简”的周文王临终遗言可见。当然,还有旁证。《论语?尧曰》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就是说,允许舜执“中”,舜才算是名正言顺的“帝”。
大禹治水,也曾多年无功。后来,如《尚书》所称,“天乃赐禹洪范九畴”,使他取得成功。所谓“洪范”,使“洪”就“范”的,不就是河图洛书吗?汉代孔安国也曾说:“天癸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第之,以成九类常道。”
再说气候好转。
前文说过,据历史文献记载,鲧采用“堙障”法,修筑堤坝围堵洪水,而大禹成功治理洪水的关键是采取疏导的方法。但以当时人们的知识水平和物质条件(主要以木石为工具),无论是鲧的“堙障”还是禹的“疏导”方法都不可能治理好洪水。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屈原就提出了类似的疑问。他在《天问》中问道:“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大致意思是说:浩荡的洪水,大禹是怎样把它制服的呢……鲧是如何治理的(为什么没有成功),禹为什么能够治理成功?这些质疑耐人寻味,表明屈原也十分怀疑大禹和他的臣民有这么大的能耐来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
既往的传说将鲧治水的失败归结于“壅防”,而将禹治水成功归结于“疏”、“导”。可是,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人们管理和控制洪水主要是筑堤建坝,而不是疏导。黄河流域的洪水灾害即使是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水平也很难控制;何况,疏通九川,开辟九州是非人力所及的功业,因此很难相信在几千年前的大禹能够通过疏导的治理方法完成他的丰功伟绩。
那么,如何解释大禹实现了这种“不可能”的事呢?
地质学者与气象学者的研究表明,气候异常事件的结束时间,亦即气候好转的开始阶段,即传说中大禹成功治理洪水的开始。二者在发生时间上的一致性表明大禹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制服洪水可能也得益于气候的好转。
一般认为从暖期向冷期的气候转变往往是相对缓慢、逐渐的,而从冷期向暖期的转变则是快速的、突变的,如格陵兰冰芯氧同位素记录的气温变化表明,在新仙女木事件(按:距今12800年前后,温度在数百年内突然下降6℃,使气候回到冰期环境。此强变冷事件以丹麦哥本哈根北部黏土层中发现的八瓣仙女木花粉命名)后的快速转暖过程中,气温在短短的20年左右中上升了6℃~7℃。
气候好转,使得气候带北移,季风降雨正常化,植被恢复。洪灾自然随着气候的好转而好转。这时,禹利用手中的“中”,采用疏导的办法,使处于尾声的大洪水,相对较为容易地被治理了。但是,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人们可能并不知道气候突变与洪水灾害之间的关系;相反由于饱受洪水灾害,人们可能更注重结果。大禹当时领导他们治水,将功劳归功于他合情合理。
而今,我们或许对“治水”的重大意义缺乏了解。在古代社会,治水可是核心命题之一。君不见,秦始皇统一各国之后,碣石颂扬秦德,自称“决通川防”,改黄河名为“德水”,更称秦为“水德之始”。直到清朝,尚书慕天颜还说“水治则国治”。
这背后的道理并不复杂。当时是农业社会,耕作技术较低,人们只能望天打卦、靠天吃饭。一旦天公不作美,持续干旱,或者洪水泛滥,农田或许要绝收。一旦采取治水措施,兴修水利,则干旱之时可以引水灌溉;洪涝之时,可用水利设施避害。于是,治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而农业也是当时经济实力的表现。
而且,治水,在当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整合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一过程,恰是导致古代国家产生的重要因素。德国的罗曼?赫尔佐科(RomanHerzog)称:为引水和治水而进行的斗争,与防卫等同等重要,是国家产生的目的。《古代的国家:起源于统治形式》第9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掌握了整合人力、物力资源的机会,并逐步掌控了权力的核心,“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有一件重大的事情,不容忽略:“定九州”。《史记》云:“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也就是说,禹并非仅仅治水,同时是在划分疆土(禹敷土),树立界牌(随山刊木);是在山区和丘陵间整修山路(披九山),在湖泊和河流中开通航道(通九泽,决九河);是在顺应九山、九泽、九河等高山大川的走向,将广大的领土划定为九个行政区域(定九州);以求由此来规范和促进各地行政首长的朝贡职责(各以其职来贡)。
禹在位期间,还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如“禹攻有启”、“禹伐共工”、“禹征有苗”等。据说,禹在讨伐有苗前杀气腾腾地宣布:“济济有众,咸听联言,非唯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即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通过战争,禹“声教讫于四海”,权势日隆。
当然,禹并没有直接取消禅让制,而是“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但是不久,“皋陶卒”。接着,禹又宣布将首领位置传给东夷族的益,但是他让自己的儿子启“为吏”,使其家族势力日益增长,逐渐取代了部落联盟议事会。禹去世之后,启已经羽翼丰满,“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此时,启“与友党攻益而夺天下”,终于夺取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而且连禹时期的“国号曰夏后”也沿袭下来。“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对此,《战国策》一语中的:“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夏朝建立之后,开始设官分职,制定法律。朝廷官吏主要由负责处理日常政务的外廷官和负责夏王日常生活事务的内廷官所组成;而地方官僚机构,即为各受封的侯、伯及其政权。地方侯、伯一部分是夏禹取得联盟首领的职位后,由其子孙所建立的诸宗族的方国,另一部分则是承认夏王的共主地位,受夏王之命,并对中央王朝尽一定义务的异姓宗族的方国,其中如《帝王世纪》所说的“皋陶卒,葬之于六。禹封其少子于六,以奉其祀”;《史记?五帝本纪》所说的“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这种形态,是后世王朝分封同姓与异姓贵族制度的滥觞。
这样,夏朝——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产生了。被称为“国家”,它须具备相应的治理机构与治理机制。一个组织被称为“国家”,那么,它须拥有行政、司法、军队以及相应的制度等。由此可见,舜之时,已具备“国家”的雏形,设有总揽百官及庶政的四岳;有专业分工的行政组织:工程营造——禹;农事生产——弃;人民教化——契;掌理刑罚——皋陶。
在行政上,夏朝有行政机构和职官。夏王朝建立之后,也同时建立了相应的政权机构。职官制度是国家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夏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后”。《史记?夏本纪》曰:夏“国号曰夏后,姓姒氏”。禹、启又分别称为夏后禹、夏后启。夏朝的官员称为“正”。夏朝有“车正”。如《左传?定公元年》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夏少康曾为有仍氏(今山东济宁市及微山县西北和金乡县东北一带)“牧正”,为有虞氏(今河南虞城县一带)“庖正”。有仍氏、有虞氏皆夏王朝的同盟小方国,既有牧正、庖正的长官,夏王朝亦应有此官职。
在司法上,夏有刑罚、监狱等。《左传?昭公六年》云:“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的内容已不得而知,但夏朝国家肯定是有刑罚的。夏后氏对所属的官长及民众有生杀之权,《国语·鲁语下》云:“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夏王朝已有监狱,如《史记?夏本纪》曰:(桀)“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夏台,《索隐》曰:“狱名,夏曰钧台。”又引皇甫谧云:“地在阳翟是也。”夏台,又名钧台,就是夏王朝的监狱,在今河南禹县境。禹县,古称阳翟。
在军事上,夏有军队。如《墨子?兼爱》记载,禹伐三苗时说:“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群,指广大士卒。由此可知,夏王朝及所属封君都有自己的军队,作为“万国”之君的夏后氏,其军队的规模亦当是可观的。依靠这支军队,夏禹死后,启与有扈氏在甘之战中,敢于“恭行天之罚”、“剿绝其命”,并且打败了有扈氏。正是依靠军队的力量,夏王朝的传子制度最终确立了,夏后启的统治也得以确立。
土地制度具体化
如果说黄帝以来,部落的土地分配制度有所萌芽,那么,大禹时代,土地制度便具体化了。大禹在掌握统治权之后,除了军队、司法、行政机构等之外,也开始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制度,其中就包括土地制度,即“任土作贡”。明末清初的顾炎武(1613—1682)说:“古来田赋之制,实施行于禹。”
大禹时期的土地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土地清丈。禹设置了名为“太常”的负责绘制人文地理图、丈量划分田地的官员。实施“敷土,随山刊土,奠高山大川”,即进行丈量国土工作,沿着山脉进行测量,竖木为标志。
(2)“公地”(公田)、“私地”(私田)并存,且采用劳役式地租。《孟子?滕文公》说:“夏后五十而贡。”史称大禹为夏后。看来,夏代的农夫可能在耕种自己的五十亩“私地”外,还要耕种五亩“公地”,即如东汉赵岐《孟子注》所说“民耕五十亩,贡上五亩”。这种年纳五亩之获,作为“贡”的实际内容,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劳役地租”。此时的“地租”,耕者均等负担,土地也相应地平均分配。“私地”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私有”,只是一种准私有产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租用权,因为它不能买卖。
(3)对土地实行分等定级。“贡”,其实是建立在土地分等定级基础之上的。禹实施“任土作贡”,对九州土地进行分类,将全国土壤分为壤、坟、卢、涂泥、黎、斥卤等类。《尚书?禹贡》记录了将九州土地分为三等,每等又分为三个级别,并相应分为九个等级的地赋。
当然,夏朝并无“封建制度”,尽管后人说当时有“五服制度”。《尚书?夏书?禹贡》云,“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这一说法完全被《史记?夏本纪》采纳。
由上述记载可见,只有“甸服”,也就是王畿之地,才有贡赋关系。甸服之内明言“纳”贡,且纳贡内容十分具体,或许的确是一种地方向中央缴纳贡物的纳贡制度。侯服及以外诸服,不言“纳”字,明显与甸服不同,说明不存在周代的那种分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