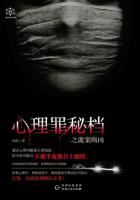这一句话,让我看到了白兰的心,她的心里,有与我一样的柔情,但是迫于一个女孩子的羞涩和内敛,她极力地隐藏住了。不经意的那一句,其实于她,已是鼓足了勇气。而自私的我,却是不敢去碰触一点一滴的真情,任凭它们溢出来,浸湿我飞快逃脱的脚。
终于熬到可以去陈慕的公司实习的机会,那时的陈慕,已是公司一个业绩出色的负责人。有了他作为支持,我对留在这家公司的信心,增强了许多倍。但陈慕还是一再对我强调,一定要自己努力,否则即便是他再怎么给老总说好话,也是徒劳。公司靠的是业绩,而不是关系。我并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凭我对陈慕的帮助,他一定会在老总那里力荐我,只要我稍稍努力,就一定可以把同来实习的几个人打败的吧?
我很用心地将公司的所有客户都记下来,工作以外的空闲里,我会时不时地约一些重要的客户出来吃饭闲聊,通过他们的介绍,我也有了自己的客户;而且,更让我欣喜的是,这些重要客户,在签约的时候,总是点名我去,将原来的公司成员,给抛在一边弃之不用。起初陈慕还会提醒我,最好不要抢公司同事的客户,虽然同事之间有竞争,但道德还是要讲。我有些不解,想是这些客户来找我的,怎么能算是抢呢,这顶多算是公平竞争吧。陈慕对我的辩解,不置一词,但是脸上,却有了淡淡的不悦。我并没有把他的变化,放在眼里,那时我的业绩成绩,已是直线上升,老总甚至有一次还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里,发了红包给我。我几乎坚信,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将我挤出去。
毕业的时候,公司公布最终留下来的人员名单。很奇怪地,没有业绩名列第一的我。我发了疯地去找老总,问他为什么?!老总抬头淡淡地看我一眼,说:“做每一件事,能够问心无愧才是最好的成绩,这样的结果,你其实应该问的是你自己。”
这样的话,陈慕其实早就对我讲过,只是我在不顾一切地往前冲里,给忽略掉了。临走的时候,有个一块实习的人悄悄过来,说:不让你留下来,其实是陈慕在老总面前极力要求的。我已经没了任何的冲动去找陈慕,因为我听说,白兰回了自己的家乡,任凭陈慕怎么挽留,都不肯留下。那么陈慕,当然也不会将我留下。
当我凭借自己的实力,终于在另一家公司找到更好的工作时,陈慕发短信来祝贺。他说,其实你一直都可以凭借着自己来得到一切的。工作如此,爱情亦是。我给我你机会,可是却都被你给放弃了。甚至是那么爱你也被你爱着的白兰,你也给错过了。幸好,你还没有放弃希望,所以才有今天的工作……
我没有看完,就已是泪流满面。其实陈慕怎么知道,不只是他给过我机会,那么羞涩的白兰,在毕业的时候,都发短信问我:肯不肯跟她走?一心只想着工作的我,竟是漠漠然地,没有回复她一个字。一份绽放的友情,和一份含苞的爱情,青春里最值得我用力挽留住的东西,就这样无情地与我擦肩而过。
杀死一只逃命蟑螂
玄月打开卫生间的门,又摸索着开了灯,迷蒙中看到马桶里那滩鲜红刺眼的血,即刻被恐惧袭击了全身。尖叫之中,她听见有人紧贴着她的后背压低了嗓门阴笑道,你逃不掉的。
她果然没有逃掉,当即在那片红色面前,晕死过去。
玄月在来这所租住的公寓之前,李朗就几次三番地阻止过她,最好还是别去这所新开发的小区,听说房地产商在买卖交易房子的时候,曾经因为一个住户毁约而发生过纠葛,住户不满地产商与宣传严重不符的房子,但又因为合约而要交一笔不菲的违约金,于是便在网上发泄忿恨,四处发帖,号召同买了房子的白领们都联手放弃。那一阵子房价大跌,地产商们急红了眼,便警告住户不要放肆,住户置之不理,但没过一段时间,便发生了奇怪的事情。那个闹事的住户,很快地得了怪病,全身皮肤发红,瘙痒,而且这痒据说是在内里,有想要割开肉去抓挠的痛苦。不过是一个月,住户便奇怪地死掉。而此后小区里的住户,每在月圆之夜,便会听到有人在楼下的竹林里嘤嘤地哭泣,像个被丢弃的婴儿,又像寻不到身体依附投胎的女鬼。
李朗这样讲述的时候,用了极夸张的语气,听起来好像电台里那个讲鬼故事的张震,直让玄月听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但玄月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她从小就生长在乡下的姥姥家,习惯了撒开腿在有月亮或者没月亮的野地里跑,所以等她来到城市,在喧嚣中更没有什么可以惧怕。况且,有李朗在,她更不用怕了。所以她听后不过是片刻,便刮刮李朗的鼻子,说,哼,我偏向虎山行,看看这个小区究竟多么可怕,再说了,这么便宜的房子,又这么好的地理位置,离我上班公司也近;即便是有鬼,像我这样地震都震不醒的睡死鬼,绝对能将那鬼魂气死。
所以当玄月风风火火地收拾房子,而李朗却找了借口公司有事不来帮忙时,玄月也只是生了一阵子闷气,便又被那乔迁之喜,给鼓舞地欢欣忙碌起来。
玄月在搬到新房的当天晚上,因为疲惫,也因为好奇,特意早早地熄了灯,而后躺在房东留下来的老式雕花床上,倾听周围的声音。
她先听到的是楼下有人经过的脚步声,很轻,很慢,应该是一个女人,但没有穿高跟鞋,或许是晚间睡不着觉,于是带了自己的猫,在楼下的小花园里散步。间或也有人骑车,叮铃铃地经过。更远的地方,是这个城市还没有完全消解掉的燥热与喧嚣。但这样的热闹,因为小区重重的树木隔着,便显得渺茫,像是高楼上的歌声,更显出周围的寂静。
屋内则是悄无声息,玄月只听得见自己均匀的呼吸声,还有水在管道里沿壁缓慢下滑的声音。玄月侧耳听着那楼下的脚步声有些淡了,而后她又听见楼下的门,哐当一声,那重重一摔里,明显是带着怨气的。
但玄月还是很快地睡了过去,直到她半夜里被冻醒,昏沉中去橱柜里翻找带来的毛毯,却不小心将什么东西打翻在地,随后便是玻璃碎掉的声音。玄月想打开灯,却是忘了灯开关所在的位置,这样摸摸索索地,便摸到一个软软的东西,借着窗外路灯射进来的微弱的光,玄月随即“啊”一声尖叫,将手中的“软组织”疯狂甩开去,又连滚带爬地钻进了被窝。
玄月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将屋子照得如一件通体透明的玉器。玄月看着地上被打碎的幸运星瓶子,还有一只已经僵死的蟑螂,这才想起昨晚的事情。看着乱糟糟等待收拾的房间,她忽然觉得一阵孤单,于是便拿出手机要打电话给李朗。可是一连拨打了几次,都没有回应。
玄月有些失望,又拨打了一次,却是没有靠在耳边,而是将之丢在地板上,开始收拾东西。等她想起来的时候,手机里已经有了人声,说,呀,窗帘怎么坏了个洞?
但却是一个娇媚的女人的声音,而且,很快便被挂断了。
玄月再打,却是再也没有接通。
玄月探出头去,看见同一个单元里有个女人出来,趿拉着拖鞋,将一大袋垃圾丢进路边的垃圾桶里,然后便拐个弯,不见了踪影。大约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女人的脚步声再一次响起,玄月看见女人恰好经过自己的窗下,而且,也恰好抬头,朝上看过来,只不过,她看的大约是楼下的位置。
那个女人噘着红嘟嘟的唇,遥遥送了一个飞吻,然后便进了楼门。
玄月的孤单,在这样她也曾经熟悉的幸福里,愈加地深且黯了。
玄月在将小小的房子打扮得如新房般温馨甜蜜后,便给李朗发了短信,让他过来庆贺。李朗起初有些支吾,说公司这一段时间的确很忙,抽不开身过去,况且,他对路线又不熟悉。玄月当即撒娇,说,那我去接你好啦。李朗这才叹口气,说,那好吧,你不用过来了,那么麻烦,给我个路线图,我自己可以摸索着过去。
李朗抵达玄月小区门口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见他进来,门卫狐疑地看他一眼。玄月想要解释,李朗却略略紧张地拉她快些走。玄月噘嘴,说,要不是小偷,干吗怕他?李朗回头悄悄看那门卫一眼,说,我不是小偷,但你也抵不住别人将你当小偷看。
玄月便笑,说,那他会将你当成偷什么的?至多,是偷人吧。
玄月嘻笑着将唇凑过去,李朗却以一句“没刷牙”,躲开去了。玄月借着路灯,看见李朗的脸,有些微微的红。
玄月随即揶揄他一句:偷人不是一次了,干吗还红脸,让那门卫看了,还以为你真的偷了别的女人呢。
李朗拿话岔开她:有没有准备热水,我有些疲累,想要泡澡。
玄月啪一下给他一个响亮的吻:那还用说,浴池正好可以盛下你和我呢。
玄月在浴池里洒了许多花瓣,是她从花市上专门买来,要和李朗洗浴用的。
但向来喜欢与她共浴的李朗,这次却有些烦乱地拒绝了她。理由,是他有些头疼。
玄月坐在客厅里,听着浴室里哗哗的水声,有些心烦意乱。她走到窗口,朝下望去,又看到那个趿拉着拖鞋的女人,将一袋子垃圾扔到筒中,同时开始拨打手机。
玄月还想继续看下去,却听见李朗的西装口袋里,手机响了。玄月走过去,拿出来,很自觉地走向卫生间,还没有敲门,就见李朗一脸紧张地开了门,将手机几乎是抢了过去。玄月从来不会主动地去翻看李朗的手机,但她还是无意中瞥见了那个打来电话的人,名为伊拉。
玄月自觉地将门关上,继续走到窗口,她看见那个女人正坐在不远处的木椅上,说着什么。似乎是愠怒了,还听得见隐隐的哭声。但也就是片刻,她便将手机啪一下扔到草坪上去。是她扶着腰身起来的时候,玄月才发现,这个女人的腹部,原来已经显出了淡淡的“孕味”。
玄月还想继续看下去,却被悄无声息潜到身后来的李朗,一把抱住,而后朝卧室走去。玄月兴奋的尖叫着,想要挣扎,却被李朗抱得愈发得紧。
玄月在不久之后,才发现了夜晚总是有东西在悉悉索索响动的原因。竟是一群生活得自由自在的蟑螂惹的祸。
那群蟑螂,寄居在洗手间里,还在水笼头后面的小孔里悠哉穿梭。玄月想知道,是不是水管管道里也有蟑螂在任意爬行,于是她好奇地拿一个铁棍敲了敲管道,一阵当当的声音响过之后,玄月随即又听到相同的一阵当当声。
这声音是从楼下传上来的,而且像是作对般,玄月每敲一下,楼下也便符合着回敲一下。有点警告的意思。
玄月笑了,想这楼下的人,也必定是像她一样,周末闲得不知该做什么。这一点她跟李朗总是矛盾重重。李朗也来自于贫寒的家庭,大学毕业后一心想着挣钱,在同学家人亲戚面前挣足面子,而后带她荣归故里。但可惜总是一路不顺,事业上始终不温不火。想要跳槽,却又没有魄力,担心会连现在的这份薪水也保不住。玄月总告诉他,她不需要他这样辛苦,只要能够租房住,她也愿意与他白头到老。李朗却是讨厌她这样说,觉得是在讽刺于他。他还让玄月周末利用公司资源加班多接些私活,这样他也不用如此辛苦,为在这个城市有一个自己的房子而拼命工作。
玄月并不怎么听李朗的话,照例拿着那一份做文员的小薪水,悠然自得。就像现在,她宁肯自己下楼去扔一袋垃圾,也不想听从李朗的意见,在网上帮他联系客户一样。
玄月提着一袋子垃圾,走到楼下门口的时候,门突然开了。玄月在窗口看到的那个女人提着一袋子垃圾,也恰好要下楼去。玄月看她挺着的肚子,动了怜悯之心,笑道:恰好顺路,我帮你提下去吧。
女人并没有现出多少的感激,她的手机又恰好响了,于是便连一声谢谢也没有,就转身进了房间。玄月站在门口稍稍郁闷了一阵,她听见房间里女人接了电话,不知那边是不是信号不好,女人很大声地重复了一句:喂,我是拉拉,你是哪位?
垃圾桶有些满,玄月将女人的那袋放进去的时候,有些东西便溢了出来。幸亏是些废纸,玄月便弯腰用手去捡。
这一低头捡起,玄月便有些吃惊。那纸条上的字迹,竟然与李朗的,几乎是一模一样。那上面写着:拉拉,我这几天不来了,你照顾好自己和孩子,记得醒来喝我煲好的乌鸡汤。另,我已经新建了一个帐户,他打来的那笔钱,我已经转入其中,我很快可以买到一套好的房子,将你和孩子接过去。
玄月看得心内发凉,她下意识的一抬头,看到对面的窗户上,那个叫拉拉的女人,正冷漠地盯视着她。
玄月将纸条攥在手心里,一低头,走出了女人的视线。
之后的一连几天,玄月都翻来覆去地睡不好觉。
公司的工作也进入了繁忙期,她更是需要加班加点的才能在苛刻的上司面前勉强应付。玄月本来身体就不好,这样忙碌又失眠,让她有些神色恍惚,晚上闭上眼睛,总觉得有许多骇人的蟑螂在床上爬来爬去。
她于是打电话给李朗,却总是无人接听。玄月知道李朗习惯在做事的时候,将手机调成静音,但她还是心里一阵接一阵的失落与惶恐,似乎,李朗正在离她愈发地远,远到她根本寻不到他。
也就是这天夜里,玄月去洗手间,打开灯,看到了那滩怪异惊骇的血,并“啊”一声划破夜空的尖叫,然后昏了过去。
她醒过来的时候,是在医院里,只不过,身边没有李朗,而是一个面无表情的医生。玄月问大夫,自己究竟是得了什么病。大夫冷冷答她,疲累和惊吓所致,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还有,你月经有些失调,自己多注意一些。
玄月这才恍惚想起卫生间里的血,原是自己的经血,只是她已经50天没有来月经了,才忘记了这回事。
玄月想要打电话给李朗,却发现手机没在身边。于是她问大夫,送自己来的是不是一个高个子平头下巴有颗痣的男人?
大夫依然是冷淡:是你楼下的一个孕妇打的电话,我们去了救护车将你接来的,哪有什么男人?
停了片刻,大夫又说:倒是那个陪在孕妇身边的男人是高个子平头且下巴有颗痣。
玄月的心,瞬间跌落入冰窟去里。
玄月借助于小区的门卫,查到了楼下房间的电话。她打过去,是个男人的声音,与李朗有一模一样的低沉嗓音。
玄月自始自终,都没有吱声,任那个男人,在那端奇怪地又喂了几声,便挂断了。
出院之后,玄月便去找了李朗。她毫不费力地,在公司门口将李朗堵住。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将那张有他笔迹的纸条,递给了他,而后笑笑,说,李朗,你不用这样捉迷藏吧,楼上楼下的游戏,玩起来太累,不是吗?搞不好,那有钱大款的女人,某一天将你甩了,你是人财两空,哦,不对,是人财三空,还有一个没有出生的孩子;尽管,或许连你也不知道,那孩子究竟是不是你的。不过管他呢,有钱又有孩子,终归是好的。
玄月没有等到李朗的脸色青到发了霉,便笑笑走开了。
玄月想,她要很快地搬出去住,但在搬走之前,她一定会将那些蟑螂,全部消灭干净,省得让下任租房的住户,与她一样,晚上不能安睡。
每次看到蟑螂,就吓到面如土色的玄月,这次杀起来,不会下不了手。
她知道杀死一只逃命蟑螂,比掐灭一段过往,其实难不到哪儿去。
因为不舍,所以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