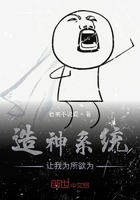最近,报上曾载美国正在试验之雷达炉,据说:煮鸡蛋七秒钟即熟,以纸裹包饺入之,三秒钟熟,而纸仍完好,科学诚科学矣!然而未必艺术,亦惟美国人能发明之,能利用之,何也?因其距吃的艺术之宫,尚有十万八千里途,此途又非飞机可达,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走也。然而高等华人,未必解此,据说他们已科学化了,早饭是白蒸猪肝和花旗桔子,如此的自卑自贱,还有何说?自然雷达炉子首先采用的,便是此等人了。
上面所举用温火之例,未免太贵族,其实家常菜之可贵,是不讲形式,不讲颜色,只考较香与味。比如作笋,如上面所说,馆派则难免加上一些二六芡,厨派则不用芡,但必须将其漂之至白,取其悦目,而味则无有,家常作之,乃有菜之真味。又如上面说的冬寒菜——川人以为胜于莼菜——馆派就根本不能作,若叫强勉作之,必仍油大味重,而菜未必熟。厨派作之过于精致,每每只摘取嫩苞,不惜好汤火腿口茉以煨之。好却好吃,然而绝吃不出冬寒菜之味,这就须家常作法了:连苞及嫩叶先以酱油炒之,加入米汤烹煮,不加锅盖,色自碧绿,若于沸之后,再加入生盐合度,菜既熟而微带脆意,无其它佐料,乃有清香,有真味。然而为其寒伧,只好主人自享,以为奉客,客则不悦,故为显客者,殊无此口福。不过已往士大夫之家常菜,重在精致刁巧,以求出奇争胜,故往往在大厨房之外,更有小厨房。主持小厨房者,多半为姨太太,或由太太训出之丫头,收用了为姨太太者,如西门大官人府上之孙雪娥焉。初不解为何必用姨太太,后闻人曰:凡雇用的厨子,每不可靠,学到了手艺,不是骄傲得忘其身份,就是动辄喜欢跳槽,或一跳就跳进了馆,而自立门户,于是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发太太,以地方色彩太浓,不必具论——已无姨太太制度,故此种封建风尚,不愁不连根拔去。得亏我们许多有识的太太们,尚未整个走出厨房,故家常菜仍得保留一部分,将来之变化如何,不可知。或许再进步后,此种古典派的艺术,便将成为历史的名词而已。
譬如为山,馆派是基层,厨派是中层,家常派则其峭拔之巅也。无论走到何处,要想得其地方风味,只到馆子中吃吃,未可也。能进而尝试一下私家厨味,庶乎齐变至鲁矣!除非你能设法吃到若干家的家常菜,而确乎出于主妇之手,或是主妇提调出来的,那才是鲁变至道,你才可以夸说登了山顶,不管风景如何,奇妙不奇妙,总之是山顶也。本此途往,便知中国菜到底算是何处好,何处更好,何处最好,何处绝好,殊不易言!何哉?以无此一人吃得遍全中国之馆、之厨、之家常,而又非常内行,起码也得像清道人之“狗吃星”一样也。无此种人,便不可表论中国菜,尤其不可作食谱;食谱或亦可作,但不可妄标科学方法,譬如说某菜煮若干分钟,今试问之:用何种火具?而火的温度,究在华氏或摄氏之若干度上?如不能表而出之,则所云科学者,只半吊子科学,亦只一知半解之高等华人信之耳。何况说到底,好的菜品,根本就不能太科学,例如利用外国机器切刀来切肉丁,你用最精密的尺子来量,几乎每颗肉丁,其六面俱相等,但是你炒熟来,却绝对没有用不科学的手,切出来的其大小并不十分一致样的肉丁好吃,何也?盖面积大小相等了,则其受热和吸收佐料的程度亦相等,在味觉上显出的只是整齐划一的一种激刺,而参差不齐的激刺,好不好吃分别在于此;馆派、厨派、家常派之差别,高低亦在于此。本此孤证,便知道一门艺术,真正说不上科学也。
成都人的好吃
中国人对于其它生活要素,由于顶顶重要的“自由”,大概都可模糊,有固然好,精粗美恶倒不十分计较,只要有哩,并不一定拼身心性命以求之。独于食,那便不同了,在川人中间,按照旧习,见面的第一句话,并非是“你过得怎样?”
“你好吗?”而是“你吃了饭没有?”或曰“吃过了没有?”而且在询问时,还带有时间性,在上午,问的是早饭;过午,须问午饭,四川语谓之“饷午”,读若“少午”;入暮则问晚饭,谓之“消夜”;其严格犹洋人之问早安、日安、晚安也。其它,凡与人相交接,团体与团体相交接,大至冠婚丧祭,小至邻里往返,庄严至于纳贡受降,游戏至于“撇烂”打平伙,甚至三五小儿聚而拌“姑姑艺儿”——黄晋龄的餐馆名,引用为“姑姑筵”,亦通——无一不有食之一字为其经纬。笔记载:以前漕河总督衙门,顶考较吃了,诸如吃活猴脑,吃生鹅掌,一席之肴,可以用猪八九头,每头只活生生的取肉一块,余皆弃之。
这种暴殄之处,姑不具论,甚至一席之肴,必须吃到三整天方毕,这真可以表现中国人好吃的整个性格,而且不吃不行。乡党中许多事故,大都由于不具食而起,谓人悭吝,辄曰:某人是不肯请客的,“要吃他么?除非钉狗虫!”言之痛切如此,甚至“破费一席酒,可解九世冤;吝惜九斗碗,结下终身怨。”可以说,中国人对于吃,几乎看得同性命一样重,这不但洋人不能理解,就是我们自己,亦何尝了解得许多!
枕江楼
节选自《大波》,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他当然不能推辞,只好说两句应该说的抱歉话,便一同朝着文庙前街,再沿上莲池边,插向南门走去。
枕江楼是前年重修南门大桥——一般叫做万里桥时,才趁热闹开张的一家小饭铺。地点选得还好,恰处在大桥上流的岸边,临着锦江江水,砌了一道短短的石堤。堤上简简单单地修了一排仅蔽风雨的瓦顶平房。平房尽头处,也就在石堤尖端,盖了一间圆形草亭。石堤得亏比大桥低,向下流头望去,靠岸第二孔石拱桥洞恰似它的大门。大门外景致甚好:天竺寺的后围墙,墙外临河小路,路边的大黄桷树,树脚下的石碛,石碛上面的水波,那么远法,看来真像画面。只是近处岸边一座积得山样的垃圾堆,成天都有一些穷妇女穷小孩蹲在上面刨渣滓,找东西,不免有点杀风景。毕竟因为地当桥洞,又在水流湍激之处,无论何时,好像总有一股凉风拂人,在天气热时,这地方的确是一个乘凉饮酒的雅座。而且上流头也是一大片鹅卵石坝,坝上河岸边一排斫折不死的老杨树,树下是个卖鱼虾的小码头,好吃嘴的客人每每亲自去买了鱼虾,烦厨房大师傅趁活做出来,非常好吃。这一切都合上了成都人的口味。于是它便从一个普通小饭铺摇身一变,变成一家馆厨派而兼家常味的、别具风格的中等南堂馆子。座头幽雅,又有天然景致,更兼价廉物美,首先来照顾它的是南门一带生意人,就不办会酒,也常来打平伙。其次的常客是学生们。到学生们作了常客,才悬上招牌,不知是哪位雅人给它取了这个切合实景而又带有诗意的名字:枕江楼。虽然这时还只有楼之名,而无楼之实。
枕江楼只有五个座头,寒冬数九还好,从初春赶青羊宫的日子起,它这里就生意兴隆。如其在下午两三点钟来,包你不能够随来随坐,人少也绝不能独霸一个座头,不让后客来镶一下的。
这天,顾天成三人来时,刚从大桥这头走进一间柴炭铺子的过道,再下几级石阶,踏上枕江楼的石堤,就听见全排平房里全是高声大嗓、癡拳闹酒、谈家常话、讲生意经的声气。从没有糊纸的菱形窗格中看过去,只见盘着发辫的头,精赤条条的背脊和膀膊,原来正逢上座时候。
吴凤梧站在石级上说:“好生意!”顾天相说:“我的估计没错罢?依我说,还是到北新街的精记去。不然,就总府街的崧记也好。”顾天成前天来吃过这里的醋溜五柳鱼和醉鲜虾。觉得精记、崧记都只有蒸菜、炖菜,没变化。光是吃饭倒方便,泡菜都不差。但这里……隔着木栏杆,看见厨房正在癶鱼,炉火好旺,岚炭火焰从耳锅边冒起来好几寸高。四五个人站在菜案边挤虾仁。另一个厨子从炉子上一个挺大砂罐里,热漉漉地舀了一中碗黄焖鸡,把旁边耳锅里刚焯好了的三塌菇盖上两汤杓,递给身旁一个堂倌道:“亭子上的。”堂倌打从身边过时,啊!好香!顾天成决心不打退堂鼓。“喂!找个座头。只有三个人,镶一镶都使得。”
一顿家常饭
节选自《大波》,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摆在桌上的,是昨夜特别留下的一大品碗莴笋红焖鸡,一大品碗芋头煨羊肉。今天早晨旋做的,是素炒黄豆芽,素焖小菠菜。并非逢年过节,又不是红白喜事,两荤两素吃早饭,这在陕西街三圣巷中是稀奇事,在吴凤梧家中,当然也不平常!
吴凤梧一手挽着四岁不到的幺娃子,精神饱满的样子,从节孝祠茶铺吃了早茶回来。进门之前,特别给幺娃子擤了一泡浓鼻涕,用自己锁有狗牙边的蓝花布手巾,把一张胖胖的小圆脸揩得一干二净。一面叮咛说:“娃儿家第一要学爱干净,第二要学讲卫生!莫跟巷子里那些滥娃娃学:不管啥子脏东西都要抓一把!也不管吃得吃不得的,捞到了便朝嘴里塞!要不得!不听话的娃儿家,妈妈见不得,我也不再带他进茶铺,也不再买和糖油糕跟他吃了!”
“我听话,明天你再跟我买一个和糖油糕哈!”
刚刚掀开木板门扉,一股油香味直扑鼻端。吴凤梧摔脱幺娃子小手,抢到桌子跟前,只一眼,便欢然叫道:“吆!好阔啦!两荤两素。大女子,快拿饭来!”大女子提起尖嗓子高应一声:“就来!”立即从堂屋后面的灶房里,把一只钱花大瓦钵捧出来,放在靠壁一张大茶几上;顺手舀了堆尖尖一大碗糙米饭,端给坐在方桌上首,已经在动筷子的父亲。“你妈呢?”
“妈还在弄菜。”
“有这们多菜,还要弄,哎!哎!有福不可重享!”他不由想起上次只有一盘臭豆腐乳的光景。
老婆穿着蓝布围腰,双手端了一只海碗出来,翘起厚嘴皮笑道:“并没弄啥子菜,只是打了一碗酸辣蛋花汤,你喜欢吃的。”
“哎!难为你啦!”吴凤梧今天会说出这样客气话,足见今天的脾气格外好。
他的老婆也像叫化子中了头彩,喜欢得合不拢口。那只有毛病的眼睛癋得格外起劲。小心翼翼地把海碗放在桌子当中,把两样荤菜尽量挪在上方。然后拉围腰揩着手指笑道:“有啥子难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