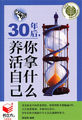进驻东寺农场的社教队,由省上一位厅局级干部挂帅,社教队员由本省东部地区农(牧)场抽调干部约二十人组成。场党委书记李士奎由于新从外单位调来不久,与农场历史旧账无涉,为了便于工作’被委以社教队副队长职务,可谓一身二任。由于相类似的原因,曾源也被吸收到社教队办公室搞材料兼做相关工作,也是一身二任。
全场的社教运动分四步走:第一步学习文件,武装思想,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为指导“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统一全党思想,指导各单位的社教工作。
社教运动的进程大体上分四步走:
第一步,学习两个“十条”,提高思想认识,重点领会和掌握开展“社教运动”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工作重点,干部政策和方式、方法、问题等内容。
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国际形势严峻;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数不少的干部爱搞浮夸,瞎指挥,以权谋私,多吃多占,强迫命令。加之饥饿受困,使广大群众情绪低落,对前途失去信心。为了拨开迷雾,激励斗志,在学习文件的过程中,教唱一首名为《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新歌,教歌任务由汪继丰担当。汪音色圆润,唱歌旋律流畅,在灿烂的阳光下,场部大院里荡起了动人的歌声。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劈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
我们的道路条条宽广,我们的前程无比辉煌,我们献身这壮丽的事业,无限幸福,无上荣光,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气势不可阻挡,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
音乐给人饱满的激情,音乐给人想象的翅膀,音乐给人时代的记忆。在数十年的人生道路上,汪继丰优美的歌声,总是给曾源无尽的感染:解放初期投笔从戎之际,汪继丰吟唱的一首《友谊地久天长》,激励同窗好友投身革命,奔向光明;1951年国庆游行的队列前汪继丰教唱的《歌唱祖国》,唤起战友们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前些日子他在场广播室播送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一一焦裕禄》和今天教唱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又一次激荡起同志们奋发向上的豪情,为动员群众投人“社教运动”增添了力量。
第二步,在深入学习文件精神,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四不清”的人和事,同时号召有问题者走“坦白从宽”的道路。
三年困难时期,一部分干部和管理财、粮、贸的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多吃多占、假公济私相当严重。一般群众对此愤懑不平,当地有个顺口溜唱道:“社员吃的四两粮,拄着棍子扶着墙;干部吃的四两粮,推着车子赶着羊,又打庄子又盖房。”这种反差虽有夸大之词,但却是一个“吃”字分出“两个世界”、两种群体。这种情景加上运动初期执行政策偏“左”,一度出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人人过关,基层干部和财、粮、贸人员几乎无一幸免地被列入“四不清”之列。
第三步,召开场、队、组“三级干部会议简称“三干会”),听取和帮助场领导干部及前一段清理出来的“重点人物”在“三干会”上检查、交待问题。为了壮声势,增强“火力”,会议还特意从基层吸收了一批“斗争性强”的“积极分子”代表列席会议,使会场时而出现逼、供、信和过火斗争的局面。
会议的结局与一些人的预期相去甚远。原来的一位副场长,一位副书记,都比较清廉,律己甚严,检查了一通,经济上都没有多大问题,尽都是官僚主义作风方面的一些问题。副场长还检讨了自己用从老家带来的旱烟叶子在面粉厂换麸皮吃的“错误”,听来令人唏嘘!
有个生产队长心眼儿稠、点子多,今年二轮灌水特别紧张,正面要水要不来,他想了个办法,把水管所管事的请到队部,油饼煎鸡蛋、好烟、好酒招待,门口却栓了羊圈上最凶的那只狗,生人别想随意进出。安顿好水管所的管水人,生产队长立马命令几个组长组织力量,扒开渠口,从中午一直浇到太阳落山。
绝大部分被称作“四不清”的基层干部,实际只有一般性的多吃、多占和强迫命令的缺点毛病。检讨了,认错了,本该放其过关,但因少数社教队员和“群众代表”思想偏激,揪住不放,使好几位基层干部过不了关,受到停职检査的处置,吓得一位干部上吊自杀未遂。‘为了便于澄清问题,防止发生意外,将已停职靠边站的几位基层干部集中到场部,连同场部几名群众意见大的干部共编一个班,任命曾源任班长一一有人背地里叫他“四不清班”班长:一面参加平田整地劳动,一面落实问题,缓解了这些人与所在单位群众的矛盾与对立,有利于“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
问题严重,情景恶劣,受到严厉惩处者只有两名:一名是一个基层单位的管理员,贪污盗窃公款、公物,倒卖职工口粮,数额较大,且本人态度恶劣,被判处劳改;另一名是四场合并前某场总支副书记,利用职权诱奸一上海移民的妻子,另有吸食毒品之嫌,被开除党籍,撤职查办,因其认罪态度好,免于刑事处罚。
第四步,整改阶段。主要工作是落实定案,精减机构,调整干部,建立健全制度,发虐党团员。
社教中只发展了一名党员,此人便是场党委书记李士奎的老婆、农场小学校长叶曼玲。促成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叶曼玲早年的情人贾成龙从中斡旋。
这事说来话长。
半年多以前,农建师师部成立不久,当时曾源在师政治部宣传科任干事。有一天下午,师机关职工在大食堂餐厅听师政委做形势报告,会议中段休息期间,与曾源同坐一桌的一位尚未脱去军装的转业军人主动与曾源搭讪,他露出一副早就与曾源相识的样子问这问那。开始曾源误以为是当年在部队搞“审干”外调期间在什么地方偶然相遇而结识的一位外地军人。后来他又问曾源你还记得解彦西吗?”“呀!你是、你是贾成龙?”一下子弄明白了与自己套近乎的此人原来确实是个老熟人:少年时的同学,参军初期短暂相聚,也有几分恩怨等等。只是由于十多年未见面了,才有陌生的感觉。
贾成龙所说的解彦西是当年与曾源同在一个团的教导队的指导员,当时贾成龙从青干班毕业后分配到这里当军体教员,后来解彦西调团干部处任副处长,不久贾成龙被调到司令部作战股任见习参谋,那时曾源在团政治处宣传股任干事。
贾成龙调来团部不久,部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贾成龙因解放前有恶迹被人告发而遭逮捕,送军法处法办,此后再未见过面而且不知其下落,算来已是十三年有余。那些年他们正值发育旺季,双方从外形到气质都有不小的变化,故而有故人对面不相识之事。
贾成龙得知曾源在政治部工作,不无羡慕地说:“我在部队当政治指导员多年,对政治工作比较熟悉,现在分配我在供应科工作,有点不习惯,也不感兴趣,你能不能给政治部有关领导反映一下,把我调到政治部工作。”
曾源笑着说:“我是个小萝卜头,人微言轻,无济于事,你何不自己打一个报告,更直接,也许还来得更快些。”
后来的结局是贾成龙未调往政治部而是步曾源的后尘调到东寺农场当了组织人事干事,这可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实权岗位。令贾成龙惶恐不安的是到了东寺农场之后,他才知道十多年前的旧情人叶曼玲也在这个农场,而且是丰场一把手的妻子,这多么尴尬。叶曼玲这边则暗地里自叹“不是冤家不聚头”。尽管两下里进退维谷,但还必须接受这个现实。由于这种微妙关系,叶曼玲采取“绕道走”,佯作不识的态度;贾成龙则是利用其职权,暗地里使劲,取悦对方,回报和安抚对方,以表愧疚之情。
这种缘由,在场里包括李士奎在内无人知晓。知其根底、原委者只有曾源和汪继丰二人,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曾、汪二人面对如此这般的现实格局,只能讳莫如深。
贾成龙与曾源一样都是新调来的干部,与全场过去的是非无涉,贾成龙便利用人事配备过程与社教队干部接触多的机会,推荐叶曼玲作为党员发展对象,说她在原单位已作为“发展对象实际仅写过人党申请书),时下担任学校校长不是党员不便工作等理由,使叶曼玲成为这次社教运动中发展的唯一党员。就这样以投桃报李之术一方面满足了叶曼玲的虚荣心,一方面化尴尬为默契,收到捐弃前嫌之效,但却为未来场部机关的政治生活埋下了祸根。
东寺农场的“点上社教”历时约三个半月,于1964年7月中旬结束,继之而来的是借社教运动的强劲东风,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促进农场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开发、大发展时期。
在国营农场的历史进程中,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人们的思维定势是:农场的建设与发展就是增加人,上基建规模,以开荒造田的数量来评功过、论是非。凭基建项目向上面要投资,靠上级拨款,安置从不同渠道来的劳动力,其中有不少人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被送到农场。由于资金有限,劳动力素质不高和简单、粗放的经营管理,致使劳动生产率低下,劳动成果不足以养己;开荒造田不长庄稼,反而起了破坏植被,引发沙尘暴,打破生态平衡的结果。地荒、人散,愈开愈荒。
1965年初,从“五花农场”调来一批从营到班的各级领导骨干。这些同志大多数是前一年被安置在该场的复转军人和来自天津、西安等地的城市“知青”,以此为基础,又从本场抽调一些连、排干部组成接收新兵的骨干队伍,分赴有关城市接收当地政府动员好的一批社会青年。是年5月开始,先后接收济南、青岛、天津知青1179人,分编为六个连队,投人农田建设和房建工程,农场随之更名为农建师四团。
为了适应知青人数猛增,农场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师部从兄弟团场给四团陆续调来一批干部。其中有四人是曾源的熟人:原“五花农场”常务副场长杨光远调任四团团长;从“红星农场”调来三人:左德恒任四团政治处保卫科科长兼公安局局长;高强任机关协理员兼党总支书记;吉子实任工商科会计。
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和锻炼,年轻的朋友们力闯“三关”(思想关、生活关、劳动关),脱去骄、娇二气,愈来愈自觉地将所学的革命道理和“雷锋精神”融人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劳动出成果,精神变物质。知青们已成为农场的一支强大的突击力量,为农场的生产建设和各方面的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截止1965年冬天,六个青年连队共修建成大小渠道29581米(合土方81913立方米),平田整地6亩,改造老农田25亩,洗盐碱163亩,房屋建设332平方米,修建地窝子23平方米,修建简易公路3公里,烧砖137块,制砖坯3万块。此外,在夏、秋收等农忙季节还大力支援了农业。
知青们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增长了才干,学会了做各种农活,在平田整地、挖沟开渠等劳动中由完不成定额到超额完成任务,不少人学会了灌溉、砌墙、盖房、油漆门窗,制作水泥预制块乃至套犁、赶车等劳动技能。
这年年终,知青们被吸收加人共青团的122人(其中男39人,女83人);被提为排以上干部的19人,正、副班长的154人,调任其他业务干部的6人;被选送到场内外各种训练班学习的24人;被评为本年度“五好职工”的24人;被评为各种“突击手”称号的225人。
青年们在劳动生产和新的集体生活的锻炼中不但强化自身,而且给农场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改善着职工的精神面貌。
田间地头,宿舍内外,随处可以看到小伙子矫健的身影,听到姑娘们银铃般的歌声,荡漾着青春的气息。
各连队分别抽文体骨干组建业余演出队、篮球队和黑板报小组,成为对内鼓舞士气、对外展示连队风貌的重要工具。场部平均每月都要举行文艺会演和球赛一至二次,为各类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在此基础上,场里择优选拔组建了半专业性的演出队和篮球队,常到场外友邻单位和市里演出和参赛,为农场争回不少荣誉。
《长征组歌》、《江姐》和《打靶归来》等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在农场的土地上随处可以听到,比之当时的城市文化生活毫不逊色。
来农场的知青中蕴藏着为数众多的各类人才,各基层单位分别选拔了一批政治思想表现好、劳动好、文化程度较高或有某一方面的专长者充任会计、统计、施工员、水利员、文书、小学教员等职务,促进了基层业务建设和各项任务的完成。
机关科室更是择优选调,好中选好:广播员、打字员、收发员、气象员、户籍员等一个个长相俊美,心灵手巧,被誉为机关“五朵金花”,招来不少青睐。
成百上千的年轻人当中难免有少数调皮捣蛋的“小痞子”为青年群体增添着别样的色调:有的恣意找乐,穷开心;有的纯粹是恶作剧;有的于调皮捣蛋中夹杂着几分黑色幽默。场里流传着几则小故事“涝池当海”。知青们初来农场一段时间,由于井水量小,做饭、烧开水都紧巴巴的,又要尽量满足青年们洗衣服、讲卫生的需要,为此,各连专门挪出一两块地灌上水作为“临时涝池”,经过两昼夜的沉淀后汲取清水使用。这事最怕施外力将水搅浑,所以饮牲口者也不准擅人,然而有一天,一池清水却被一个调皮的小青年搅了个一塌糊涂。
这个小青年来自青岛,是海边上长大的,来农场半月有余没有洗过澡,身上黏糊糊的难受,又想“蚊龙人海”施展游泳本领。有一天他发现这块“临时涝池”里盛满一汪清水,便不问青红皂白,脱去衣服,来了个任我沉浮,悠哉悠哉。片刻工夫,’一池清水被搅了个浊浪翻滚,一片混浊。正在这个时候,他们连的连长一个年约四十岁的转业军人扛着铁锨从干渠上走了过来,见此情景,手指着这位“游泳健将”连说:“你、你、你!”他气得说不出话来,又一想城市知青到了戈壁瀚海,不明事理,情有可原,遂按下怒火,耐心地向他说明缘由。这个青年如梦初醒般一伸舌头,摸脖子憨憨一笑,溜了。
“军垦吉普”。许多连队距离场部较远,青年们去场部办事,到卫生队看病,来商店购物或到邮局寄信,取包裹等,常常乘毛驴车前往。当然许多时候是经连领导批准的,也有不少时候是“偷”着干的,找一辆架子车,套上毛驴就得了。这种车轻快、省力,又没风险,坐上去找根柳树枝一吆喝,自由自在。有人便给这种毛驴车起了个雅号叫做“军垦吉普”,倒是颇具几分“时代气息”。
“庄橡(装甲)部队”。那时候正规部队早已用数宇符号作部队的代号,小青年们对此如同羡慕红五星、绿军装一样馋眼。他们给自己编了个代号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庄稼(装甲)兵2654部队”,系按月工资26—54元标数,既幽默还蛮能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