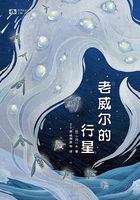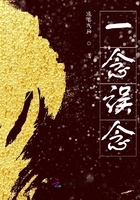期待中的油印小报《拓荒报》创刊号于党的生日前夕正式出版了。曾源写了《抓革命,促生产’迎七一》的述评,根据第二季度评选结果,表彰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梁玉泉和贺小露下基层跑了一圈,征集、采编了一组从各个侧面反映生产生活的稿件,内容丰富多采,形式生动活泼。创刊号一炮打响,深受群众欢迎,不少人反映该小报办得好:真实、生动,贴近生活,使得报社人员挺受鼓舞,决心尽最大的努力,给军垦战士们送去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小报按此思路继续办了几期。小报受到基层广大读者拥护的同时,却在机关的一些人中受到冷遇。有人贴出大字报批评编者“不关心国家大事,是最大的脱离实际”,这等于是向小报兜头泼了一盆凉水,实际是向小报采、编人员下战书。“怎么办?”“报社”的人又气又有点惊惶失措。对此举曾源已做了冷静思考:“什么是关心国家大事?如何去关心?”用意十分明白,就是要把小报的倾向性拉向“两斤棉花问题”的旋涡之中,为其推波助澜。曾源告诫自己:不能上当,任他叫板,我自岿然不动,他提出的“背靠机关,面向基层”的方针得到报社全体成员的拥护。
“报社”未受干扰,依然我行我素。
全团范围内文化大革命”的潮流冲决一切。兴许是接到了上级的相关指示,团党委决定将小报“暂时停刊”〔如何处理小报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心里没有谱,倒不如停刊了事从连队借调来的四名知青两名男的暂留安置办公室工作,两名女知青中肖玉玲留作打字员,贺小露当了收发员。
曾源和大批机关人员抽出来派到基层,任务是“发动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不言而喻,此举乃是文革初期派工作组路线的思路。
2曾源作为工作组成员被派往“机车保养间机修厂的前身)。他这个工作组,既无领导又无被领导,光杆司令,孤军作战。
保养间是直属团部的一个小单位,有职工三十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曾在机车上或机修单位干过,有一定的机车维修保养技术和经验,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群体。职工之间,程度不同存在着技术封闭、保守,互不服气,互相戒备等旧工匠式的一些陋习,严重地影响着内部团结,故而单位不大,是非不少。
保养间有一部分职工,曾源因多次同他们一起打过篮球,早已是熟人,彼此说话比较随便。
有一位四川籍姓黄的修理工问曾源:“曾秘一噢,该叫曾组长了,没得组长叫啥子工作组一一曾组长,我问你,你这工作组下来干啥子哟?”
“同大家一道学习,搞‘文化大革命’嘛。”曾源郑重地回答说。
“说得倒轻巧,案子不破,人心惶惶,谁还有心思搞啥子‘文化大革命’。”
黄师傅直摇头。
黄师傅的话虽是一家之言,却让曾源摸到了保养间职工时下的思想脉搏。曾源到保养间两日来,发现职工中议论最多、最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一“破案问题”。
这事还需从头说起。
最近一个多月来,保养间先后发生了四起机车修理事故:一起是已经上好的螺丝莫名其妙地松脱了,试车中险些翻车;一台正在检修中的机车的一处连接部件不翼而飞,使这台车一时装配不起来;另有一台车油路几度堵塞,原因不明。最为严重的是一台修好的发动机,启动试车时发出异样的声音,打开一看,不知道是何人把一节连接杆放了进来,差点磨坏缸体,使发动机报废。
就这么几件事,事出蹊踐,不得其解,闹得人心惶惶,生产频于停顿。保养间的领导向团里报案,保卫科长兼公安局长左德恒带了一名干事,亲自来保养间破案,又是查现场,又是拍照,又是找“嫌疑人”搞“审讯笔录”,煞有介事,怪吓人的。
保养间有个叫古振武的修理工,1949年人伍,开过多年的拖拉机,现任拖拉机修理组的组长。工作认真负责,技术上也有一手,只是由于他秉公办事,性格急躁,得罪了一些人,多次评比中,以“不能团结人”之类的缺点而落选。
这次政治处保卫科长兼公安局长左德恒下来破案过程中査知那台被塞了连接杆的发动机就是古振武经手修理的。审查过程中,左德恒找他谈话时,他情绪激动,发了很多牢骚,左德恒对他的印象很不好。后来在对“怀疑对象”的排摸中,左德恒凭想当然提出是古振武自己搞鬼,栽赃陷害别人,有“监守自盗”之嫌。此事后来被古振武得知后,又哭又闹,破案者手中无证据,下不了结论,事情就这么搁浅了。其他几起事故,也都欲破未破,或主观臆断,或扑风捉影。案子一个未破,反而煮成了一锅夹生饭。导致的负效应是人人自危,互相猜疑,互相埋怨,组织涣散,生产、工作不如“破案”之前。又使团政保卫科在保养间威信扫地。
面对保养间如此严峻的环境,曾源肩负的“发动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使命无法兑现。人们期盼的是悬案告破,关心的还是还好人以清白。别的事还无法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
保养间的人对曾源的到来持怀疑的态度。“堂堂保卫科长兼公安局长都破不了案,又派来一位‘秀才’做工作,这个是弯弯路过了山嘴嘴一没有指望了。”“我们想关心国家大事’可是没人关心我们的大事!案子不破,人心不安。”
身临其境的曾源思来想去:不从破案入手,一切将无从谈起。那时候法制不健全,民事、刑事诉讼都无处投诉,况且既无原告又无被告,更是无从入手。“我必须面对现实。”曾源决定,从深人调查研究起步,多动脑筋,解开谜团。
曾源凭借当年搞“审干”时练就的调查取证的基本功细心排查,严密思考,找出矛盾,追本溯源的思维习惯向疑案挑战。
他首先从“面上调查”人手:先后召开班组长座谈会、党员座谈会、复员军人座谈会、团员座谈会、相关人员(参与修理过后来事故机车的人员座谈会。对四起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发现过程等细节做全面了解,从总体上对几起事故的轮廊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第二步,缩小范围,理出线索。保养间共三十几个人,曾源挨个儿进行了个别谈话,主要是询问每个人所了解的情况和对破案的看法。
三天时间,曾源与保养间的全体职工分别谈了话,然后做综合分析,将无关的人和事排除在外。剩下来的便是直接或间接与四起事故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牵扯的人和事接触,这部分人还不到全体职工的四分之一。这部分人在全体职工面前“亮”了相,他们不同的表情和姿态给包括曾源在内的与会者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东西。
第三步,突破重点,解开谜团。曾源与骨干们反复研究,选定从发动机里塞螺杆这起事故入手,揭开盖子,全面突破。这样选择的理由有三:一是这台机车是组长古振武经手修理的,不难找到下家,古振武本人有急欲洗清自己的强烈愿望;二是事故中人为做手脚的迹象明显,引起强烈公愤,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三是团保卫科长左德恒上次来破案中下过“监守自盗”的结论,给后来者树了“反面示范”,有利于逆向思维,破中有立。
基于以上分析,保养间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会名“事故调査分析会”,这里没有“审察”和“被审察”之分,也没有“原告”与“被告”之分,而是就事论事,名抒己见。
保养间设在老场部旧庙大殿,廊檐很宽,会场极不规则,与会者或坐在门坎上,或坐小板発,或坐在拆卸掉的拖拉机部件上。7月的午后,天气燥热,大伙儿精力蛮集中,对今天会议的内容和完全“亮开来”的开法饶有兴趣。
果然未出所料,古振武迫不及待地站出来为自己辩护。
古振武长一张国字脸,三十七八岁年纪,身体壮实,皮肤黑里透红,说话口齿有点不清楚。
“上次左科长来保养间破案,硬拿屎盆子往我头上扣,有的人诚心当跟屁虫,故意把水搅浑,背地里嚼舌根栽赃害人,有种的拿出证据来?谁修好的车谁故意整坏?那还是人吗?真是!”他下意识地擦了一下鼻尖上的汗,他这人一激动鼻尖上就冒汗。
“肚子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有理走遍天下,有话好好说,你急啥?把你那些带把儿的话都收回去。”会场上有人夹枪带棒地与他较劲。
“你说发动机里塞螺杆的事你没有干,有谁能证明?”
“你修好车后,试车没有?”有人追问。“试了,机车运转正常。”古振武回答得很干。
“有谁看见了?”
“小黄黄小东。”
“小黄,你说说是这样吗?”会场上有人插问。
“对头,那天古师傅试车时,我在现场,没发现有啥子问题嘛。”
会场上一片嗡嗡声。
“不要开小会了。”曾源把会议引人正题,“试完车到发现出故障,这中间隔了多长时间?”
“我试车是9点多钟,发现有人给发动机里塞螺杆是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一因为这台车第二天要交付使用,我又把发动机仔细检查了一遍,一切正常。”
“俺提一个问题,”一个山东籍叫王守成的修理工用推理的口吻说,“现在看来’上午和下午的上班时间车间里都有人,干这事只能是中午一一中午是最紧张的一段时间,谁还有闲工夫跑到车场搞鬼?”
“这个问题提得好。”
“这家伙真狡猾,专门钻空子干坏事。”
“咱们应当好好查查,这天中午有谁到停车场来过?”
会场上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我看到有个人到停车场来过。”说话的是一位姓傅的修理工。
“谁?快说出来!”
“噢,嗯,那个,那个一”
“这有什么?你看见谁了?说出来怕什么。”曾源扬了扬手臂。
“是袁师傅袁正兴,我看见他从停车场走过来,朝古师傅修理过的那台机车跟前走去。”
“你那时候在什么位置?你咋看到他的?”
“那天下午特别热,我想找个阴凉、透风的地方,好好睡个午觉,找来找去停车场南边那台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上最理想,我就爬了上去。”
会场上一阵哄笑声。
“我躺下身子没过多久,一只苍蝇嗡嗡嗡,老在我的头上、脸上飞来飞去,这咋能睡好觉?正在我爬起身子轰苍蝇的工夫,我看见袁师傅正从停放机车的方向走了过来。”
会场上的人,齐刷刷扭头朝袁正兴看去。
袁正兴,三十出头年纪,身体修长,文质彬彬像个书生。此刻他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脸上转颜转色,很不自在。
“袁师傅,有没有这回事?”曾源不愠不火地问了一句。
“我,我没,去,不一一我是说我没到那台机车跟前去。”袁正兴出语吞吐,欲言又止。
“那你是去了停车场?中午下班的时候你去停车场干啥哩?”会场上有人质问。“我、我,找鸡我家的一只下蛋鸡不见了,我,我没,没找着。”袁正兴依旧遮遮掩掩,只不过越描越丑罢了。
会场上又一次潇起一片鳴鳴声。
快到下班时间了。曾源与同座的保养间负责人交换了一下眼神意思是会议就此打住,会后再做工作。
会后,趁热打铁,曾源于当晚找袁正兴个别谈话,火候正好。
曾源说:“袁正兴同志,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给你留了面子,这一点你该明白。”
袁正兴频频颔首,面露愧色。
曾源接着说墙里说话,墙外有耳,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想这些话对你是有切身体会的。错了,咱们就认错、改错。闭着眼睛说假话,那叫自欺欺人。”
“唉,”袁正兴长叹一声,“都怪我一时糊涂,私心膨胀。”
袁正兴生性乖巧,工于心计。他原是农建师凉城拖修厂的一名技工,去年夏天师部为加强基层修配力量,从拖修厂抽调一批技术骨干充实到几个团的机修部门,袁正兴分配到本团的这个保养间,发现这里的设备和修理水平远不如他原来所在的单位,特别是这里的修理工基本上都是拖拉机手岗位上调来的“半吊子”和从部队复员下来的“门外汉”,使他在这里有“鹤立鸡群”之感。年轻的修理工们对他很尊敬,他还嫌人家“笨手笨脚”。唯独古振武见他那副傲劲儿,不太搭理他一古振武这个人工作踏实’做活细心,出活质量好,受人敬重。人家如此,不仅无求于他,有一次袁修理一架发动机时,大概由于粗心大意把一个部件安装错了,古振武当众给他指出来,使他很尴尬,虽然口头上认了错,心里却装上了几分忌恨。一山不容二虎,自己想充大拿,却被别人一头顶翻,他便思谋着找个机会给对方一个“扫堂腿”,让古振武吃不了兜着走。于是便有了后来他把螺杆塞到古振武修好的那台机车的缸体里的事故发生。
袁正兴在曾源面前认了错,同时还交待出另一起小事故也是他所为,用他的话说:“我是想试试这帮人能不能找出毛病来”他表示今后坚决改正,决不重犯。
曾源对他认错、改错的态度表示肯定,并鼓励他在全车间职工大会做深刻检查,一定会得到同志们的谅解。
第二天下午,召开保养间全体职工大会,袁正兴在会上做了全面检查,既交待了作案的动机和作案过程,又挖了思想根源,流着泪恳切表示自己今后一定痛改前非,光明磊落做人。
袁正兴做完他的检查,有几个同志提了一些意见和希望,袁正兴的大会检查遂告通过。这可算是思想通,检查实,放下包袱,重新做人。
会场上呈现出宽容、谅解和促进的氛围。古振武对自己的傲气和粗暴主动做了自我批评。
抓住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便会迎刃而解,借袁正兴案件结案的东风,其余两起案件相继告破。由此而使保养间职工群众的气也顺了,心也齐了,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曾源靠走群众路线,靠抓人心破案一事,被保养间职工传为佳话,同时还受到老团部那边诸多友邻单位职工的好评。消息传到机关,使保卫科长左德恒的心头落上了几分嫉妒,几分苦涩,那滋味比1951年看到曾源在军区理论教员训练班大会发言受好评和1957年得知曾源因“审干”外调工作出色受嘉奖的妒意,有过之而无不及。
破案问题告一段落。正当曾源思谋着如何将群众的积极性引向投人“文化大革命”之际,有一天下午,党委书记、政治委员李士奎检查完老团部这边几个单位的工作,顺道来保养间视察。曾源向他简要汇报了破案的情况和破案后群众情绪高涨的可喜形势。
李土奎说破了案是好事嘛,但也不能满足眼前的成绩,停滞不前。最近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咱们要紧跟哩。要引导群众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可不能掉队呀。”他又对曾源说你们下到基层的机关干部,既要抓好你们所在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也要积极参加团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应当写出一些有分量的大字报送到机关去。”
李书记走后,曾源对他所说“有分量的大字报”琢磨不透,故而对大字报的主题一时确定不下来,心里有点着急。
这天吃午饭的时候,曾源从食堂打了一份饭出来,正碰上工商科的几个人前来打饭。当时老团部这边的几个团直属单位的职工都在这个食堂就餐,食堂归机耕队管理。
曾源和工商科的几个熟人蹲在一棵大树底下一面吃饭,一面聊起机关“文化大革命”的近况。
工商科会计吉子实是曾源的故交,说话不避嫌,他说:“机关上的‘文化大革命’还在‘两斤棉花’里转圈子,不打破这个僵局,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
工商科副科长老盛个三十出头的河南人,处事精明,出言谨慎,他插话说:
“老吉以我们三个人的名义写了一份大字报,我们想请你这个‘秀才’提提意见。”
“曾源同志肚子里墨水多,好好给我们参谋参谋。”大个子、工商科指导员老齐是个爽快人,喜欢直来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