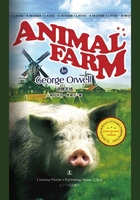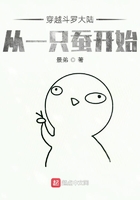“医师若能快点回来就好啦!”
“说这话也无用,回不来仍是回不来。”
伦子歇斯底里地狂喊起来,只有两眼不住地朝正门望着。
救护队员从治疗室跑到二人面前。
“大夫还没来吗?”
语气虽然平和,内里却饱含愤怒。
“刚刚去‘出诊’,现在也该回来了。”
“什么地方?”
“就这附近。”
“那里有电话吗?”
“我刚挂过电话,说是已经回来了。”
“出了那么多血,若不赶紧抢救,恐怕……”
“真对不起!马上就到。”
伦子鞠躬致歉,内心真想大哭一场。等直江医师回来时,定要狠狠地发发牢骚,但另一方面也应责怪自己明明知道可能会发生这类事情,为什么还默许他出去呢?
救护队员们明白向护士们抱怨也无济于事,于是又都回治疗室去了。
“跟他们说谎话能行吗?”
“不那么说不行呀!”
阿薰似有所悟地点点头。
“若是他也因为喝酒把脸划破该多解气。”
伦子在昏暗的楼房正门喃喃自语道。门前救护车上的红色标志灯仍旧一亮一灭地闪着。伦子又抬头看了一次钟表,与上次看它时相比,只过了三分钟。
又有一辆响着警笛的车开来了,两人从挂号室里急忙跑过来,原来是乘着巡逻车的警官赶来了。
“患者在哪儿?”
“在治疗室。”
“不要紧吗?”
“估计没大问题。”
“做手术了吗?”
“还没有。”
警官点了点头,走进治疗室里。
医院门前似乎已经集聚了很多人。伦子闭上眼,数起数目来,一、二……数完六十个数就是一分钟,数过四五个反复,直江就能回来。
第一次刚刚数到三十时,一个救护队员从治疗室跑来问:
“护士小姐,他要喝水,可以给他喝吗?”
伦子觉得患者不是腹内创伤可以喝点,但没有确切把握。
“他说渴得要死。”
“若是少许一点点,我想是可以的。”
“杯子呢?”
“这就给你拿去。”
伦子从药房里拿来杯子递给救护队员时,阿薰大喊:“大夫回来啦!”
回头一看,确实见有一个男人正在昏暗的入口处脱鞋。他换上院内鞋后径直朝这边走来。他瘦长身材,右肩下垂,正是直江医师。
“大夫!”伦子朝大楼正门跑去。
“怎么样啦?”
“浑身是血,暴跳如雷,无从着手。”
“给我拿白大褂来!”
直江医师脱掉西服,只剩下没系领带的衬衫。伦子急忙把挂在外科门诊室里的白大褂拿来,从直江身后给他穿上。
“我对他们说您是‘出诊’去了。”
直江会意地点点头,然后把脸凑近伦子的脸问:“有酒味吗?”
“有点,不过不要紧。”
“嗯。”
从黄昏起一直喝了四个小时,可直江丝毫没有醉意。他的脸色更加苍白了。
“不缝合不行呀。”
“缝合准备已经做好。”
“真够吵闹的!”
直江轻轻皱起眉头走进治疗室。
“大夫来了!”
伦子一声叫喊,救护队员们便一齐回过头来,从担架旁闪开。
直江来到床前,盯视患者。
“喂,大夫!你干吗来的?混账东西!”
患者挥舞着拳头坐起来。直江在离他一米远的位置上察看他脸上与头部的伤势。
“他妈的……”
患者放下两腿,要从床上下来。救护队员们再次从左右把他按倒。
“回家,我要回家!”
醉汉在床上乱蹬两腿。
“喂,你消停点!”
“少啰唆,给我滚开!”
“让大夫给你看一下。”
“我要回家,躲开!”
醉汉大叫,每次转过脸,鲜血都四下溅出。
“消停点,请大夫给你治伤。”
“滚开,滚开!”
他一边骂人一边往地板上乱吐唾沫。
直江起初默默地看着他,随后向旁边的警察使了个眼色,走出治疗室。
警官也随后跟了出来。
“您看怎么样?”
“是啤酒瓶划破的。”
“嗯,好像是从正面砸在额头上的吧。”
“受伤多长时间了?”
“唔,离现在有十五分钟或是二十分钟吧。”
“他喝了多少酒?”
“听说喝了二十杯威士忌酒,反正他醉得够呛。”
又传来了醉汉的喊叫声。
“同他打架的对手逃掉了,他就更躁狂了。”
“多大年龄?”
“二十五岁。”
直江点了点头,又转身吩咐伦子说:
“把门诊厅的厕所电灯打开!”
“厕所灯?”
伦子反问了一句。直江未予回答,只是朝对面的警官说:
“请把他抬到厕所去。”
“厕所?就是大小便的便所?”
“是,送到女厕所去。”
“抬到女厕所干吗?”
“锁上门。”
警官惊诧地看着直江。
“锁上门?”
“等他老实了再说。”
直江从白大褂兜里掏出香烟,叼在嘴里。
“可是他正大量出血呀。”
“厕所里墙上、地面全是瓷砖。”
“不是这样,你听我说……患者是否会因大量出血而死亡?”
“不必担心。”
他划根火柴点着了香烟。
“只要从厕所上方不时看一眼就没事。”
“从上方……”
“是的,门诊厕所的挡板不同天棚连着,所以能够从上面观察。”
“这期间若是继续流血也没关系吗?”
“血流到一定程度会自然停止。”
“然而……”
“一会儿他的血压下降,就没有力气暴跳了,那么一点伤算不了什么。”
“可他满脸是血呀。”
“额头的伤口往下流血,所以比实际的伤显得厉害,伤口虽大却不深,用不着担心。”
治疗室那边又传来醉汉的呼喊声。
“他能吵嚷喧闹足以证明没有生命危险。”
“那么说,现在就把他塞进厕所里?”
“每隔五分钟派人去察看一下,待他老实了,再来通知我。”
警官呆呆地望着直江。
“缝合要等一会儿进行,领他们到厕所去,我在值班室等着。”
最后直江向伦子说,便转身向电梯走去。
值班室在三楼病房的里侧。
警官看清直江医师走进电梯以后,转身问伦子:
“果真不要紧吗?”
“那位大夫是这么说的,当然不要紧。”
“然而,这么做是否太蛮横了?”
“没关系的。”
伦子极其坚定地说。但她自己也是初次碰到这种情况。
治疗室里,患者像野兽一样不停地吼叫。警官背着他小声向救护队员们传达了直江医师的指示,救护队员们听了警官的话也同样迷惑不解。
“真把他塞进厕所里?”
“是的,厕所在楼梯口的右侧。”
伦子在前头带路,打开电灯,推开近前的女厕所门。
救护队员们满腹狐疑地把醉汉放在担架上抬向厕所,醉汉仍旧胡乱骂人,然而,当他被撂在厕所门前的一瞬间,便惊慌地朝周围环视了一眼。两个救护队员立刻从两侧把他架起来,不由分说地推进女厕所的门里了。
“你们要干什么?喂!妈的,浑蛋!”
患者猛烈地敲门,大喊大叫。然而,有两名救护队员从门外顶着,他毫无办法。
“开门!你们给我开门,开门啊!”
醉汉继续喊叫,但救护队员们只管顶紧门一声不吭。
“请踩着这个从上往下看。”
伦子从手术室里搬来脚踏凳,放在厕所门前。
“每隔五分钟看一次就行吧?”
“在他喊叫着的时候肯定没有问题。”
“这么说必须等这家伙老实了我们才能离开喽?”
“对不起!就得这么办。”
“他不会死在里面吧?”
“不用担心,我也常来看他。”
救护队员表情生硬地点了点头,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请给我们救护总署打个电话,就说患者狂暴,暂时不能回去。”
“好的。”
伦子返回挂号室,警官正在打电话,仿佛正在了解被害者的身份。伦子把救护队员托她办的事交代给旁边的另一个警官便回治疗室了。
阿薰正呆呆地站在治疗室里的煮沸消毒器前发愣。
“怎么啦?”
“那张脸多可怕!他额头上闪着光的是玻璃碎片吧?”
“好像是啤酒瓶碎渣。”
“太可怕啦!”
“我看光是那套缝合器械恐怕不够用,你再从手术室里拿来五六个柯赫尔钳和培安氏钳。”
阿薰脸色苍白,向手术室走去。
伦子用水桶打来热水和冷水,搓好抹布。病床上的人造革和周围的地板上都血迹斑斑。当她擦完地板,做好器械消毒时,挂号室里传来一群男人的谈话声。那是语调粗暴地争论着什么的声音。
伦子来到走廊一看,有四五个汉子围着两名警官,这些人都穿着皮夹克或红毛衣等潇洒的服装。
“把浑身是血的人塞进厕所里,真是无法无天!”
“死了人怎么办?”
“这里难道不是医院吗?”
汉子们七嘴八舌地逼问警官。
“治疗方面的事与我们无关,我们只是遵照大夫的指示办事。”
警官答道。
“那好,我就去问大夫,大夫在哪儿?”
警官看见伦子从后边走过来,便走上前说:
“请把大夫叫来。”
“怎么啦?”
“希望向这群人说明一下把患者塞进厕所里的理由。因为他们的伙伴挨了打,正杀气腾腾的。”
“快点把他叫来!”
一个汉子喊道。
伦子拿起电话机,挂向值班室,三遍铃声响过,直江接了电话。
“患者的朋友们赶到这里来了,说是要见您。”
“什么事?”
“要求说明一下为什么把患者塞进厕所里……”
“你告诉他们不用担心!”
“可是,您不下来很难了结……无论如何您得来一下。”
“……”
“求求您。”
“好,我去。”
电话挂断了。伦子转身向汉子们说:
“大夫这就来。”
“本该如此!”
汉子们晃着膀子盛气凌人地坐到候诊室的椅子上。
“好像是K帮的小子们干的,只要懂点道理,他们也会后悔的。”
警官抱歉似的向伦子说。
停送暖气的门诊室寒气逼人。汉子们有的弓腰抱膀,有的两腿打战。也许是直江在三楼按动了电梯电钮,电梯指示灯从1升到了3停住了,然后又由3向1降下来。警官和一伙人一起望着指示灯的移动。
指示灯从2降到1停下来时,那伙人站了起来。这时,电梯的门开了。
直江没穿白大褂,还是刚才那件浅蓝色衬衫。他走出电梯,平静地环视了一下小伙子们,什么也没说,径直向右面走去。电梯附近有个楼梯口,再往前就是门诊部的厕所了。
一伙人同警官鱼贯地跟了过来。直江走进厕所,向倚在门上的救护队员问:
“怎么样啦?”
“噢,多少老实些了。”
救护队员慌忙从脚凳上站了起来,直江登上脚凳,从门上方朝厕所里俯视了一下。
“喂!开门……”
厕所里的汉子又喊叫起来,他的声音显然没有当初那么有力了。直江看了他一会儿,然后从脚凳上下来,又看了看手表。
“塞进这里有十五分钟吧?”
“是的。”
救护队员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答道。
“还得等一会儿。”直江说完,拧开水龙头冲了冲手,走出厕所。
那伙人又跟在他的后面走回来。尽管他们一言不发,脸上却是阴沉凶恶的。伦子走在最后,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事态发展。
直江医师似乎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他迈开大步走去。过了楼梯口来到电梯前时,他突然停住,转身问道:
“你们有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