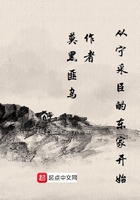真英雄,真美人,都是处在社会大动荡、大转型时代的腥风血雨中。英雄是经过非常考验的非常人,美人是霜打花愈艳的非常美人。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在安全地、平庸地、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所谓英雄也不过是鼓出了老底的勇气喊了声,吓跑了歹徒,下水救出了一个因失恋想不开的少女,诸如此类,能做到这点,也不容易;所谓美人,也不过是眉眼周正一些,打扮得入时一些,在银幕荧屏的后面和那些见色心动的导演花絮多一些,在选美赛上,让那些风光不再的老夫老妇看着顺眼一些。如此,便英雄了,便美人了?真英雄是要能扛住一个世界的,还不是只扛一时一刻,而是要扛一个时代的,要扛千秋万代的;真美人,固然要形体美,关键是心灵。我说的不是我们日常说滥了的那种心灵美。这种美是一种智慧,一种识得真人的眼光,一种穿透世俗尘埃的大通脱,一种既享得天下大福,又吃得人间至苦的胸怀。拿项羽和虞姬说,项羽亲率八千江东子弟,敢于与灭了六国的强秦叫板,一枝画戟,一匹快马,天下披靡,四海翻腾。《史记》说他自我表白道,起兵八年来,“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仅存二十八骑时,仍三胜汉军,斩其将,夺其旗,气概不减;彻底失败后,剑光一闪,一缕英魂与天地相终始,决不起苟且偷生之念。那个虞姬,红颜伴英雄,生,随之于后,万马军中,香飘四海;死,翩然于先,苍茫天地,鬼神感泣。
项羽虞姬之后的数百年间,英雄倒是代代不绝,可英雄的身边总是缺少相配的美人,还是枯燥了些。美人也是江山代有美人生,可美人总是在污浊皇宫里,与糟糕皇帝莺莺燕燕,如养在温室里的名花,其兴也勃,其败也忽,难以引动旁观者的爱怜心。这期间,衣冠南渡,北方英雄一头扎进江南杏花烟雨中,骨头马上松了,一个个变成了精于寻花问柳的风流嫖客,而生于脂粉气太重的南国的佳人,在失了阳刚的北方男人的娇宠下,从里到外除了脂粉气,更多阴气妖气。张丽华那光可鉴人的拖地美发,本是可以在朔风吹拂中撩扰天下的,却只有在糜烂后宫任其糜烂。那位暴殄天物的陈叔宝就这样把无数美人的美白白糟蹋了,她们一个个成了他的殉葬品,身也殉葬,名也殉葬。他倒也罢了,孽由自造,而美人何辜,跟着他,丧生于当世,损名于后代?不值呀。看看他作的那首被列为千古亡国之音的《玉树后庭花》吧: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客观地说,诗还是不错的,也没有那些善于跟风说话的文人说的那么“淫”,里面也没什么亡国之音——一首诗能亡了国,国家就用不着花钱养军队了,诗人写几首诗,就当七首投枪亡别人国得了——陈国要是幸而不亡,这首诗完全可入选婉约派的。按说文责自负,古今宜然,而这首诗,却让陈宫所有美人都背上了“倾国”的恶名。诗是别人署名发表的,责,却推给了几个美丽女人。
中国配与美人相伴的男人太少了啊。而在陈宫糜烂透顶时,北方人在混合了草原健儿的血液后,一批男儿悄然孕育,终于在大隋末世,一个个横空出世。与此同时,一批不甘于在脂粉中沉沦的美人也闪亮登场。英雄美人,又让历史的眼睛为之一亮,千载以下,为人津津乐道,又反复演绎的,恐怕要数李靖与红拂女的故事了。
李靖、红拂之外,还有一个虬髯客,被称之为“风尘三侠”。他们三人有点三角恋的倾向,但他们是大侠之大恋,后世的恋情小说多从这里汲取写作灵感,甚或直接套用其叙事模式,三角,多角,无数角,昏天黑地恋了起来,打打杀杀,吵吵嚷嚷,哭哭啼啼,死死生生,看似恋得紧,恋得深,恋得寻死觅活,恋得风云惨变,可经不起推敲、琢磨,稍一思量,那眼泪是用辣椒水催出来的,那情是做出来的,那恋是作者的拉郎配,本是以情串联众生的,里面最缺的却是情,无情之恋、无论恋得多么铺张,只能是对情的亵渎了;即便有恋,即便有情,也多是小男人小女人之情、之恋,犹如天上的浮云,看似阵势不小,风一吹,什么都没了。反观风尘三侠之恋、之情,正应了一句话;情不知何起,一往而深。人与人的感情,尤其男女之感情,其来源大致有二,一者常年交往,共赴危艰,耳鬓厮磨,由共同人生记忆缔结打造之情。这种情来得慢,去得也慢,但其中,男女之情的因素相对较少,更多的是一种友谊,一种习惯,一种互相依靠扶持,一种责任。另一种来源,来得奇妙,来得花非花,雾亦雾,来得没有逻辑支持,但它却来了,真真切切地来了。这种情只属于当事人,是拒绝第三者参与评价的,哪怕是父母和多么亲密的朋友,甚至当事人也不能用语言去解释,勉强说出来,一定是离了谱的。它是一种完全私人化的感觉,是一道击中心尖的闪电,是静夜里一晃而逝的月光,是闷热天的一股凉风,是眼前倏然的一亮。在物质形态上,它是易逝的,在精神层面,它却是永恒的。那一抹模糊的印记,让人心动,让人怀恋,让人忧伤,让人为之不顾一切。这种情感状态,往往被人说成是一见钟情。
李靖与红拂,红拂与虬髯客的初次见面,便是这一种情形。
红拂是杨素的家妓,深得杨素宠爱。杨素堪称隋唐之际第一人物,辅佐隋文帝夺天下,平北方,灭南陈,统一全国,许多大政方针都出自他的谋划。天下平定了,在老皇帝那里,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朝二十载;在新皇那里,他又得迎立首功,没有他的支持,隋炀帝是当不了天子的。因了这些缘故,其贵,其富,其骄横,普天之下没有可与之争锋者。加之,皇帝又一味游戏,不把朝政当回事,眼下又久留江南不归,他奉旨留守京都,成了不是皇帝的皇帝。
然而,杨素的挑战者来了,一个是他身边的美人红拂,一个是布衣平民李靖。暮年的杨素表面看来独步天下,实则不过是夕阳残照。
看看他待人的态度就知道了。
文武大臣虽比他级别低些,但也是同僚,待人以礼,不只是处世规则,亦为个人修养,即便是天子,也不可倨傲大臣,讲究的是,以国士之礼待人,对方则尽国士之职,以常人之礼待之,则做常人之事,也算是责权利相当。大流氓刘邦取得天下后,不知道自个姓甚了,大儒叔孙通去见他,他不仅以儒者之冠当尿壶,以示污辱,还故意让女人给他洗脚,以示轻慢,结果让这位儒者一顿教训,他才有点皇帝样了,或有点人样了。刘邦这种人其实挺好的,他懂得轻重利害,对自己有利的话,他能听得进去。晚年的杨素全没了青壮年时的聪明捷悟,与大多老朽一样,整个一个又老又蠢的老混球。他不是天子,却偷着享受天子的待遇,这种僭越行为,是会被灭族的,脑子正常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可他作为元老重臣,却不识其中利害。这倒罢了,每有大臣来谈工作,有客人来访,他则傲踞于床,待理不理的,眼皮都不屑于睁得开些;如此还不够,每接见来人,他还要摆排场:“令美人捧出”。这个“捧”,当然是簇拥之意了,要用手捧。除了孙二娘之类的悍妇,哪个美人有这么大的劲。中间一个糟老头子,苍髯白发,血枯形衰,衣饰华贵,却如裹在死尸上的寿衣,而身体四周,鸟语花香,百娇千媚,这是内围。还有外围,各色侍婢,四周罗列,穷极艳丽,愈显得杨素风烛残年,日薄西山气象尽现,而散回返之光。
不只杨素如此,此时,盛极一时的大隋天下气数将尽,身怀异志者早已动起来了,四海扰攘,如汤如煮:心蓄大志者,暗中在秣马厉兵,延揽人才,蓄势待发,静观其变;不愿挑头起事的志士,正在周游天下,睁大了眼睛,在做良鸟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的打算。其实,有思想有远见的美人,或游荡江湖,或身居高门,眼观六路,也正在寻找着真英雄。以杨素之久历风云沧海,且位高权重,握有天下,又俯视天下,他要有心网罗人才,哪路豪杰也比不上他的。但他早已雄心不再,老气横秋,只知尸位素餐,坐等别人为他操持豪华丧礼备极哀荣了。而那位风流天子,正风流得有趣,全不知他是日日夜夜形同男尸奸女尸,最后的风流,最后的疯狂,最后的风花雪月,最后的美人歌舞。腐草下破土的嫩草在疯长,古墓群中的树苗生机盎然,这些鲜活的新生力量,在寻找着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一代军事天才李靖前来拜谒杨素了。他一身布衣,萧条无偶,可他胸中藏着深似海的机谋,他要将这些无形的财富,卖给识货人,换取个人的功名富贵。
这是一笔双赢的买卖,对当权者,或准备当权者来说,都是一本万利的交易。李靖想把胸中之货卖给当朝第一人物,而这货,也只有杨素买得起,用得起。
李靖萧萧而来。
杨素以他惯常的姿势接见李靖。可能在杨素看来,他是给了李靖面子的,像你这种没身份没声望的布衣平民,我肯见你,都是赏了天大的脸了。可真英雄,胸藏宇宙,气吞八荒,一文不名,也是把自个当天下的主人看的。李靖不高兴了,当即敛容正色,进前一步,双手一揖,朗声说:“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杨素还算是没有彻底朽败,听了眼前这个有点冒失的年轻人的呵责,当即敛容而起,邀以共语。李靖献的是奇策异谋,听了他的话,依计而行,未来的天下大势将向何处去,还不一定呢。杨素是见过大世面、干过大事的,李靖的话他是能掂出斤两来的,当下大喜,接受了计策。在他两人说话时,杨素身旁有一绝色女子,手执红拂,边伺候主人,照应客人,边偷眼看李靖。此女乃杨素最宠爱的家妓,常伴杨素左右。如果说,杨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她则是杨素之下,众人之上。一个为人役使的女子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多不容易呀。李靖告别去后,红拂女随后出来,隔轩问杨府工作人员:“刚才出门的那个没有官职的先生排行第几,下榻何处?”大概那时的人在拜谒高官时,在拜帖上是要写明闾里籍贯家庭基本情况的。工作人员一一回明了,她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回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