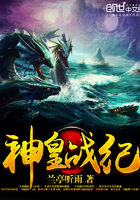秦同从怀里摸出二十两银子塞到二狗的手里,说道:“最近运气不错赚了些钱,你拿着这些银子去给大娘置办几件像样的衣裳,把那床破被子也换换,找人修修屋顶漏水的问题,剩下的钱都给大娘买药、买好吃的。”
这二人本是一个德行,二狗见秦同拿出二十两银子当即有些发愣。论感情,他跟秦同、二白是铁杆兄弟,如果他自己有钱也愿意分给二人,可论数目,二十两银子可不是他们这种十三四岁的穷少年能拿的出来的,一时倒不知道是接还是不接。
对于秦同来说,钱够花就行,这一世没有那么大的生活压力,也就不用把钱看的那么重。二十两白银虽多,其购买力也不过就是六千块钱的样子。他看二狗犹豫不接,又说道:“你快拿着吧,大娘、花姐他们有咱仨这样的儿子,也算是造了孽,现下有了钱,得让他们过几天好日子。”
二狗听了秦同的话鼻子一酸,他受尽了人们的白眼,比其他的同龄小孩成熟多了,他更加明白钱的力量。除了真正生活在一起的人,谁又能体会他们这些底层孩子的心酸呢。他伸手接过了钱,郑重地对秦同说了一句“谢谢”,然后向坊市走去。
秦同的心情颇为不错,好好地吃了顿饭,又去赌坊里玩了两把赢了一些碎银子,然后慢慢地踱步到北街的茶肆,像其他客人一样叫了一壶茶,坐下来听先生说书。这是他第一次堂而皇之地就坐,那茶肆的小二脸上露出狐疑的神色,却仍是恭恭敬敬地端上来一壶好茶。
茶喝到一半的时候,五公子走进了茶肆,在秦同的对面坐下,望向他的眼睛满是不可思议。赵思让出丑的时候她不在现场,只是听说那顿饭不欢而散,然后就被告知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嫁给那头黑驴了。她听了心里一高兴,连忙换了男装来送剩下的五十两定金。
五公子刚准备说话便想起了曾经发过的毒誓,把一个黑色的钱囊往桌上一丢,一语不发地走出了茶肆。
如今秦同身上有一百多两银子,来路虽不好明说,倒也不妨碍他小小地奢侈一把。于是喝着好茶、吃着点心、听着说书一直到天黑给了那说书先生打赏才站起来拍拍屁股走人,只觉得今天过得着实舒服,完全不知道有几个男人已经盯了他一下午。
北街茶肆距离醉花楼比较远,路上虽有夜市摊贩,却也隔了几条黑魆魆的小路,秦同来来往往不知道多少次,自信闭着眼睛也能走过去。哪知走到一半的时候猛然被几个人拉到了一旁的小巷子里,还没有看清来人是谁,便有一个袋子套在了头上,然后就是各种拳打脚踢。
那些男人个个正值壮年,下手没有丝毫的顾忌,竟是要把他活活打死。其中一个边打边骂:“打死你个妖娃子、婊子生养的杂种。”
秦同一边死命护住头脑要害,一边思索着是什么人,现在听得骂自己“妖娃子”,便断定十有八九是崔去疾派来的人。
本来秦同已经受了不轻的伤,又加上这些汉子毫不留情的拳打脚踢,很快晕了过去。
——————
与夜晚比起来,醉花楼的白天可谓是门可罗雀,连后门都没有打开,只是错了一条缝。
透过门缝可以看到一个女人穿着素雅的粗布焦急地走来走去,正是花姐。秦同平常虽然像个痞子,但夜晚从来没有不回家过,她一大早就让后院儿里的男人们帮忙去找了。
过了片刻,二狗便带着一个背着秦同的壮年男人气喘吁吁地回来了,后面跟着几个醉花楼后院的杂役,面上俱是愤怒的神色。
花姐一听秦同回来,当即骂了一声:“这天杀的野小子,胆子越来越大了。”说完便走了过去,可当她看到秦同的模样时,两腿发软、双眼一黑就此晕了过去。
秦同面上红青黑一片,没有一块正常肤色,几乎分辨不清口眼耳鼻,浑身瘫软,伏在人的背上宛似软体动物,骨头不知道断了多少根。猛然看上去,就如一个死人。
又过了一会,东街回春堂的姚大夫下了马车急匆匆地走到小屋内,对秦同的身体细细地端详,伸出手上下按按,探探秦同如游丝一般的鼻息,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然后列出一个方子让人马上去抓药。
这时花姐已经醒了过来,踉跄着跑到姚大夫的身前问道:“大夫大夫,无论如何你都要救救我儿子啊,没了他,我也不过了!”
姚大夫重重地叹了口气,看着花姐撕心裂肺的表情终于忍住没有把那句话说出来,只是说道:“我尽力吧,你先到旁边休息一下,他醒了我让人叫你。”
大夫的话说完,便有人扶着花姐到了隔壁的屋内。姚大夫轻声对身边的人说:“他浑身骨骼断裂,身上处处瘀血,如此重的伤势恐怕凶多吉少,准备一下后事吧。”
二白依旧躺在床上,浑身如粽子一般包起来,伤势也很重。他听到了大夫的话,猛然挣开了那些布带,骂道:“胡说,你这个庸医,没得误认性命。”
那大夫脸色骤变,却并没有理会二白的话,冷冷地对那老妈子说道:“我开的那副药喝下去,如果日落之前能醒过来,你们再唤我过来,如果没有醒过来,那就无力回天了。”说完这句便大步走了出去。
取药的人已经回来,花姐强撑着喂药,哪知汤匙刚贴到秦同的嘴唇,他便一口鲜血吐了出来,顺着脖子淌到了床单上,嘴唇变得惨白,面色呈现不祥的乌青,出气多进气少,过不得一时三刻便要一命呜呼。
花姐再也顾不得其他,让二狗掰开秦同的嘴巴,把一碗药一勺勺喂了进去,然后把碗“啪”的一声摔碎,面上露出愤恨的神色:“你们都是冤家,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自打走路开始哪一天不让人操心,临到头了说死就死,你死吧,死了算了,我也不活了。”
话音未落,便飞身撞向了门榜,猝然之下,竟然没人拉住。门榜有棱有角,花姐这一下若撞实了哪里还有命在?
众人的眼睛早已全部投注于花姐,哪里还有人在乎二白到底是什么反应。
眼看花姐的脑袋就要落到门榜上,一柄拂尘从屋外飞了进来,白色云丝从她额上拂过,花姐急冲的姿势便有些趔趄,脑袋重重地撞上了门后的圆柱子,虽然撞得头破血流,却也保住了她的性命。
二白脑子瞬间一片空白,也顾不得身上缠着的厚厚纱布,扑过去将花姐抱在怀里。二白母亲也是这醉花楼的姑娘,前几年因疾辞世之后他就跟着花姐生活,只当花姐是亲娘,当秦同是亲兄弟,如今一个活不成,一个决意要死,他实在不知道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两行眼泪瞬间涌出,脑子空虚茫然,嘴里喃喃道:“一定是崔去疾,我要把你千刀万剐!千刀万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