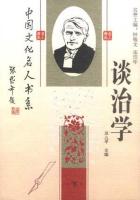一般认为,学衡派是一个远离政治的文化学术团体,有的学者相信“《学衡》的兴趣不在时评,电不在政论,它与政治、现实保持着知识分子理应保持的距离,此乃思想独立之本”。还有学者断言学衡派“只关注文化本身,而无力关注政治”。《学衡》杂志的确少有诸如“我们的政治主张”之类鲜明的直接论政的文章,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文化学术方面。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处于弱势地位,国内政治混乱不堪,国家的命运难以令人乐观。身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中,政治问题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正如胡适等人所言“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同时,受儒家“治国平天下”传统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有天然的使命感。因此,当时包括学衡派在内的知识阶层对政治问题抱以密切地关注和思考是不应当有所怀疑的。吴宓在编辑《学衡》第5期时,虽刊登张其昀撰《论刘知几与章实斋之史学》一文,但又“嫌其为考古述学之专著,无关国事与时局”。表明他不仅关注现实,而且愿意通过《学衡》杂志对国事时局发表议论。对于文化与政治,吴宓也没有把二者对立起来,他说:“(政治与文学)二者实关系密切。广义之政治,包含经济实业教育及国民之各种组织经营活动。广义之文学,包含哲理艺术社会生活及国民凡百思想感情之表现。政治乃显著于外之事功。文学则蕴蓄于内之精神。互为表里,如影随形。政治之得失成败因革变迁,每以文学之趋势为先导为枢机。而若舍政治而言文学,则文学将无关于全体国民之生活,仅为文人学士炫才斗智消遣游戏之资。是故欲提高政治而促进国家之建设成功,应先于文学培其本,植其基,濬其源。而欲求文学之充实发挥光大,亦须以国家政治及国民生活为创造之材料,为研究之对象,为批判之标准。更就狭义之政治与狭义之文学而论,征之中西往史,无分专制共和,凡在国运兴隆民生安乐之时,文学与政治常最接近而相辅相成。而当衰亡离乱之秋,则文学与政治率背道而驰,各不相谋。吾人望从事政治者毋蔑视文学,并望努力文学者能裨益政治。”当然,不同的知识群体和政治派别政治诉求方式不尽一致。有的直接针对现实问题设计明确的政治改造方案,并努力将其付诸实践,如国民党、共产党所为。有的虽远离政治实践,但积极论政,企图以这种方式来激发民众对政治的热情,进而影响政治进程。学衡派并非对政治不闻不问,《学衡》杂志的“通论”栏发表有少量政论性质的文章评议时政。此外,学衡派关于政治的见解大量地体现在他们发表的文化评论、学术文章以及译介的西方著述中。由于这些见解并非是全是有意识、有条理的完整表述,没有形成明确的系统的政治主张,只是表达了他们大致的政治倾向,因此我们将其名之为政治观念。
近年来关于学衡派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但关于学衡派的政治观念,似乎尚未有人言及。笔者认为,政治活动家(在当时主要是革命者)的活动固然是政治生活的主流,普通民众对政治进程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加强对这一时期一般民众政治观念的研究实属必要。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把学衡派看做一个与政治生活比较疏远的属于普通民众的知识分子群体来研究,尝试在了解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知识群体一般性政治倾向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知识分子阶层以及普通民众的政治观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的研究结论是学衡派具有大体一致的政治观念,但也由于学衡派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群体,没有纲领性的统一主张,诸成员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社会地位又各不相同,他们的政治理念必然有差异。笔者的注意力将主要集中发掘学衡派普遍性的理念,同时尽量兼及差异之处,以求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
一、对现实社会政治的认知
促使学衡派形成的最直接动因是批判新文化运动,因此他们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极其激烈地批判现实的姿态。他们在讥评时政时,几乎对现实社会政治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言辞之激烈程度,丝毫不比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相关言论逊色。在学衡派的眼中,北洋时期的中国是一幅无官不贪、百业俱废的图景:
辛亥革命,为亘古未有之大事业,然真正革命家,牺牲生命,图灭满清者,太半已死于黄冈之役。其奔走运动,迄民国成立,不变初志,确然树立民治主义者,殆无几人。其余侥幸因人,遂尸创造民国之功,擢党费,猎勋位,购洋房,拥姬妾,大失国人之信用……民党之分子既复杂矣,又与官吏盗贼,互相利用,如赵秉钧、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陆荣廷、徐宝山、王天纵等,竞挂民国之旗,瓜分满清之遗势。而穿插点缀于其间者,又有所谓名流、政客、学生、新闻记者,以到各地方之绅董乡棍地痞流氓,淄渑混淆,玉石错杂,争攘叫号,以谈民治,或以武力,或以民治,或以阴谋,或以金钱,或以清党,翻云覆雨,光怪陆离,以讫今日。
中国大多数人皆不仁。不仁者,非必如袁世凯、陆建章、陈宦、汤芗铭,杀人如草芥,而后谓之不仁也。心视全国人民利害休戚漠然不动其心,而惟私利私便是图者,皆麻木不仁者也……例如比岁北方之赈,南方之赈,皆以为灾民也。而彼承办之官吏,目睹析骸易子日曷死溺弊之惨状,曾无所动其心,而反因缘为利,时时挪移赈款,以供黑暗运动弥补亏空之费,是尚有丝毫之仁心乎?其他地方慈善事业,号为救灾恤患者,无往非丛弊之渊薮。以鳏寡孤独废疾之养,充董事员司挥霍浪费用者,比比也,无官无民,皆是一丘之貉。故国家不能自立,地方亦不能自治……今中国大多数之人惟知有利,举国上下,汲汲皇皇,惟日不足者,求得利之机会耳。革命一党之机会也,伟人攫资若千万;独立一机会也,财神攫资若千万;组党一机会也,政客攫资若千万;办报一机会也,流氓攫资若千万;买收议员一机会也,掮客攫资若千万;乃至兴水利,倡实业,修道路,办学堂,讲自治,充代表……存在皆谋利之机会也。往者官奉微薄,不能尽责人以廉洁,今则官奉倍蓰什伯于前清矣,而衙署机关局所上下之舞弊赚钱,亦倍蓰什伯于前清焉。县官征租,征租有利焉;委员查烟,查烟有利焉;警察捉赌,捉赌有利焉;而厘卡税局无论矣。银行停兑,股票交易投机之业,顶踵相望.买卖议长,选举议员,运动之事,公言不讳。
柳诒徵笔锋所至,从官府到民党,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军阀,从高官大吏到乡棍劣绅,无一不在其痛诋之列。在他看来,民国的吏治,已是腐败到了极点,现实政治实在是没有任何可取的地方了。
除了抨击政治的腐败外,学衡派将当时国势不振、百业萧条归咎于各级官吏的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却又夸夸其谈、沽名钓誉,他们对此有生动的描写:
言政法,则仅知高谈法理,而于判例成案,则罔知究心。言外交则仅知宴会跳舞,而于条约章程,则索之高阁。言工程,仅习于说帖条陈,而于机械土木则不知应用。言经济,则仅知搜款借债,而于节流开源、勾稽综核之烦,则不暇措意。言军政,则仅习于要挟叛变,而于逻侦攻守、步骑炮工之术,则无所用心。言文章,则仅知源流派别,而于书牍笺启、庄谐骈散诸作,则不能秉笔。乃至言改革,倡革新者,亦仅习于开会演说,行列示威,而于实际工作,进行步骤,则更不复问讯……噫嘻,此中国二十年来,所以新政繁兴,新潮迭起,膠膠扰扰,每下愈况,寸效未收,而百弊从集也。
学衡派抨击时政的这些言论,不可谓不激烈。而学衡派却是以保守而著称于世的。由此可见现实政治之不可收拾,已经成为当时的知识界、舆论界的一种共识。相应地,各种政治力量已经失去了知识阶层的信任。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北京政府上演的是一幕幕政治闹剧:府院之争、贿选议员、贿选总统。其影响不断衰微,其名誉也在一次次的政治风潮中变得一文不值。至于各地军阀,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各个阶层的认同,“人人诅咒军阀,它(指军阀)自己亦应和着诅咒军阀。它可以否认它自己的合理,承认它自己是社会一危害物”。军阀自己对自身存在的正当性都不敢确认。多数军阀都做过“废督裁兵”的姿态,固然是为了应付舆论,然既已做出姿态,就意味着他们也承认督和兵的存在是不正当的,督应该废,兵应该裁。知识界对当政者的认同已经丧失,又没有一种整合性的中心价值,知识界的分化就势在必然。几乎人人都在寻求出路,零星半点一知半解的理论(主要是来自西方的),就会产生一个主义,一个团体。在这林立的团体和形形色色的主义中,陈独秀、胡适等人倡导以西方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观念、价值,逐渐取得了主导性的话语权力。而学衡派所处的位置无疑是十分尴尬的。他们作为一个学派立论的基点就是发掘和论证中国的优越与价值,而社会政治现实如此不堪,他们只好反而求之于文化和传统。也就是说,现实中已没有什么可以能够保守,他们只好在文化中寻求能够保守的东西。少年时的吴宓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世事如此,可愤者实多,顾徒愤亦又何益,亦安得尽愤之耶?”已经隐约感到世事之不可为而要求自己“不愤”。他又说:“吾辈于世不能无愤,然当愤其远者大者。”所谓“愤其远者大者”,应该是他日后疏离于现实政治,寻求超越性的文化保守的思想端倪。
学衡派在政治上的发言不多,即使有一点微弱的声音,在激烈地否定现实这一点上,也与主流话语形态趋于一致,这可视作当时中国政治思想、政治运动在整体上呈现出的激进景观的一部分。余英时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我们发现政治的现实是没有一个值得维持的现状。所以保守主义很难说话。保守主义很难有什么立足点。你能说要维持袁世凯的独裁甚至帝制吗?你要维持后来的军阀体制吗?在没有现状值得维持的情况下,就只有另外一股力量,就是激进的力量拼命的发展。基本上中国近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
学衡派也主张变,他们对中国政治变革的方向有自己观念性的认识,这一点将在后文详述。
相对于学衡派对国内政治的激烈批评,他们对于外国列强的态度倒是比较独特的,也更加耐人寻味。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一幅民族主义高涨的历史情景,“打倒帝国主义”成为最具时代影响力的口号。国共双方在南方发动的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还有旷日持久的非宗教运动、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和修改不平等条约运动等大规模的反帝群众运动。但在思想界,在如何看待外国与中国关系问题上已经出现分歧。1922年,胡适撰文断言“现在中国已经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哪怕国际侵略的噩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地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胡适的言论颇能代表一个方面的意见。他们认为,列强以武力征服统治中国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民族危机的主要原因不在国外,而在国内政治的不上轨道。胡适的这一结论在当时的语境中已经属于不和谐音,至少已经不能像当年他提倡白话文那样一呼百应了。而以批判胡适为己任的学衡派在这个问题上却与胡适略有相似之看法。学衡派的态度尚不及胡适那样乐观。吴宓留美期间,曾对在列强觊觎下中国的命运表现出极度的忧虑:“居外国,究世界事,则比较回环,益见中国之可忧。以西洋各国之鹰瞵虎视,其人之雄健富厚、强悍精明,大势已成。我以一所当,犹不止十。况纷扰破坏,日行自残;江河益下,人心尽死。”故此他悲观地认为:“若设身局外,就事论事,则中国之终归覆亡,亦意中寻常之事,毫不足奇者也。”1921年吴宓回国后,因国内混乱政局之刺激,遂有“外人取割在即”的想法,甚至预计是年年关,必将“大局溃裂,全国鼎沸”。但仔细考察学衡派的著述,就会发现在多达79期的《学衡》杂志中,再难以找到诸如此类关于外国以武力侵略中国,造成中国沦亡的议论。这固然是因为《学衡》很少涉及政论,但也说明这不是学衡派主要担心之所在。此外,对于广泛动员了全国各个阶层的人参与的两次群众性的反帝运动——非宗教运动和五卅运动,学衡派表现并不热心。《学衡》杂志第6期专门刊登了4篇文章讨论非宗教运动,对这一运动持反对态度,认为信仰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是必要的。柳诒徵提及五卅运动时,认为“沪案之发端,乃无意识之冲动”,“其所以风动全国,则以政府军阀与学生合作之故”,‘不以为然的态度溢于言表。对这样声势浩大的排外活动不甚认同表明学衡派不把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征服看做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危险。
学衡派更为注重的是中西碰撞中中国文化生死存亡,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一问题上体现得十分充分。《学衡》杂志大量的文章都力图证明中国存亡绝续的根本不在政治,而在于文化。柳诒徵通过诠释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阐明了学衡派这一根本主张,他说:
顾氏有一语,为今五尺之童子皆能知而诵之者,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顾氏之言,实与今之诵者语者之用意绝异。
《日知录》卷十三: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日: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盖顾氏谓礼义廉耻为天下之公器,天下人皆当保之,宁亡国不可亡此,非谓天下兴亡,人人皆当干与,以此为匹夫之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