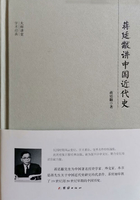9岁时到罗享庭先生家中学习,开始作文。10岁就开始学习英语。每天抽出一个小时到一位名叫黄子甲的先生跟前学英语。后来,这位先生去美国留学,把他推荐到其堂弟黄西先生门下学习,仍是每天学一小时,每月的酬金为三块银元,够一个月的伙食费。
从11岁到14岁,母亲为他聘请一位本家叔祖黄儒冕老秀才教他学习国文。他读《四书》、《诗经》、《书经》、《左传》、《礼记》、《古文析义》、《古文释译》、《千家诗》,还阅读了《通鉴辑览》等典籍,并练习大小楷,写些律诗。13岁时才接触数学,由英语老师黄西授课。他学的是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的算术和中学一年级的代数。那时,代数符号不是今天的A、B、C、D和x、Y、z,而是甲、乙、丙、丁和天、地、人。他学数学也很用功,每天让母亲半夜两点喊他起来演算。
1922年,13岁的黄席群进入九江同文中学旧制二年级读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校园就在风光秀丽的甘棠湖畔。人学考试很简单,写一篇作文,算几个数学题,外加英语口试。考作文和数学都不成问题,只是考英语的美国教师胸部毛烘烘的,吓坏了年少胆小的黄席群,害怕得几乎答非所问,不过总算过关了。这里的英语教材是MY COUNTRY(我的祖国)实为美国“公民”课本。黄席群的英语成绩开始不及格,期末一下子考了89分,到第二年,美国专家来学校进行智力测验,试题全是英语,他考了全校第二名。]923年改革学制,分为初高中各三年,他那年升入高中。高中一年级时开了生物课,教材是东吴大学美国教授编写的,英文课本。期末考试,黄席群答卷一口气写了满满12页,深得老师赞赏。
八个第一进金陵
从小学到中学,黄席群发奋读书,非常用功,学校组织共和会,他当教育部长。但他的健康却不太好,6岁时吐血,14岁时又吐血,几乎活不大,有位中医都说这孩子活不过20岁。高中毕业前又患了天花,不得不休息一个月,但他自修课程,最后还是考了全班第一名。那时候家里有母亲、庶祖母、奶妈。因奶妈的丈夫是个乞丐,儿子夭折,一直住在他家。一家人靠父亲留下的保险金的银行利息维持生活和作为教育费。他记得,母亲每天记账,一斤猪肉2角8分钱。过年的时候,负责管理存款的父亲的生前好友陈叔通先生加寄100元,母亲用10元钱买来一担(100市斤)鱼,腌制成咸鱼慢慢吃。
1926年,黄席群高中毕业,由于四年八个学期连续成绩第一,被保送到金陵大学。他怀着工业救国的想法选择了化学专业,不料因身体虚弱,进化学实验室对氨气受不了,就只好改修历史,辅修国文。
学校一个月的伙食费是3块银元。抗战前夕,南京市场上的鸡蛋一元1 00个。经济情况比较富裕的同学们嫌学校伙食不好,在外面包伙,一个月花费9元,顿顿有荤,米饭随便吃。席群读大学二年级时,与比他大四岁的表姐结婚。因为从小是私塾的同窗,交往频繁,感情甚笃。那年他虚岁二十。
金陵大学实行的是美国式的通才教育,学习除主辅修课程以外,还必须选修不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教师多为外国人,即使是中国教师,也用英语讲课。讲授《世界通史》的是美国人M·s·Bates(贝德士)教授。在这里,黄席群凭着惊人的毅力和孜孜不倦的求知态度,把自己充实成了一个饱学之士。
1931年春,席群从金陵大学文学院毕业,获文学士学位,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同时授予文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在九江儒励女子中学任教,先后讲授过国文、历史、地理、英语。1933年至1934年,到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中国史一年。回九江后仍在儒励女中任教。曾在金陵大学理学院当过一学期秘书后又去广州学海书院任史学助教。1934年又到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任讲师兼任秘书。其实他18岁时就给校长当翻译。
在此期间,金大农经系美籍教授卜凯(J·L·Buck)主编《中国土地利用》分正文、表格、地图三部分,请黄席群负责翻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是当时研究农村经济者必用的参考书。卜凯是赛珍珠的丈夫。
“谁叫黄某有一个好父亲呢!”
1937年,抗战军兴,随校由南京迁成都。此时黄席群已有四个孩子,加上母亲和庶祖母及两个佣人,十口之家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维持。本来应发工资115元,此时发国难工资80元。在南京时住花园洋房,实在难以维持生活。1936至1937年他曾于夜间在德国海通社南京分社兼任编译工作。1938年,黄席群的同学陈云阁自重庆写信给黄席群,说是海通社已在重庆成立分社,由陈云阁任总编辑,陈需要一个助手,就请席群去重庆,月工资250元。于是,时年29岁的黄席群到了重庆。
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海通社的人员也到中央社的防空洞去躲飞机,日本飞机炸了海通社办公的地方和黄席群的宿舍,他却没有被炸死。就在这一年,席群的母亲去世了,终年58岁。母亲走了,但母亲半夜两点喊他起来算题的那一幕,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
转眼已到1941年的夏天。陈云阁因请假迟到,德国人对他大发脾气。陈愤然辞职,黄席群也就不干了,在家赋闲,经济拮据。陈云阁每月派人从铜梁送来一担米,还约几个同学和朋友每人赠他一两黄金,渡过难关。
半年后,经人介绍到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总社任职,一上班就拿月薪300元。他先后在总社英文部当编译,1943年升任编译部副主任,选译国际新闻。后来又调任中文编辑部副主任,1946年晋升为编译部主任。在中央社,黄席群的业务能力出类拔萃,因而也引起某人忌妒,说:“谁叫黄某有个好父亲呢!”
中央社的月薪300元,不算少。但此时的席群一个人供养着20口人的生活,还供妻姐的孩子们读书。因人口多,花销大,还得在外兼职挣钱。他每天用半天时间干完中央社的工作,再到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刘尊棋那里干半天。
此时,他的兼职不止一处,还为中英庚款董事会任股长,除管吃饭外,一个月薪金120元。此外,他兼编一份刊物,即杭立武主持的世界学生组织主编的《世界学生》月刊,一个月补助100元。中午他不休息,为设在重庆的金大理学院写应酬信。中央社对门有个报社,他利用晚饭前的2小时为该社剪报。他还翻译小品文,译一万字,酬金30元。
人们都说他才华横溢,自强不息,精力过人。但从早到晚,来去匆匆,马不停蹄,回到家也还是疲惫不堪。几十年后,他感慨地说,虽然那时候拼命干,很苦很苦,但确实锻炼了自己。
编发抗战胜利消息的那一天
黄席群在中央社总社干了九个年头,实际为七年零四个月。其间令他最难忘的是编发抗战胜利消息的那一天。他时任中央通讯总社编译部副主任,本部翻译国际新闻电讯,即本社驻外国记者拍回的专电及中央社合作的英国路透社和美国合众社的电讯稿,也抄收翻译日本同盟社和德国海通社的电讯。
1945年8月10日下午,电务部刚抄到日本同盟社最急电。抄电报的人认得上面的FLASH这个字,“急”,知道内容十分重要。值班编辑潘焕昆一看之下,高兴得大声欢呼起来:“我们胜利了!日皇裕仁宣布接受同盟国要求,无条件投降了!”当时在重庆,潘是首先获知这一喜讯的少数人之一,潘非常激动:“这是我的一项荣耀,毕生难忘!”潘以最快速度将电文译成中文送交编辑部和英文部处理,发稿贴号。同时以电话向各方报喜。不久,编辑部送来两瓶酒以示庆祝,灌了潘焕昆满满一杯。潘说:“这准是本社及得知这一消息的其他部门和市民们送来的酒。”不一会儿,外面便响起一片鞭炮声。
黄席群是编译部副主任,知道抗战胜利喜讯的时间仅比潘焕昆稍迟几分钟。他说:我的欢愉之情不亚于杜甫的著名诗句:“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他清晰地记得,太平洋盟军接受日本投降的盛典是9月2日在美国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盛典由太平洋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主持,参加者有美、英、苏、澳大利亚、荷兰等国代表。中国代表是军令部长徐永昌,日本政府的代表是外务大臣重光葵和日本大本营代表梅津美治郎参谋长。盟军特邀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总编辑陈博生参观受降礼,中央社驻东京的战地特派员曾恩波等三人也随同登舰采访。舰上的新闻记者事先商定,礼毕即由包括中央社在内的世界五大通讯社利用该舰的无线电话设备把各自的新闻电发出去,并以抽签方式决定先后顺序。中国很幸运,曾恩波拔得头筹,他高兴得跳了起来。因此,中国记者的这则新闻最先传播到全世界。重庆的大规模游行庆祝是在9月9日,即何应钦在南京正式接受冈村宁次代表日军投降之日。市民欢喜若狂的情景,黄席群至今记忆犹新。
为四九年国共和谈起草电文
黄席群在中央社才能出众,但他自己始终谦虚谨慎。有一次编译部进行业务考核,让编辑们翻译《东京归来》一文。总编辑看了黄席群的译文后,把他从编译部办公室叫出来,说:“你翻译的文章,社长和我都看过了,决定让你当编译部主任。”席群却说:“我看这样吧,让年轻人当主任,我还是当副主任好了。”
1948年,美国旧金山成立华文报纸,席群很想去。因为他父亲是在那里遇害的,自己一直想去凭吊一番。然而社长和总编辑没让他去,打算提升他为中央社秘书,相当于总编辑一级的行政人员。他突然想起小时候算命先生说:“这孩子聪明,只能当个秘书长。”而此时他的两个弟弟赴德国留学去了。
时任水利部部长的钟天心,在1949年1月的一天夜间,打电话给中央社的秘书,说要找黄席群谈话,当时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平代表团要到北平同共产党和平谈判,要找一个中英文都好的翻译,黄的朋友王悟仁(水利部次长)想到他符合这个条件,便推荐黄席群去当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中英文秘书。那天是个下雨天,钟也不问他是不是国民党员,立即同意他担任这个职务,同时派他为水利部一专门委员。于是,他每天和代表团副秘书长左恭共事。代表团不给车费,他每天就只好自己花钱,坐黄包车去和副秘书长等候中共方面的答复。谁能想到,迟迟没有答复。黄席群便奉秘书长钟天心之命起草一份电报给中共当局说,请“贵方速派代表进行谈判,否则内战的责任由贵方负之”。
后来中共不同意国民党的内政部长彭昭贤充当代表,认为他是c.c.分子。因此代表团改组,钟天心也不是代表,所以黄也去不成北平。全国解放前夕,中央社准备迁往台湾。黄席群问总编:“我去不去?”“你是骨干,怎么能不去呢?哪怕将来是流亡政府也会带你去。”
他本来是应该去台湾的。由于他从中央社的消息中获悉他父亲的好友陈叔通先生已到解放区共产党方面,他就当机立断留了下来。1949年2月,他离开中央社回九江儒励女子中学教书,在故乡迎接解放。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1950年的黄席群,是个十口之家的户主,8个女儿,大的18岁,小的才4岁。如此沉重的家庭重担靠一个穷教师的工资实在难以维持。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大公报社的年鉴上发现,表弟盛彤笙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副部长兼兰州国立兽医学院院长。盛彤笙是留学德国的兽医和人医的双博士。席群立即写信与表弟联系,谈了自己的想法。表弟很快回信,聘请他为兰州兽医学院副教授,教国文和英语,兼任院长办公室秘书。还汇来路费300元。此时他的心绪恰如陶渊明的诗句:“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亲朋得知他要远走兰州,一个个愕然吐舌,劝他不要走。“纷传古金城,荒凉不可说。开门但见山,举目无青物。未晡即昏黄,风尖慑魂魄。”这使他“临行心恻恻”。但他自信自己能吃苦,能在西北干一番事业。
1951年2月,黄席群携眷踏上了西行的旅途。离开九江前,到父亲坟上向父亲告别。
到兰州后,在小西湖的兽医学院安了家,这一安,就是半个世纪。20世纪50年代初的兰州和九江传闻的情形差不多:“四周林木稀,一雨泥涂塞,霜秋起狂飙,飞沙压城黑。”而他却满腔热情投人教学工作。后来,因为要学习苏联,全院教师都突击俄语。院方先派秦和生教师和张邦杰讲师,赴西北农学院突击学习俄语,返校后让黄席群脱产学习一段时间的俄语。他便刻苦学习俄语,一天可记300至400个单词,很快适应了教学。并且完成了任务。然后与专家合作翻译了200余万字的寄生虫学、内科学和兽医产科兽医俄文教材。还一度兼任兰州大学英语副教授。
然而,好景不长,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他被抄了家,理由是怀疑他家有枪有蒋介石的像。结果什么也没有。又批斗他:“为什么没去台湾?”这期间仍让他翻译书稿,但不许本人署名。
1957年,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各界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黄席群当了鸣放委员会委员,在鸣放会上“大放厥词”,说人事处是阎王殿,不执行毛主席德才兼备的人才政策,只红不专。说一个出身好而学习特差的女教师,不应从事教学。还说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云云。又反对迁校(将兽医学院迁到武威黄羊镇),因此他被打成了“极右分子”。
老黄可能叫狼吃了
他随学校迁到黄羊镇,整天劳动,静候处理。就在1958年8月的一个星期六,正是发工资的日子,突然宣布:“省委通知,黄席群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从此,工资也没领上,家小都早回九江去了。幸好,两个大女儿已先后大学毕业有了工作,连大女婿也为家庭分担起“大养小”的任务。
有个叫孙玉的党员干部背着黄席群的一只箱子,送他上了火车,一直往西走。到酒泉车站下车,步行30里,来到个叫夹边沟的地方。这里原先是个劳改农场,现在把右派分子集中到这里来劳教。他到达时看见人们正在搬砖头。满目戈壁滩,盐碱地,他去办公室报到,被编到农业队挖排碱沟。这一天是1958年8月10日。
正值夏收季节。黄席群第一天割麦,不知道怎么捆。几个月后只听见场长作报告时说,你们干一年打的粮食只能够全场的人吃一个月。劳动评五等,分别为红旗、紫旗、黄旗、白旗、黑旗。他劳动特差,稳拿黑旗。收了麦子,又叫他们去挖排碱沟。他每天一顿饭发给三四两馍,工资一个月5角,表现突出者最高发1元、1元5角或2元,实际上一分钱也没给大家发。黄席群靠他的二女儿按月汇去6元,作零花钱。
他从小到大身体一直瘦弱,到夹边沟时已经是49岁的人了,年近半百,从来没有做过这么重的劳动。挖排碱沟,有人一天能挖8立方土,他只能挖1立方。挖苦苦菜,有人一天挖90斤,他只能挖9斤。
他在这里劳动改造了将近一年,其间遭遇三次惊险的生死关头,但每每逢凶化吉,大难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