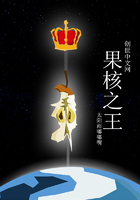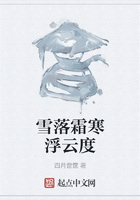这座城着是华美而庞大,同样一座庞大的城。北京给予他的,是笔直,正规,宽阔,似乎在那座城,他就必须遵循着一些规矩,去圆满地行走,不得有误。而港九之地,他一下找到散软的感觉,那是他二十八年,都未曾尝受过的松弛,如同冰冻多年的一块鸡肉,突然遇到了高压锅的蒸气,他迅速地就瘫软下来,甚至,他感觉自己即将肉骨离分。
满眼满耳的叫嚣,都是他不太熟悉的粤语。似懂非懂,没有儿话音,不干脆,却也可以铿锵。没有轻闲而又友好的搭讪,亦不见胡同口忙碌的阿姨,甚至看不到冶艳如梁宝贵。
他希望自己的一口正宗京片子,从此消失怠尽,从而也可以铿锵着全然改换。
香港,多少传奇多少春,他离开它又回归它,这里有他最原始的恩仇,也有他最根源的水土,他不至于生疏。他希望,这二十年的失散,不过是黄梁梦一场,醒过来的他,依旧有情有意有生有息,只是,他希望一切,都是用另外一个载体去享受。
他想到隐名埋姓。
这座城里,除去付理斯这个青梅竹马,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这失踪的20年里,没有任何香港这边的人与他们联系。他不知道自己的外公外婆在何处,这些重要的事情,反而是他的母亲从来不曾提起的。她所有的话题,都与那个该遭天谴的男人有关,他甚至知道那个男人的腰围和鞋码,却不知道母亲的平生,她出自何门,这些,都是他无比好奇又不敢擅自询问的。他怎么敢在一个女人埋怨的时刻,去打断她,而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说,他外婆的姓氏。
他不再是宁林。他没有往事。香港便是他的城。他要在这里,改头换面,他不要再继续联系付理斯。他预备在半年之后,将这笔款项,车的款项,汇给付理斯,并且会在这笔钱上面多付一些,算做利息以及情份,他不是不愿意再与他交往,只是,有他的提醒,他永远不会过新生活,他会一直明白自己童年少年青年的脉络,那是他无法忍受的。其实,更重要的,是梁宝贵。
梁宝贵太危险。她是28年唯一能够引起他慌乱的女人。她却抬眼不见他,对他的存在不屑一顾。--只是这样,他便已慌乱,他料想不到再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他要把生活里一切潜伏的闹腾的因素彻底掐灭。惟剩下一些安静生长的绿色,一片一片,安全地将自己包围起来。宁林很明白,他只适合一个人生活,之前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日月,便是牢笼,他只适合一个人,安静地,波澜不惊地生活。比如现在。
闲时喝酒,忙时忘记喘息。节奏控制生活,一片大好。
他将丰厚的积蓄分批分领域做了一些投资,地产,股票,娱乐……每个月可以有一些钱财滚滚飘来。他拿了一部分生活,一部分置业,一部分开展新投资,剩余的,还做了一些慈善捐献。无留名的,默默捐献,他甚至有打算在30岁的时候,确定一项信仰,然后为此信仰倾尽。比如,修建一座寺庙,或者,修建一座教堂。
对于信仰,他向来是满怀敬畏。他熟读过一切的经书,圣经,佛经,古兰经,他甚至在研究占星和周易,总是在这种看似虚幻的世界里,他的灵魂得以平安,只是,这样的依赖并非好事,他却是在一些短暂的平安之后发现,任何教义,他都接受,这在宗教里,是万不可赦的。
他惟有焦灼着,一边贪恋着平安的喜悦,一边逃潜着罪恶的追博,他就这样混沌地,走到现在。真是清白。二十八。二十八尚为青年,他却倍感孤老。唯求平静,平安,平顺。
于是,梁宝贵更为孽障,他不能不防备。
----伍。
约会一名潘姓女子,他没记住名字。
业务上面的一些盘丝关系,她对他倾慕不已,当然,他年轻,阔绰,沉稳又清白。只要确认不是基佬,哪个女人不会情慕他。
潘女离异,前夫是地产名流,舍给她大片楼盘,于是她变成地产界名女。
除了男人,她样样不缺。名车名房名气,奢华富贵,并且年轻--她不过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