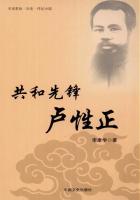苏雪林的《郁达夫论》显然是极不公平的,所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她攻击郁达夫的作品是“****文学”,是“作者自己有神经病”,“艺术手腕过于拙劣,除了自己的经历的事外便想象不出来”。“自己神经病,便叫小说中人物也个个患着神经病。”“郁氏除了性的苦闷之外又好写鸦片、酒精、麻雀牌、燕子窠、偷窃,诈骗以及其他堕落行径,所以人家给戴上颓废作家的头衔,他也就俨然以中国的颓废作家自命了。”这些东西亏苏雪林如何想得出来!这个女巫,阅读郁达夫的作品时不知为什么,没有见到郁达夫反映的性的苦闷,生的烦恼,对军阀的痛恨,也没有见到作家满腔热情的爱国主义,而只见到那些肮脏的词句!苏雪林在一万多字的评论中,没有分析郁达夫作品的一点长处,特别着眼于攻击郁达夫的《沉沦》、《她是一个弱女子》、《迟桂花》,她攻击郁达夫的《沉沦》只充满着“肉”的臭味,丝毫不见“灵”的馨香。她认为主人公的自杀与中国的不富强没有关系,否定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她也攻击郁达夫的牢骚充满了女人气与孩子气,攻击他是“名士糟粕的糟粕”,“只不过是小丑在台上窜来窜去扮丑脸叫人好笑”。是一个“元气被酒色断尽的的作家”。苏雪林没有忘记攻击郁达夫“每以革命的文学家自居”,“向读者介绍自己荒淫颓废的生活,鼓励读者去提刀杀贼,鼓励读者去赴汤蹈火为人类去争光明”。宣称郁达夫“著作运命的末日已经来临”。“郁氏那么散漫松懈……的作品,渐渐有了被淘汰的倾向。”同文中,她也攻击郭沫若为“夸大狂,与领袖欲发达”。攻击郁达夫“赤裸裸描写色情与性的烦闷”,攻击评论郁达夫作品的评论:“总之,达夫的初期的创作背景,性的苦闷是其骨干,这种苦闷自然是郁达夫个人的,每一个人在青年时期从生理的发展,必然会发生这种作用,而像郁达夫这种病态,在一时成为青年苦闷的典型,这种评论是违心之论”,“是青天白日闭了眼睛在说梦话!”……
郁达夫万万想不到,那个投身于以屠杀人民为国策的政府当局的苏雪林会来这一手!而且是这么无耻。他深知,这个名叫苏雪林的女人的文章之恶毒也完全是冲着左翼文化来的。而且郁达夫知道,上海的正直的文学艺术家,对专门造谣生事的官办《文学月刊》是不屑一顾的。苏雪林的文章无非是像上海的《社会新闻》一样,别有用心。上海现在不是在禁绝一大批的作品作家么?苏雪林的作品可以在南京官方的右翼杂志上大行其道。也不过是因为多重原因,郁达夫的书没有上禁书的名单,而苏雪林的泼妇骂街恰恰是对当局向左翼文化围剿的一种补充。苏雪林是恨不得将郁达夫的书让当局禁绝而后快的。郁达夫做梦也想不到自己避秦到了远远的杭州,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女巫打上门来。他看到,那个女巫的文章完全是一个泼妇的骂街,他愤愤不平!
林语堂的《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约郁达夫撰写《自传》,郁达夫曾经予以答应。北上之时,他已拟就腹稿《我的梦,我的青春》,可以连续发表卖钱。郁达夫在写这《自传》之前,恰恰是这投靠政府的女人给了他写自传的灵机。郁达夫在自传发表之前,先发表了一篇《所谓自传者也》的自序,拿到《人间世》上去发表,对那个“女作家”予以痛击。郁达夫一开始就讲了自传的体裁,以奥古斯汀、卢梭等人的自传,并说明自己写《自传》的缘起,他写道:“最近,更有一位女作家,曾向中央去哭诉,说像某某那样颓废、下流、恶劣的作家,应该禁绝他的全部书、流之于三千里外,永不准再写小说,方能免掉洪水猛兽的横行中国。方能实行新生活以图自强。照此说来,则东北四省的沦亡,贪官污吏的辈出,天灾人祸的交来,似乎都是区区的几篇无聊的小说所致。”“生在这个世界上,身外的万事,原都可以简去,但身内一个胃却怎么也简略不得。要吃饭,在我就只好写写,此外的技能是没有的。于是乎,在去年今年两年之间,只写下一些毫无系统,不干人事的游记。但据那位女作家说,似乎我的游记也是一罪,事到如今,只好连游记都不写了。”“虽然专写自己的事情,由那位女作家看来,似乎也是一罪。”郁达夫的猜测没有错,那位女作家评论他的文章是别有用心的。也正是苏雪林向当局卖身投靠献了一份厚礼。在文化围剿斗争激烈的一九三四年,那些投身于当局的右翼文人大部分是低能的,挡不住左翼文化的汹涌潮流。
而这位出身于法国女高师的女人的一篇《郁达夫论》,是向郁达夫开刀,把评论论及整个创造社及整个左翼文化。怪不得当局把这女人当做“国宝”,其实此女人是一个早已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的货色。郁达夫的自序完全剥掉了那个女作家一副向官方告密的嘴脸,使苏为正直的作家所不齿!苏雪林对郁达夫的攻击,也正证明他在文坛左翼的重要地位。
《申报·自由谈》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发表作品,郁达夫没有固定的职业。郁达夫不得不继续自己正常的创作,而主要发表在《论语》、《人间世》、《东南日报》副刊、《文学》月刊、《太白》、《现代》上面。那些刊物表面看来,政治色彩不那么浓厚,这个世界对于民众来说太难了,沉默难,不沉默也难。人生没有太多的权利,路人侧目,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关心国事的权力,莫谈国事……
郁达夫不是一个喜欢沉默的人。他要为民众代言,他常常这样做。
现在他开始写作《自传》,陆续写下去,从这一年的十月份写起,直写到翌年的四月,先后写成《悲剧的出生》、《我的梦、我的青春》、《书塾与学堂》、《水样的春愁》、《远一程,再远一程》、《孤独者》、《大风圈外》七章,那是他自己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写照,也是对自己生活的一个总结,也是对那个恶毒攻击他的恶女人绿漪女士——右翼文人苏雪林的有力回答。
郁达夫此时大都为小品文世界写作,投稿于《论语》、《人间世》,无形之中,壮大了小品文的力量。鲁迅先生此时也由于当局的文化围剿,文章已很少能在一个固定的刊物上发表。《自由谈》随着黎烈文的辞职,鲁迅在那里写得少多了。鲁迅虽然依然撰稿,他的杂文依然文笔犀利,但只能散见于各种报刊,而且大都还须采用化名、别名。因为他与林语堂、邵洵美、杜衡、施蜇存等有过过节,是从来不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的。郁达夫不同,他与林语堂、邵洵美辈都是好朋友,且这些刊物大多是政治色彩较淡,对当局也存在着种种不满,郁达夫正中下怀,他在这几个刊物上发表了众多的文学作品,虽然与鲁迅依然私谊甚好,可随着居家遥远,交谊有别,他们的感情已是逐步有所疏远了……
郁达夫的周围存在着一大批的文化人,这些人政治色彩不太浓厚。
大多为鲁迅称为第三种人,但人各有志,这些人在郁达夫的眼中也是真正的文化人,也是够朋友的。
十月金秋,天气高爽。郁达夫正担心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可北京大学的王文伯来访,准备与郁达夫跑跑两浙的山水,郁达夫正中下怀。那正是中秋之后,是旅游的大好季节,何乐而不为?况且他们只两人,浩浩荡荡的旅游团体,对于旅游来说,其实并不怎么样,最是朋友二三,来去自由,观赏山水,才是旅游的最佳境界!
因为杭州至建德的公路已经开通,郁达夫与王文伯在遍游西湖之胜之后,便想到富春江、桐江一带旅游。王文伯是东北人,当年与徐志摩也是好朋友,他们交往不少。王文伯交游不少,去欧美日本游学四年回国,就是在我中华各省也是游踪处处,五岳匡庐都是去过的。这个银行家仰慕两浙山水,尤慕这富春桐江一带。从古籍上看,那是中华旅游的黄金水道,唐人早已把那最为优美的山山水水都写遍了。李白、孟浩然还有罗隐等人都在那里留下游踪,那里有东汉严光先生的钓台,有元朝谢翱的游迹,有药圣桐君的庙宇,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引力甚大,也要去看看郁达夫的老家!
郁达夫当然乐意得很,他从公路局借来了汽车,直上富阳鹳山,在郁达夫家的松筠别墅里面对富春大江,开窗南望,面对定山,江帆点点,秋光融与,朋友登山好一阵感叹。他们一路游览了桐君山,的确又去了严子陵先生的钓台,但见有许多名公发出募捐启事,预备为严先生修理重建祠宇了。郁达夫很痛快,好书不厌百回读,好山好水不厌百回看,虽生在富春可对这里的山水倍有感情,富春山水天下少啊!
郁达夫与他的朋友作了半个月的浙南游之约,浙南山水天下无双。
他身居大学路,与之江大学不过数步之遥,与省立图书馆也不过是邻里。平时有事无事到图书馆里去翻阅图书,近段时间他更是平空里去研读浙东浙南的地方志书,什么会稽丛书呀,天台山志、天台山方外志呀,什么雁荡山志、温州府志、处州府志、仙都志呀什么的,一律都看,他与王文伯约定,横渡钱江,过山阴会稽,经新昌,探望天台山,游览名扬天下的雁荡山,然后再驱车游温州江心屿,控青田石门洞,饱览三十六洞天的仙都山,然后再游金华兰溪再回富阳杭州,这汽车自然可以向省公路局去借,并且借好了一辆雪佛莱,车号是五。九号。
临出发的前一天,王文伯到场官弄达夫家来,遇着王映霞就对她说:
“明天,达夫与我一起扮作刘晨、阮肇,合唱一出上天台山的戏了,你怕也不怕?”
那当然是远古的故事。这一次王郁二位朋友一起上天台山,与当年人山采药的刘阮有几分相似吧。
十月二十三日,郁达夫与老朋友渡过钱江,那时还没有钱江大桥,在西兴等到了向公路局借来的汽车,向东行驶,他们一路过绍兴地面,知道这绍兴有柯岩、兰亭、龙山禹穴、东湖六陵、吼山,他们相约了日后再来游。径直驱车经上虞,沿曹娥江,经嵊县、过剡溪、人新昌,到达天台县界,只见山转峰横,清溪水绕,进入山中都不见他们曾经远远瞟见的天台山主峰。郁达夫随口吟出了两句诗:
山到天台难识面,
我非刘阮也牵情。
他们住在国清寺,意料不到的是这里的僧众那么多,规模宏大,并且还有一个佛学研究所,他们到达国清寺的当天,还赶上了一应僧俗在讲经做功课。那国清寺是禅宗天台正宗的发源地。达夫他们的来访,自有那道貌秀异的法师前来陪吃晚饭。
他们在天台山游览了三天,饱览了那古色古香的寺庙建筑。那国清寺的建筑最为广大,占地达两万平方,内在四殿五楼:什么样弥勒殿、伽蓝殿、大雄宝殿、观音殿、雨花殿、钟鼓楼、方丈楼、迎塔楼、藏经楼,还有什么妙法堂、安养堂、闻所未闻。在寺外,他们还看见了隋代的古梅,据说是开山大禅师手栽。据说这国清寺的大名也与开山祖师有关。据传开山祖师未见寺成,只留一偈:“寺若成,国即清”。
他们游览了见之于《天台山方外志》的天台石梁,那是天台名胜古迹中的画龙点睛之笔“石梁飞瀑”,他们是坐轿车去的,但轿车只能到达金地岭下,继续上山还须攀援步行。好在晨起时,国清寺中的方丈,赠与他们两支万年藤杖,策杖上山,倒是别有风味呢。他们走了一天,到过智者大师的佛塔前的真觉寺,到过龙玉堂的方广寺,那方广寺分上方广、中方广、下方广,乃在石梁飞瀑的周遭,但见风篁万竿,一瀑飞挂,点点红瓦黄墙。飞瀑之上五六尺就是石梁一条,果然是天下无双,郁达夫大慰平生,有不虚此行的感受。郁达夫游兴甚浓,当天他们还直上天台山的最高顶,宿在华顶寺中。他们希望第二天早晨能够在华顶峰上看到旭日喷薄而出。据记载,这华顶观日,与泰山的观日峰,崂山的崂顶,黄山的最高处,有异曲同工之妙,乃天下之奇观。他们特地起了一大早,在清晨三点钟起的冷雾、云涛中,颤颤发抖,可惜直到上午六时,华顶山上依然是雾锁深山,云潜红日,可算是白白辛苦了一场。但他们在这华顶山上也是兴致勃勃,这山顶可是李太白诗中的“天台四万八千丈”哩。第三天,他们还弃了轿夫,按图索骥,游览了这里道教圣地桐柏宫,观赏了附近的桐柏大飞瀑,看过琼台双阙……
他们意犹未尽,又在天台山中盘桓了三日,他们恋恋不舍地离去,乘车去了雁荡山。
雁荡山在乐清湾的大海边。乃是直到唐宋时期才开山的的天下名山。郁达夫从范成大《桂海岩洞志》中发现,天下同称的奇秀山峰,莫如池州的九彳阜.山,歙州黄山,栝州仙都山,温州之雁荡山。他们急欲游览雁荡山。
天台至雁荡山,与金华至温州一样,公路建设正在全面铺开,右桥梁处处还未竣工,必须借用渡船,将那笨重的汽车渡到对岸。好在那时汽车还是稀罕之物,新筑公路上汽车极少,这雪佛莱乃是惟一的铁马,到了那日夕西下时,过了白溪,他们早已到了雁山的门户响岭头。
公路的终止在响岭头,但他们必须住在灵岩寺,雁荡山号称百零二峰,六十一岩,四十六洞,十八古刹,十六亭,十七潭、十三瀑、但最有名的景点不过是二灵一龙,这灵岩寺呢,又是雁荡山中心的中心。
他们刚刚进入雁荡山响岭头时,便被那博大怪异、气象万千的雁山境界惊呆了。步换景移,峰回路转,莫名万状,果然是天下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