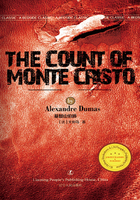一
暮色从远山外暗暗地袭来。
眼障般的南山,一会儿深赤,一会儿淡青。
一缕缕晚烟从马勺子镇冉冉升起。
太阳的最后一抹光晕暗淡下去,周围笼罩着一片深沉神圣的静默。
天黑了。
乔家小院静静的。
北屋里虽然是15瓦的灯泡,开着门儿,光也能在园子里照得满满的,而且把那颗大的老榆树的影子推到小院外小草垛儿上。
党妹在地里照应拖拉机犁地。
三狗儿在厂里。
桌上只有三个人在吃晚饭。
二狗儿碗挡着脸,喝他的稀糊儿。
老乔头还没吃,手里有烟没抽完。
老乔婆,一手抱着红红儿,想喂她吃什么。红红又哭又倔,蹦兔儿一样,在她怀里乱蹬乱抓。抓烦了,老乔婆扒开红红的小裤子,在她小屁股上拍了两下,孩子委屈地大哭起来了。
“要她妈妈了。”老乔头望着孩子,叹了口气,“哎!日你妈妈的!大西沟那儿,我去了,房子还有,他家里肯收。冬季要拉车煤去,万一生了,可不能冻着了。
“哎!”老乔婆也叹了口气,“哪来的钱呢?棉花收去了,不知啥时发工资哩!一车煤要好几百。现在贵刹了。”她沮丧地悠悠拍哄着红红儿。
老两口一筹莫展。
二
老乔头扔了烟头,刚要捧碗喝粥,突听院门儿一响,以为是二狗女人回来了。问:“耕几墒啦?”
“一墒还没耕哩。”
“啊?”老乔头站起来。
来人关上门,大大方方走到老乔头跟前一笑:“咯咯咯······乔叔,你想媳妇想疯了吧?”
听笑声,他知道是黑冲的女人,一转身回到桌边,给春嫂个屁股看。
春嫂一脚跨进来。
家里一阵窘人的沉默。
老乔头又重新卷他的烟,眼看着自己的脚尖,有些心不在焉地从荷包里往纸上抓烟末儿。纸上一半,地上一半。
老乔婆脸色有些张惶,光跟红红儿打岔儿,不去正眼看一下春嫂。
二狗儿只是听见粥响。
春嫂自觉没趣,在靠二狗儿旁边的一张木凳子上坐下,对二狗儿看看,二狗儿脸不抬一下。她便半开玩笑的伸手一拍他那脑后的肉脖颈儿:“吃的什么好东西,都不理人。”
二狗儿一吓,抬头对她望一下:“嘿嘿。”一笑又要吃。
“你女人呢?”
“在地里。”
“男子汉,大丈夫,这么早回来。让女人一个人在地里,没出息。”
“爹马上去换。”
“爹,爹,爹的。大小伙子不能去换?”春嫂说着给二狗一下。
老乔头搭茬说:“他不懂,耕地的,要经常给他们送送烟,倒倒水。他会?”对春嫂看了一下“黑冲呢?”
“在。”
“你家的地犁了?”
“没呢。”
“你家黑冲啥也会,哎!我们家吃饭的人多,日他妈妈的!”
春嫂趁机说:“乔叔,其实你早该享福了,革命几十年,退了休,还给他们操着心,要我,不干。”春嫂说着对他一看,“三狗儿女人回来没有?”
“没呢!”
“你不知她到底去哪啦?”
“我怎么知道?婆妈娘们的事。”老乔头吐了口唾沫,又把烟按在嘴上。
“是啊,前天王团长说要找你谈谈,我就说,这事与公公有啥关系。这完全是是三狗儿的主张。”又小声说,“你知道吗?三狗儿这烂尸首的把她女人藏到哪吗?”
老乔头十分凝神:“嗯?”
老乔婆静静地听着。
春嫂继续说:“我告诉你,三狗女人藏在七湖叔家呢!我今天去啦。”
老乔头老乔婆同时一怔。
“乔叔,你说这事多不好。再是老战友,把个双身人藏到人家家去,人家不担责任?即使七湖叔不说长短,七湖婶是个爽利人,有难说不出。我知道是三狗送去的,我也替你谢了谢人家。我看,你马上去把她带回来,这样大家没事,七湖叔家也不伤和气,你也不犯政策,三狗儿也不受处分,工人照当,我也不挨上边批评。再说,一家的面子,也有处搁。要不,三狗儿扎了,又生个天宝子,哪来的?你说对不对?”对红红儿看看,“你们有了这个真种,行啦。有的姑娘比小伙好,别听人家乱说。”一拉老乔头衣角,“再说,马勺子庄哪一个躲得了的?你也知道我的脾气,我跟你打也来,骂也来,叫我眼睁睁地望着你这么个老同志,老党员犯错误,我可不来。”
老乔婆这时抱着红红站起来,一手勒住孩子的腰,一手到柜上的盒子里抽了支烟给黑冲女人。
黑冲女人本来不会抽烟,但是老乔婆拿来的,也就接了。又到老乔头手边拿了火柴,点着,抽起来。
黑冲女人抽完烟,又说了几句话就起身走了。
一家人,鼻子里风儿听不见,好像都在用眼睛说话。
三
月上南山尖的时候,党妹回来了。
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一犁耕过去,一直向一眼望不到边的地那头开。车灯,像一双困倦的睡眼,发红,发白。
她觉得身上又饿又冷,便跟司机说好回家拿件一份。
一进院门,北屋只见灯火,听不见人声。
刚进门便觉得家里的人很不寻常。俗话说,进门看脸色,出门看天时。党妹不知老乔头为何这样,又是大爆发前的沉默,压得她气不敢粗出。
“你怎回来啦?”老乔头这不是说话,大声吼。
党妹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说:“我回来拿件衣服。”
“日你妈妈的!你这个养不家的狗,把家里球蛋往外衔?啊?”手里烟嘴往桌上一拍,“你跟黑冲女人嚼些什么舌头啦?”
党妹套了件褂子走出来:“这几天,我都在地里,哪有空去她家?”
“你还敢顶嘴。”老乔头一下站起来,顺脚踢倒凳子。
凳子倒在身边的狗食盆上,砸得碎瓷一地。吓得老乔婆怀里的红红儿哇哇直哭。
党妹又回头进房里去。
“你给我出来,日你妈妈的!是你把三狗女人的事说出去的!要不黑冲女人怎晓她躲在朱七湖家?我空收养了你几年!”
房里党妹抽鼻子的声音。
“你把装身子的事告诉她,又把三狗女人出去躲的事也告诉她,你不是我家人!你给我滚!滚!你这个不下蛋的鸡娘们,滚!我们乔家没有你这个野女人,今天晚上就给我滚!”老乔头疯了。
家里人没有一个敢顶他,他已经疯了,眼红红的,很怕人,脸板得刀扎不进,胡须也刺刺地竖起。
党妹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她吓得抖抖地发冷。听老乔头叫她滚,而且是决无反悔地叫她滚,她觉得伤心和绝望,她觉得屋里人都那么冷酷和绝情,小院里那么陌生和可怕。
人在绝望之后,会产生坦然,在害怕之后,会产生胆识,在痛苦之后,会产生无所谓,在谨小慎微以后,会产生不在乎,在乞求以后,会产生不买账。
党妹拭着泪,慢慢从房里走出来:“爹······”
“我不是你爹,你给我滚!”老乔头正拿着一只蓝花碗要盛粥,见党妹朝他走来,气得勺子一扔,碗对她砸过去。
党妹吓得一躲,碗从她头边飞过去,“哗!”击中她身后那块"花好月圆"的玻璃匾,玻璃片哗哗落地。
红红儿第二次吓得放声哭起来。
一片较大的玻璃掉在党妹手背上,划了个口子,立即流出了蚯蚓似的血虫儿,沿着手臂,手指,慢慢地向下爬去。
“你们好日子不过,偏要闹,闹!”老乔婆这话不知是对老头,还是对党妹。
反正两边都没听。
老乔头继续发疯,搬起板凳砸媳妇,被老乔婆拉住。
党妹哭着说:“你们别这样,就是死,也让人死个明白,我多早晚把三狗女人的事告诉春嫂了?连三狗女人在哪儿,我都不知道,你们这明明是逼我去……”声音最快大了,“走,我走!不过我要说明,是你们逼我走的,不是我要走的,怪不得我是什么忘恩负义的人,你的救命之恩,这几年,我当年做马还了,报了,我对得起你们家。”又说,“二狗儿是个老实人,我对不起他。”
党妹说着,哭着,跑到房里拿出自己带的破包儿,解开:“当着你们的面,看看,我什么样来,还什么样走。线头不捏你们家一根。”说着,又收包裹,扎好。转过脸对二狗儿鞠一躬,掉头看也不看老乔头和老乔婆一眼,走出院门。
二狗儿要出来,被老乔头喝住。
四
党妹从乔家小院走出来,沿着丰产渠一直向前走去。
皎洁的月光,静谧地装饰着初冬的夜空,风也停止了。
一望无际的大戈壁滩,像深蓝色的大海一样安静。
月边的几朵薄云像是凝固了。
远处的天山犹如伟岸的天城,庞大、阴森、威严。
四处悄然无哗。
她回头看看乔家小院,没有声息。
她不由后悔起来,她怎么在这里过了五六年的日子,到底怎么过来的?一片空白,只有一双双凶狠,挑剔,嘲弄的眼睛——永远忘不了的那些眼睛。
她又一次想起她的家,想起她所到过的地方。想起她所吃的苦,想起她所受的欺,呜呜呜,呜呜呜······她哭了,哭得好悲痛,哭得好凄凉,哭得好伤心。她并没有大声哭泣,只是嘤嘤咽泣,怕惊动了静静的夜。
这静静的夜是传情的,含蓄的和深邃的,咽泣声通过渠水,通过戈壁滩上的那像泪痕一样的水流痕,传得很远很远,引起远方山谷中狼的同情和牧羊狗的悲怆,狼嚎叫,犬嚎叫,不时遥遥相对。
她担心今后的日子,她害怕今后的日子,她绝望地站起来,抱着大树,望望渠中滚滚不息的流水——她又一次想到了死。
死,对幸福的人是一种折磨,对生活艰难的人是一种解脱和拯救······在她快要走进水中的时候——她又一次想到了他的幻影,似乎看到他朝她走来——也想到她——亲骨肉的幻影。
人在世界上生存,如梦游神一样,不知今后日子怎么安排,会碰到什么人。
于是,死神又一次将她推上岸来。
党妹又回头向马勺子庄走去。
她没有回到乔家小院,越过它,走到北街,在春嫂家院门前停住了。
“春嫂姐,”党妹轻轻地拍门,“春嫂姐。”
没有人应。
她想走,可往哪儿走呢?
又叫:“春嫂姐”
“谁?”
睡梦中,春嫂听见有人叫,连忙披衣出来。没开门,先问:“你是谁?”
春嫂姐:“呜呜呜······”
“啊!党妹!”开开门,“你怎么了?”
党妹双膝跪地,又叫:“春嫂姐。”
“别哭别哭,快别哭,这深更半夜的,让人家听了吃惊。”
把她让到家里,“告诉我你咋啦?”
“乔家逼我出来,说我坏了他们的好事,这几天,我都在地里干活,一次也没碰到你,说我把家事告诉了你。”
“我知道了,”老乔头这个老顽固,不见棺材不掉泪。“这事与你无关。”问,“你出来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不想过了,呜呜呜······”
“你傻呀你?难道乔家不要你,你就没处活了?他不让你活,你偏要活下去,总怪我们女人太无用了。自古以来,我们偏要依附在男人的身边过活。属于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我们的,自己安排,当然你的命运也太不幸了。但也不是只有死呀。有党,有社会主义,有邻居。你就在马勺子庄活下去。活给他们看看。你先在我家住下,有了好地方再走。让老乔头承认,逼走你,对他,对他那个家都是一大错误!跟倩倩睡,明天咱们找团部去。”
春嫂一席话,党妹听了佩服。春嫂又懂道理又坚强,自己为什么这么软,面团儿一样,让人捏?她觉得她以前不是在生活,而是生存。
是在乞求生存。
六
天亮后,春嫂把事情向团部领导作了报告,团里决定:由老乔头把三狗女人带回来,三狗停职检查。党妹原来跟二狗结婚没有通过手续,现在无所谓离婚,由她自愿仍回乔家也可以,但必须重新做结婚登记。不回乔家,团部负责安排个体活,她没户口,不包地,如果要离开马勺子庄,由春嫂送到县民政局。
一切由春嫂负责处理,春嫂把团部的意见告诉党妹,党妹不愿意回乔家,也不愿离开马勺子庄。
春嫂说:“党妹,我也不希望你离开马勺子,我不仅同情你,我也喜欢你,如果你不嫌弃,我们拜个干姊妹,你看怎么样?”
“春嫂姐,你是好人,不用说你,我早就把你当亲姐姐了。只是我命苦,怕你嫌弃。”
“我不是那样的人,今后你嫁人更好,不跟人,倩倩是我的女人,也是你的女儿。”
“姐姐,我这一辈子忘不了你!”又要哭了,掏出手帕,捏鼻涕。
“嗨,以后你要坚强些,眼泪救不了我们女人的命。”
“不过,黑冲哥·····”党妹担心起来。
“放心,黑冲听我的。”又一想,“有个事,我相对领导说说,让你去先干。团部招待所那两个千金小姐,都是关系上来的,自己倒打扮得花枝招展,可那十几张被子脏得黑狗儿精一样。我想让你去那儿洗洗被子,怎样?闲下,还可以干点别的,好不好?”
“好倒好,我怕人家不要我。”
“有我呢,我对领导说去。”又说,“你还会干些什么?”
“我,我以前在老家搞过红枸杞儿卖,我看这儿也有许多,搞点买卖也可以。”
“哎呀,死人······”春嫂双手一拍大腿,“你怎么不早说?马勺子原有个枸杞专业户,去年去了精河镇,你跟他学习,怎么种家枸杞,怎么晾枸杞干。你知道吗?枸杞干比葡萄干好吃,还能治好几种病哩。外国专家说它是最佳药用食品。”
“是吗?”
“怎不是呢?我看你就干这个,比包地好,包地十个人九个赔。现在都不肯包地,有办法的人个个做生意去。”
“嗯。”
七
“倩倩,过来。”
倩倩到放学才进门,春嫂在厨房叫。
悄悄走过去。头上两把刷刷辫,圆圆的小脸蛋,红格子褂,红领巾,蓝裤子,白球鞋。她跳跳蹦蹦地来到厨房,一见党妹:“阿姨好。”
“哼,”春嫂忙着切菜,对女儿一瞥,“不准叫阿姨,以后叫姨妈。”
“姨妈好。”倩倩一笑。
春嫂笑了。
“党妹,你说倩倩像不像我?”
“嗯?”
“不像我,像你。是像你。你一来马勺子庄,我就对黑冲说,哎,怎么这么绝,倩倩眼睛、鼻子、嘴、下巴,哪一处都像党妹。他也说像。咯咯咯······怕命中注定是你的女儿呢?”
党妹把倩倩一把揽在怀里:“我哪有这么好福气唷!”
‘不瞒你说党妹,我这个女儿比男孩强一千倍,你看我们庄上那几个独生儿子,奶奶的!整天把他当小老太爷服侍都不行。长大了到底有啥好处?儿子打老子打老娘的多的是。你看老乔头,一家人把红红儿不当事,拼命想男孩子。老霉球儿,也不知是那个王八下的野种,还当宝贝一样。哈哈哈······真愚昧。哎!这也不是他一个人。有的人拿几级的官换儿子,有点拿党籍换儿子,这些人怎么都成了病态。“
锅要开了。
春嫂刹住话头。
党妹羡慕她懂的大事多,会说,能干。
她更羡慕这个家,一个充满欢乐的幸福的家。
啊!家!
人没有家还谈什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