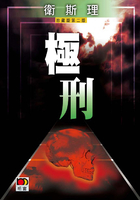一
“麦黄收割!麦黄收割!······”
天刚蒙眼儿,东南天际那颗启明星还亮闪闪在南山尖上。一对呱呱咕翘着尾巴在乔家小院里的老榆树上一个劲儿地叫。
新疆的节令跟口内不一样,江南江北小满吃半枯,不到芒种,麦子就全黄了。常说乡间四月无闲人,四月闲人不是人。可在新疆,小暑大暑,麦子还嫩青。也应了诗里写的:
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里桃花始盛开。
二
今天好大的雾!
慢慢地,曙光茫茫。
整个马勺子庄和庄外的林带、戈壁、天山,处处都寂静无声,只听得睡意朦胧的树木上的露珠,哒!哒!打在葵花和南瓜那宽大的叶面上。
不知谁家的公鸡,脆脆地拉了个长鸣,“喔!喔!喔——!”全庄的公鸡也长一声,短一声地跟着叫了起来,此起彼伏,一呼百应。
浓雾越来越沉。
整个马勺子庄像装在牛奶瓶里。
晨时雾,晌脱裤!——又是一个大热天!
中午天上下火,干活全靠早晚凉。
于是,小院里开始有了动静。
“麦黄快割!麦黄快割!”树上那鸟儿一听到人得声响,更是叫得紧。
“吱!”东屋门开开一扇,上面印着熊猫画的新竹帘儿,高高地掀起,走出一个人来,两手提着裤子,对天望望,打了一个呵欠。虽看不清面孔,也便知是老乔头——小院里的当家人。老伴、儿孙七八口,全在他肩上扛着。大人小孩要吃要穿,而今团场不发薪水,承包了,靠自己苦!当家人能睡觉?睡不着!早起三日一天工呀!
他慌慌地走到院西边,哗哗哗!响响地撒了泡尿,扎了裤带,双手一窝,呵了一口晦气。走到驴棚跟前,给小灰驴儿扔了把青草。顺手拿起棚边的小铁铲,弯下腰,寻金子一样,将院场上的鸡屎,一堆堆地铲到粪堆上。天一热,这些畜生比人起得早。
仿佛在屏息的大地,开始有了一丝丝轻风,轻得犹如婴儿熟睡的鼻息。
沉重的浓雾,倦倦地开始蠕动。从裂开的缝隙里,还可看到黑蓝黑蓝的天空中的残星。
晨光将要来临。
天山顶上出现了一片柔和的、浅淡的玫瑰色。
远处的山,近处的房屋、草垛,都显出了水墨一般的轮廓。
三
老乔头咳了一声,又拿起锄头当啷!在水泥地上使力着了一下,像是给屋里睡觉人发出警铃。
于是,竹帘里又走出一个人来。一手扣扣子,一手拿着一条蓝花围裙。
“他爹。”是老乔婆。
“嗯。”
她刚说着话,看一群鸡在围着老头叫,又折回头,从屋里端出一瓢黄黄的苞谷:“咯咯咯·····”一唤,几十只鸡轰的一下,全飞到她周围,有的飞到她手上、肩上,气得她又打又骂,“瘟器!”手里的瓢狠狠一泼。
遍地都是啄食声。
老乔婆拍拍瓢,走到老头跟前:“地里的苞谷,今天可要锄了!”
“哪地?”
“十八条。”两手背到身后,“你没见人家明富地里的苞谷?早锄过了,又上了水,像浇了沥青,绿得发黑。我家地里哩,黄黄的筷杆儿粗,根下几片叶儿点得着火!中午太阳一晒都卷卷的,蔫蔫的。秋天收啥!人家吃饭,我家水还喝不上哩!”
老乔头不理她,还是低头“嚓!嚓!”磨着那把大扁锄。
“我说今天全去那地里突击,中午我送饭。”说着,将黄瓢放在窗台下,顺手理开围腰布,扎上,掏出钥匙,打开北屋西头下的厨房,准备做饭。
老乔头没听见老伴已经走开,雾蒙蒙的,以为她还站在一边在等他嘴里那句话,便说:“我在更头里已盘算过,今天二狗儿俩人和我都去十八条。三狗儿带他婆娘去县医院检查检查······嗯?”
好一会儿没人搭腔。他停住手,掉面一看,没人。
天越亮了,山顶尖上已经淡淡地拖直了一条乳白色的狭带。一种酔晕晕的,薄薄的绯红,透过雾,朦朦胧胧。浓雾悄悄开始变薄,有的降到凹地里,池塘里。有的悄悄往山后躲藏,有的徐徐向上升高,像是香炉里飘出的烟氤。
庄上已经开始有人走动、还有驴蹄声、工具撞击声。
老乔头看看北屋和东屋的帘儿,平平静静地垂着,又重重地咳了一声。
这时,一只小花猫从北屋帘下钻出来,四足伸直,扬起尾巴,痛痛快快地伸了个懒腰。
老乔头打不着山中虎,便拿身边的猫出气:“你也懒睡!天亮了都不知道!”
话音刚落,二狗躺在床上喊道:“爹,给我那把锄也一块磨磨。”
“在哪?”头不抬,手里也不停。
党妹掀开门帘,拿出一把大锄,送过去。
“要使劲磨!钝!”二狗仰躺着,又补充一句。
老乔头听着不悦,心想,你们两口子睡,我抓黑就起来了,还嫌我没劲!火便往还没起床的那一口子身上发:“二狗儿,还没起?都什么节下了?去看看人家的地!还躺得住?没心!”
“他起来了,马上就出来。”党妹眼对东屋一瞥,走到厨房:“妈,缸里要不要担水?”
“让他担。”大声喊,“二狗儿起来担水!”从怀里拿出火柴,“党妹,你烧火。”
——叫党妹的,是二媳妇。
四
炉里火一着,映在党妹的脸上。看得清楚,模样儿打足了,说三十出头。她的神态很是清雅。尽管她还称不上风流、妩媚和一看即令许多男人神魂倾倒的女人,然而她给人一种朴实、内在的美感。满头厚实的短发,没烫。早上起来还未着手梳妆,只是很不留心地用手随便往后拢了拢,夹在右边的耳根里。
眼睛深邃、有神。老一会看着灶膛里的火,不眨一下。鼻子和嘴都严格按照比例和方位长着。鼻子吸气,轻轻地、慢慢地。嘴唇缄默安祥,似乎平素不大启动,只保持一种和谐、有力的线条。脸色不亢不卑,悒默里稍稍流露出抑郁。身上一件开始褪色的红底白花的确凉衬衫。腰里不肥,显出她那有线条的身材。大翻领,露出细白的脖颈来。
锅里的水听见了响声。
她勾着头对外面喊:“妈,水开了。”
“噢。”老乔婆答应了一声,掀开帘从东屋里端出一瓢苞谷面。
锅烧好了,党妹还不见男人去担水,就自己套上水桶,走出院门。
五
乔家小院,前几年的院门并不是朝南开着,而是朝东。朝东是街,又对着对面的乔怀珍家院门。老弟兄俩门对门,既显得和气,又能互相照应。
三狗儿女人过门后,二十八天就有了肚子。老乔头查来问去,还是狗日的小乔三提前下的种。
管她保人啥种,老两口一样喜欢,东里西里算命打卦,请阴阳,都说要生男孩。但是,看风水的人说,要想抱孙子,就将院门要改一改,改朝南(男)。
老乔头很信,因为这不是瞎说的,是根据命辰八字,天地阴阳,风水星宿决定的。他一听就照办:堵了东门,开南门。砌东屋,铺南路,一切围绕“男”儿做。
结果,三狗儿女人叫娘喊爹,叫了几天几夜,蹬通了一条被单,抓烂三狗儿两只大腿,咬着牙,撑下一个丫头!
老乔头也靠着家里腰墙听了三天三夜。耳朵也磨满了墙上的白石灰。哎!最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口气很重,差点儿把脚边的芦花鸡吹跑了,扛起铁锹便下地。
从此,便走惯了南门,绕了路,也得走。
走东门,去担水很近。出了门边,经过乔怀珍屋后,再向东,不远就到了。这下非得绕过一个院子,从乔怀珍门前经过,再绕过他家东山墙,七绕八拐,一担水,走双倍路,人也吃了力。
党妹担着水,绕完冤枉路,到了院门已肩疼腰酸,身一歪,后桶撞在院门框上!
老乔头连忙掉过头,心疼:“嗐!前眼后眼一齐始嘛!”又大声喊,“二狗儿!二狗儿!不争气的货,男人睡,叫女人担水!”
二狗儿使劲将帘一掀,往上一扔,憨直直地站在门台边。他喜欢图凉快,只穿件裤头儿。上下一样溜圆,一样黑。
老乔头听见帘声响过,不见动静,气得掉过头摔了他一眼:“没出息的东西,尿不涨,不得起!”
这话一点没说错,二狗儿是觉得小肚子鼓硬鼓硬的。他站着是想看看院西根的尿桶在不在了。可是不在,被老乔头拎走了。他想找个地方放尿,又不行。天亮了,妈和她在院里,而且东屋里小乔三两口子也被老乔头嚷醒了。
他双手提着裤子在院里匆匆转了一圈,只得又回屋穿了件汗衫,出院门,对着草垛后边的南瓜根,足足追了一次尿素。
六
晨光来临了。
太阳还没有出来。
马勺子庄上的一切已显而易见。
东方的天空,渐渐地由黑变白,由白变蓝。天山上面那一峰连着一峰的、海市蜃楼一样壮观的云城,遮住了天边的太阳光,光在这些云峰边上,镀起一条曲折迂回的光边,粉红色、玫瑰色、电光色、金光色、灿灿烂烂!
于是大地充满了光明,充满了生机。山的朝阳的一面,像刷了一层金。
马勺子庄上一家家朝东的墙,统统染上桔红色,掩映在葱茏的林带之中,显示出大戈壁一种神圣的、安闲的、独特的美。
七
老乔头身边放着三把磨好了的大锄。
他甩甩手上的水,从上衣口袋摸出一包莫合烟,侧抬起身子,从大口袋里拿出张折了好几折的旧《新疆日报》。折起一个小长方形,用手抹平,对着舌头一捋,撕下,将烟末倒在纸上。很熟练地卷成一根粗粗的烟棒棒,点着,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一连磨了三把锄,中间没吸烟,瘾早来了。所以一口烟吸进去,好一会让它闷着,然后慢慢张开嘴,再让它轻轻冒出来。一缕缕从胡子,到鼻子,再到眉毛。闭上眼,细细地品,细细地熏。
晨光明明地照着他的脸。一张满是皱纹的脸,一张饱受风霜、缺乏营养、刻着无数道年轮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