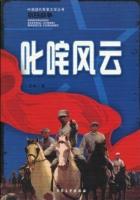雨过天晴,日光如水,悄悄落在身上,感觉麻嗖嗖的。天空蔚蓝,很纯粹,好像是被谁抹去了杂质。绸子一样的云朵缓缓移动过来,转瞬间演变成了各种模样,给平淡无奇的天空增添了些许乐趣。远处的西山上笼罩着一层薄雾,将挺拔的山体包裹起来。
风迈着缓步徐徐而来,把方炜蓬松的头发吹散。他停下来吸入一口气,空气中似乎充满了泉水的芬芳。方炜笑了笑,继续往前走,今天他的心情像天气一样好。前两天,方炜的老乡请他吃饭,饭桌上老乡给他介绍了个四星级酒店的工作,方炜心动了,想也没想便答应了。
方炜换了一套最体面的西服,天不亮就出了宿舍楼,他没等公交车,他怕西服被挤皱了。马路上早已是人满为患了,打工者们穿着各式服装,夹着公文包,举着早餐在道路两侧穿梭着,他们一边走一边吃,脚底生风,忙忙碌碌的样子。这条老街永远都是这个样子,老人走了,新人马上补上来。
方炜拦下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酒店的名字,然后坐在后面上闭目养神。车到了酒店门口,老乡迎上来,方炜付完车费,大大方方地下了车。说实话,他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他从未见过如此之多的外国人,空气中弥漫着异国的味道。他估计这片土地是由上帝说了算的。
酒店大概有二十多层,外墙纯白,阳台宽大,里面摆着两盆叫不出名的绿色植物,植物旁边是一张塑料椅子,躺上去一定非常舒服。有的人在阳台上浇花,有的人在上面看书,阳光照在他们黝黑的皮肤上,一派悠闲富足的景象。方炜忽然想到了自己的宿舍,不由得咽了口唾液,嘴巴里真不是个滋味。
老乡带着他往里走,院子里铺着平整的柏油路,三四个戴头盔的小青年像踩着烽火轮似的朝方炜冲了过来,方炜站在原地没有动,两个小子从他的两侧滑了过去。
方炜的老乡原本也是酒店的员工,他在老家开了一家小型的食品连锁店,上个月办理了离职手续,临走前他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他古道热肠地把方炜介绍进去。老乡对方炜并不隐讳,把实情一一相告,方炜表示自己愿意当作一面红旗插在酒店的楼顶上。
方炜感谢这位老乡,不单是对方首先想到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他听到了实话。这年头,讲实话的人快要灭绝了。
人事部在配楼的拐角处,棕色的大门相当醒目,上面是英文,下面才是中文。办公室里的桌椅都很陈旧,与豪华的主楼不相匹配。办公室里坐着五六个人,穿着黑色的制服,胸前别着绿色的塑料名牌,有英文也有汉语拼音,好像很民主。
老乡让方炜在门口稍候,他去里面找熟人。他这么一说方炜才发现,原来里面还有一个大间。方炜傻乎乎地坐在门口的沙发上,手和脚都不自在,那感觉像是进了人家的客厅才发觉房主根本不认识你。
办公室的职员各干各的,谁也没有抬头看他一眼,仿佛这个人不存在似的。方炜有些不爽,胸腔里的火苗子腾腾往外冒。
老乡拿着一张空白表格回来了,他用手指了指,方炜会意,立即从公文包里取出签字笔,一笔一划地填写个人履历。这种表格他见多了,无非就是户口本上的那些东西,还有之前供职单位的名称、电话,都是老一套,没啥新意。由于这次是熟人介绍,所以他写得格外工整,像小学生的字,方炜的手心出汗了。
老乡带着他进入了里面的大间,方炜看到两个人,一个在低头发呆,另一个在打电话。老乡毕恭毕敬地站在办公桌前,两手自然下垂,脚跟并拢,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打电话的职员大概三十出头,前额很宽,高挺鼻梁,嘴角略微下垂,嘴唇丰满,洁白的牙齿,一头漆黑的披肩发,头发有些卷曲,有染过的痕迹。她的名牌被衣领遮住,看不清上面的名字。她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两个人,然后继续她的谈话。她的说话声低低的,像是在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耐心等着吧,求职的人似乎本该低人一等,爷爷和孙子的表情都写在脸上。
“她是李姐。”老乡耳语道。
过了十分钟,李姐终于放下电话,她在记事本上刷刷地写起来,又过了五分钟,她好像才想起这两个人,于是她放下笔,抬起头打量来者。李姐莫名其妙地皱了皱眉,草草看完简历,把方炜从上到下看了一遍,然后从下往上看了一遍。方炜被看毛了,他担心对方会掰开自己的嘴巴看看牙齿。
“他可能干了,脑袋瓜灵活,干啥啥行。”老乡画蛇添足地说。李姐不耐烦地摆摆手,老乡的话立刻被打散了,飘到房间的各个角落。
“懂英语吗?”她问。
“有基础,简单对话没问题。”方炜实事求是地说。
李姐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她的眼里好像有把秤,正在称量方炜话里的水分。方炜马上用英语作了个自我介绍,发音标准,吐字还算清晰。李姐微微点点头,她眼睛里的秤被方炜砸烂了。
李姐拿起一个黑文件夹,翻了几页,然后拨了一个电话,低低地说了几句。方炜知道,第一关算是过去了。“去二楼餐饮办公室,找彭师傅。”李姐放下文件夹,下了驱客令。
老乡说了一堆的感谢话,两个人离开人事部,大厅里的职员还在忙碌,有说中文的,有说英语的,连电话铃声都透着一股不可一世的傲慢劲。
“我是干保卫的,其他管理人员我就不认识了。”老乡惭愧地说,好像干了一件不齿的事似的。方炜从包里取出一盒好烟硬塞到老乡手里。“你等我的消息吧。”说完,他转身进了酒店主楼。
员工通道干净明亮,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地面像镜子,走在上面连脚步声都没有。方炜问了两个保安,找到了二楼的餐饮办公室,他敲敲门,没人回应。一个中年人走出来,他告诉方炜可以直接进去,不用敲门。
方炜走进去,他看到办公室里隔出了两个单间,每个独立办公室里都坐着一个外国人,胸前挂着绿色的胸牌。方炜愣了,彭师傅难道是外籍员工?
“你找哪位?”穿绿西服的小秘书问道。
“我找彭师傅。”
“他刚出去,你没见到?”
“噢。”方炜知道了,那个中年人就是彭师傅。
方炜追上了彭师傅,如果错过,他的工作大概就告吹了。彭师傅高大魁梧,穿着一套黑西服,裤子上装饰着密密麻麻的条纹,像睡裤似的,看上去有些滑稽。他头发很短,这样一来脸就显大了,呈鸭蛋形,他有一双精明税利的眼睛,面相较为憨厚,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举手投足有大人物的范儿。
彭师傅站在走廊里问了一些基本问题,无非就是年纪,学历,兴趣爱好等等,方炜一一作答,这是一个奇怪的面试,爷爷和孙子居然都站在走廊里。职员们三三两两擦肩走过去,无一不回头观望,眼神中有好奇的成分,也有喜剧的成分。
“去人事部办手续吧。”彭师傅说完,转身走了,多一句话也没有,感觉他要去机场赶飞机。
方炜觉得辈分搞乱了,爷爷瞬间变成了兄弟。
回到人事部,方炜把彭师傅的话重复了一遍,李姐再次拿起电话,核实了一遍。方炜想笑,谎言的威力是巨大的,现如今每个人都必须携带测谎仪才能出家门。
挂上电话,李姐又拿出一张表,这张表格要详细得多,在方炜眼中,手中的纸变成了入场券。他详详细细地把所有的空白处填满,然后又认认真真地检查了一遍,最后他把“入场券”交还给李姐。“明天去医院做个健康检查,我把地址留给你。”她在一叠黄纸上写了两排字,随手一撕,纸就下来了,上面还有些粘性,很神奇。李姐的字很秀气,有艺术家的潜质。
方炜把纸条小心翼翼地塞进钱包的最里层,出了办公室,他觉得太阳笑了一下,随后将光均匀地洒在他脸上,方炜扭过头,发现酒店主楼上金光闪耀。
方炜壮得像小马驹子,健康检查注定成为形式。他拿到医院的检查报告后,直接去了酒店,李姐二话没说,复印,存档,办手续,干脆利落。方炜有了更衣柜,领了名牌,去了工作服,诸事妥当,他想起一件事,他将要去哪个部门上班?不会是洗碗部吧。
方炜不踏实了,心里闹腾了,那感觉像是临进洞房前连老婆的模样都没看过。怎么办?去问问李姐?算了吧,你早干嘛去了,丢人了。方炜那股子狠劲上来了,他想打人,打他自己。他倚在墙壁上一声不吭,这是他出手前的前奏。走廊里人太多,不宜动手,方炜耐着性子等,反正打的是自己,不用着急,他跑不了。
方炜眯着眼睛目视前方,心跳频率降到最低,像动物冬眠似的。一些俊男靓女从他身边经过,嘻嘻哈哈的,好像在嘲笑他。方炜热了,从里到外冒热气,他开始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后悔了。
“干吗呢,你?”一只大手拍在方炜的肩膀上。
方炜回过头,看到高高大大的彭师傅。“想事呢。”
“检查身体了?”
“合格。”
“手续呢?”
“办齐了。”
“明天八点半上班。”说完,彭师傅走了,又像是去赶飞机。
方炜回到宿舍,收拾行李,酒店提供宿舍,他终于可以告别这个乌七八糟的鬼地方了。几个室友帮他收拾,忙了半天只装满了一个旅行袋,剩下的哥几个分了吧,也不是啥值钱的东西。晚上方炜请室友们吃了一顿,路边的大排档,他们第一次吃饭,也是最后一次。三个小伙子喝多了,吵吵嚷嚷要去歌厅找小姐,方炜笑了笑,独自回到宿舍,他们永远不会成为朋友,因为他们脑子里想的东西根本不一样。
第二天一早,方炜跳下床,洗漱完毕后他看了看烂醉如泥的室友,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宿舍。当方炜推开人事部的大门时,里面的人惊呆了,他们张着嘴看着方炜,方炜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们。他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原来是肩膀上缝着几个补丁的背包,他们大概是把自己当难民了。
方炜大大方方地往里走,对面投来的眼神遮掩了,然后转向别处,气氛尴尬了。方炜笑笑,走到里屋。李姐把考勤卡给他,随后告诉他宿舍楼的具体位置。去宿舍楼已经来不及了,方炜把行李寄存在更衣室的大叔那里,说好下班取回的时间,然后,他开始换衣服。
更衣室里潮乎乎的,由于临近浴室,他身上一阵发痒,一个多星期没洗澡了,真想一个猛子扎进去,在浴室里滚,在浴室里喊。
着什么急呢,反正每天都能洗。方炜又笑笑,身体立马不痒了。
换好工作服,他走到镜子前照照,黑色的制服,短打扮,白衬衣,黑领结,胸前挂上名牌,还真像那么回事。不可能去洗碗,酒店可不会为洗碗工准备这么好的工作服。方炜踏实了,习惯性地眯起眼睛。旁边过来一个矮胖子,两个人的眼神在镜子里相遇了,他们的穿戴一模一样,方炜知道遇到了同事。他刚要打招呼,矮胖子一转身走了,喉咙里哼了一声。方炜吹了一声口哨,去餐饮部办公室了。
“你找哪位?”小秘书像是得了健忘症。
“彭师傅。”
“他的办公室在三楼。”
“知道了。”方炜推出来,去了三楼。
方炜刚要打听,看到矮胖子刚好从电梯里出来。这下好了,省口舌了。矮胖子迈着四方步慢腾腾地走在前面,方炜鬼鬼祟祟地跟在后面。两个人前后进了办公室,彭师傅正在里面喝菊花茶。“我忘了告诉你办公室了,你还真找到了。”彭师傅咧开嘴笑了,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
“问呗。”方炜坐下来,打量起办公室来,其实这里更像是库房,两个立式冰柜,三四排不锈钢架子,墙上贴着各式各样精致的宣传画,房间里到处都是酒,有躺着的,有立着的,有一米来长的,有指头大小的。商标花花绿绿,有人头,有动物,还有怪兽。办公桌上摆着奇形怪状的杯子,杯子旁边是五颜六色的杯垫,像学生时期使用的垫板。
方炜有些晕,他知道自己要和这些数不清的洋酒打交道了,那些张牙舞爪的英文字仿佛要扑上来,狠狠地咬方炜一口。
“你小子运气好,酒吧正好缺人手,否则就算是等上一年也不见得能进来。”彭师傅喝了口茶,慢条斯理地说。
“酒吧是干什么的?”方炜问。
“他会慢慢告诉你的。”彭师傅指了指坐在旁边喝茶的矮胖子,说,“他是你师傅,张庆海。”
张庆海胖胖的脸上露出冷峻的、略带讽刺的笑容。方炜心里咯噔一下,血管里好像堵住了,身体抖了一下。
“前三个月是试用期,合格后转正,签正式的劳动合同。”彭师傅放下茶杯,“这段时间你要跟张师傅多学技术,不懂就问。”
“知道了。”
张海庆终于说话了,他的嗓音很粗。“我们该上班了。”
方炜跟在张海庆屁股后面走出来,两个人谁也没说话,方炜就像他的影子。走着走着,灯光绚丽了,地面光亮了,背景音乐响起来,雪茄店、美甲店、首饰店金光闪闪,另一个世界哗啦一下向方炜扑过来。
身材魁梧的外国友人们挺着肚子在酒店里晃来晃去,全是一副闲人的样子,他们身上散发着浓烈的香水味,嘴里冒着一嘟噜又一嘟噜的外语,声音浑厚响亮,个个都像是朗诵家,在练习,在表演。
家庭主妇推着高级婴儿车在过道中间闲扯,她们不断地挑衅时间,时间却不为所动,该怎么走还怎么走,坚决不和这些闲人一般见识。婴儿车里是含着手指的大头娃娃,头发如绒毛,眼睛如宝石,他们咿咿呀呀,像哭又像笑。
餐厅里的服务员奇装异服,各大洲风格应有尽有。方炜探着头向里面张望,张海庆像是后脑勺有眼睛,他喉咙里哼了一声,那意思是让方炜赶紧跟上。方炜暂时把好奇心放进口袋里,沉着脸跟上他的张师傅,张师傅快他就快,张师傅慢他就慢。
张庆海七拐八拐进了厨房,厨房里很热闹,洗菜的,备料的,刷锅洗碗的,唯独看不到炒菜的,方炜看了一下表,噢,吃饭时间还没到呢。张庆海走到厨房的一角,盯着塑料筐发愣,方炜明白,该干活了。方炜张开双臂,把杯筐抱起,玻璃杯在里面挺不安分,乱动又乱响。张庆海指了指洗碗间,墙角处有一个机器轰隆隆响,方炜会意,大概那是洗碗机。一位慈眉善目的大妈接过方炜手里的杯子,从一头塞进去,过一会儿杯子从另一头热腾腾地钻出来,方炜闻到了消毒液的味道。真是高科技呀。方炜扭头看着背着手的张庆海,心里面想象着把他塞进洗碗机的情景。
两个人进入酒吧,方炜还没来得及看看周边的环境,一块蓝白条毛巾就扔到他面前,甭问,该擦杯子了,谁让你是新人呢。方炜把杯筐架在水池上,嘿嘿地忙乎起来,张庆海背手站在旁边,脸上挂着耐人寻味地笑容。几十个杯子擦完了,张庆海凑过来,用两个指尖提起一个杯子,举到一盏射灯下,转了半圈,然后他把杯子插回原处,笑着说:“全部返工。”
方炜二话没说,从头开始擦起,这一下他心里有数了,张海庆是个欺负新人的货。忽然,方炜笑起来,他觉得故事的开端越来越有趣了。
酒吧门被推开了,一个穿着同样制服的小伙子走进来,他双手插兜和张庆海打了声招呼,然后把注意力移到方炜身上,他看看杯子,又看看方炜,眉头拧在一起,五官不约而同地往中间靠拢。
“嘿,杯子快被你擦破了。”小伙子说。
方炜听不明白了,自己又不是超人,怎能把杯子擦破呢?方炜对这个人有所戒备。
“仔细看着。”小伙子拿过一个冰桶,灌满热水,然后把杯子倒扣在水面上,五秒钟后他抢过方炜手里的毛巾,一个毛巾角裹在杯底,另一个角塞进杯口,两只手朝相反的方向转,转了七八圈,小伙子举起杯子放在射灯下,晶莹剔透。
方炜注意到对方的左手腕缠着一团纱布。
“明白了?”小伙子问。
“明白了。”
“照方抓药。”小伙子把毛巾扔了回去。
“谢了。”
“张师傅没教你怎么擦杯子?”
“没有。”
“你要主动问,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