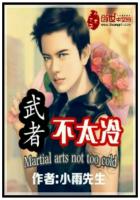“谢皇上恩典!”舒赫对着南宫百川鞠身作揖道谢。
舒赫靠坐于椅子上,双眸一眨不眨的直视着前方,一脸的冷肃与阴森。
舒清鸾大婚后的一天,鸢儿不声不响的进入太子东宫。
“来人!”舒赫对着门口处喊道。
“相爷,您有何吩咐?”管家进屋,微躬着身子。
“让二小姐来见我。”舒赫对着管家吩咐道。
“是,相爷!”管家鞠躬转身离开。
不到半盏茶的功夫,便见着舒紫鸢迈着细碎的小步迈门坎而入。
“鸢儿见过爹!”对着舒赫侧身行礼,而后又朝着他迈进两步,“爹,您找女儿可是有事?”
舒赫精睿的双眸沉了沉,直视着站于他面前的舒紫鸢:“你娘的情况可有好转?”
舒紫鸢的眉头微微的拧了拧,轻叹一口气,略显无奈的摇了摇头:“没有,还是把舒清鸾当成是我。女儿已经换过好几个太医和大夫了,都看不出什么来。可是因为娘亲怀着身孕,所以大夫和太医都不敢开药方。就算开了药方,女儿也不敢让娘服用。一切还是等娘生产后再说吧。”舒紫鸢略显的有些无奈,且无奈之余还微微的有些无助,“昨儿趁女儿不注意,又跑去舒清鸾的兰心居了。女儿真是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舒赫原本拧着的眉头又是一沉,然后重重的舒了一口气:“皇上今儿对你和太子的事,给话示下了。”
舒紫鸢的眼眸里划过一抹浅浅的喜悦之色,然后则是略显有些羞涩的垂下了头。
在她的潜意识里,舒赫说皇上对于她和南宫佑的事已给话示下,那便是她已然成了南宫佑的侧妃。
虽不是太子妃,但之于她来说,只要是侧妃,便说明对于太子妃一位,她还是有希望的。只要她到时剧力以争,只要她压过了百里飘絮,那么太子妃还是她舒紫鸢的。再说,她从来不觉的自己比百里飘絮差。
论相貌她远在百里飘絮之上。论心计,她自认不亚于百里飘絮。她唯一比不上百里飘絮的便是身份。
百里飘絮是宁国公府嫡女,而她是相府庶女。
但,若非沈兰心当初对爹娘的设计,相府嫡女便是她舒紫鸢,何是轮到舒清鸾那小贱蹄子了!
她现在的庶女身份,全都是拜舒清鸾母女所赐,所以她绝对不会让舒清鸾好过,她一定要报此仇!
所以,眼下便是一个好机会。
然后,正当她的眼眸里划过那一抹喜悦之色时,舒赫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是再度将她打入了万丈深渊。
舒赫沉厉的双眸直视着她,面无表情的说道:“皇上的意思是让你在她大婚过后,自行入东宫。没有任何排场,不许任何声张。安安静静。”
“什么?!”舒紫鸢大失所惊,一脸错愕中带着不可置信的瞪大双眸直视着舒赫,甚至于就连身子也微微的颤晃了一下,“爹,怎么会这样?”
舒赫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那你觉的应该是怎么样的?皇上钦封你为太子侧妃?还是太子亲自派桥来相府接你进宫?”舒赫的脸上划过一抹不易显见却又真真实实的苦涩,“鸢儿,你不是她,何故做这般的白日梦?皇上对她是的态度与对你的态度从来都是两样的,就好似爹对你的态度和对她的态度从来都是两样的一样。再加之之前你与太子传出那般的事情,皇上与皇后本就十分不悦了。你还以为会让你体体面面的入宫吗?”
“爹,难道你就看着女儿这般委屈的进宫?”舒紫鸢双眸含泪委屈中带着凄凉的看着舒赫,“若非当初沈兰心的用计,相爷夫人这个位置会是她的吗?她舒清鸾会是相府的嫡女吗?这一切本就是属于娘和我的,为什么现在却什么都被她舒清鸾拿了去?为什么女儿就得这般屈居于她之下?爹,女儿并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娘,为了爹的脸面,更是为了我们相府的颜面。我是爹的女儿,是相府的二小姐,可是现在却连一名宫女都不如的默默无闻的进宫。爹,就算女儿真进宫了,您让女儿以后如何在宫里立足?如何与那百里飘絮一争高下?”
舒紫鸢的意思何不就是他的意思,可是现在,他还能做何?
“皇上圣意已下,爹做为臣子,无能为力!”舒赫沉厉的双眸直视着舒紫鸢,“如你真想在宫中站稳一袭之地,从现在开始,你就好好的想想,到底自己该做些什么?你只能这般进宫已成定局,既如此,那便把心用于该用的地方。”对着舒紫鸢挥了挥手,示意她离开,“回去自己好好想想,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舒紫鸢张嘴还想说什么,然而突然这间似是想通了一般,略显倒三角的媚眼里划过一抹精芒,对着舒赫侧了侧身:“女儿告退。”说罢,转身离开了舒赫的书房。
舒赫重重的一拳击在了椅扶上,脸上满满的尽是阴霾与戾气。
尚书府
南宫樾坐于靳破天对面,手里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碧螺春,“最近本王听到一些关于你的谣言,很是有趣,你可曾有听说?”
靳破天不以为意的抿唇一笑:“那么王爷如何看待?”
举杯至唇边,轻吹一口气,饮上一口热茶:“本王对于谣言如何半点不关心,不过对于是谁传出这谣言倒是更有兴趣。”
“下官如王爷一样,对于传言者更有兴趣。”靳破天目不斜视的与南宫樾直视,“看来,似乎有人很想下官与王爷失和啊。”
“哼”南宫樾冷冷的一哼声,“打算什么时候娶柳大人的千金过门?”突然之间话题一转,竟是直接转到了柳悠娴的身上,“本王听说,柳小姐为了救你身中奇毒。相诗的医术不在于太医之下,是否需要本王帮忙?”
靳破天摇头:“下官谢过王爷好意。不急。”一脸的高深莫测中带着隐隐的诡异地,完全让人猜不透此刻他心中所想。
南宫樾会心一笑:“你不急,人家急。”
“这不正好,急了才能跳墙。若是狗不跳墙,又怎么能不费吹灰之力的将其捕之呢?”靳破天似笑非笑的看着南宫樾,“王爷,您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