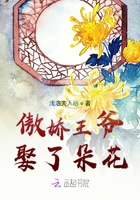五运相互承续循环,是国家大事,历来载籍,都有明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相续,但有不同。后梁自命承续大唐“土德”而为“金德”,但后唐却不承认后梁,而自认后唐就是对大唐的恢复,所以后唐与大唐是一个圣统,依然属于“土德”。在后唐看来,“五德终始”的天命关系中,没有后梁什么事。后梁不过像夏王朝中间出来个后羿、寒浞,汉王朝中间出来个新莽一样,都属于篡代,非正统。后唐中兴大唐,理应是正统。
在此之后,后唐“土生金”,代替了后唐的后晋就是“金德”;后晋“金生水”,代替了后晋的后汉就是“水德”;后汉“水生木”,代替了后汉的后周就是“木德”;后周“木生火”,故代替了后周的大宋就是“火德”。
从国初到现在,二十五年,已经有过多次祭祀大典,而且天下承平,显然这是上天降佑,祖宗显灵,“火德”这一圣统是符合天心的。因此,不要听信布衣赵垂庆的这类意见,“伏乞圣宋永为火德”,我匍匐而请求:我神圣大宋,永远属于火德。
史称太宗“从之”,接受了徐铉的意见,“火德”没有改。
可以推知,赵光义之所以改名赵炅,自有附会“火德”,应天顺人之意。
有一故实,可以约略看看赵光义对“火德”的自信。
红鸟与白兔
公元995年,是至道元年。这一年,纳土归宋的吴越国最后一任国王钱俶,他的从子钱昭序,正在执掌通利军(属河南开封),辖境内发现了一只红色的鸟,一只白色的兔子。红鸟、白兔不算稀奇,稀奇的是这俩同时出现,被人同时捉住。
按照传统神秘家言,红鸟代表太阳,白兔代表月亮。这俩一个属于“阳精”,一个属于“阴瑞”,同时出现,就有阴阳和谐的意味,而“阳精”则恰好属于“火德”。这就等于大宋到了太宗一朝,有了“火德”的“祥瑞”。而“火德”昌盛,更意味着其他“德”应该“服膺火德”,譬如位于大宋西部的西夏,就属“金”。现在有红鸟、白兔这样的“祥瑞”,这是“示金方驯服之征”。表示西夏就要有驯服大宋的征兆。
钱昭序将这俩东西带到朝堂,上表,说了这一番道理,认为这俩东西属于“希世之珍,罕有同时而见”,希望能将此事通告史馆,也即国家历史档案馆,记录下来。太宗看到了红鸟和白兔,答应了钱昭序的请求,并且对近臣说:“乌色正如渥丹,信火德之符矣。”你看那红鸟,颜色红得像红百合,可以相信国家“火德”的征兆了。
赵炅,相信天命,但并不特别相信“祥瑞”。各地经常有人“献瑞”,他都做了很低调的处理,只有这个与“火德”有关的“祥瑞”,他给了肯定性的意见。按照天下治理原则,“炎宋”的“火德”,预示了王朝正朔,是天命条件下的德能彰显。在契丹、西夏、吐蕃等诸邦觊觎之下,王朝应有“顺应天命”的表征,以此宣示内外。后来的真宗皇帝策划天书符瑞,荧惑朝野,泰山封禅,兴师动众,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理解。
改名赵炅的宋太宗,初期还没有“金方”西夏的问题,按照方位,最大的地缘问题来自北方,那里有个强悍的恶邻:契丹。正是因为契丹,才使得北汉至今顽梗地存在着。但赵炅认为可以用一代人时间造就太平天下,他也有能力成为一代“太平天子”。但“太平”的条件是河山一统,是为中原治理争取更多合理的地缘生存空间。
大宋帝国,当人们期待以后不再打仗,期待天下太平时,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新科皇帝赵炅,久久萦回不去的第一个念头是:
平定北汉,收复河东。
但他将这个念头雪藏起来,不说,不动,一直在隐忍。
诏罢河东之师
河东,黄河之东,在今天的山西中部和北部,中唐五代以来,为天下第一藩镇所在,现在,北汉在那里。
就像当初赵匡胤面对南唐,忍不住要咆哮一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一样,赵炅先生面对蜷缩于河东的蕞尔小国北汉,也恨不能如此这般咆哮一句!当初周世宗柴荣费九牛二虎之力,没有拿下北汉;赵匡胤也曾经顿兵于太原城下,功亏一篑。北汉,如此顽固!
最近一次,赵匡胤出兵平北汉,已经两个多月,虽然北汉还在那里,不倒,但它已经摇摇欲坠。京师汴梁,不断地接到来自前线的捷报。现在,哥哥赵匡胤不在了,他派出去征讨北汉的军队还在那里,怎么办?
继续征讨,还是调回?
太宗赵炅思前想后,最后,拿定主意,在国丧期间颁诏,调回了前线的征讨大军。史称“诏罢河东之师”。
他为何要召回看上去胜利在望的北伐军?
北汉政权一直得到契丹的支持。但宋太祖时,大宋已经与契丹“通好”,契丹对赵匡胤、对大宋有敬意,对困守河东的北汉则更多了约束,要求他们不要撩拨大宋。
北汉主刘继元感觉到契丹与大宋的“通好”,不免忧惧丛生,甚至想过破罐子破摔,干脆南距大宋、北战契丹,与两个大国决一死战,最后经臣下劝谏才放弃了这个昏妄的念头。
赵匡胤在世的最后一年,感觉到了河东与契丹之间微妙的政治裂痕,于是抓住难得的战机,开始收复河东。当时派出两大指挥官: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禁军马军总司令)党进为河东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河东前线马军、步军总司令),宣徽北院使(略相当于中直机关副总管)潘美为都监(河东前线总监)。这两位前线指挥官干得不错,开宝九年冬十月之前的几个月,不断传来捷报,宋师已经包围了太原,大有指日可下之势。契丹接到北汉泣血请援,一直拖了很久,才派出援军缓缓前来,在石岭关与宋师发生一场战事,败归。但并没有提出终止与太祖的“和约”。失去了契丹有力支援的河东,似乎就要覆亡了。但是,现在,前线将士们得到太祖赵匡胤病逝的消息后,同时得到了新任皇上班师回朝的命令。史称党进、潘美等人,“皆自行营归阙”,都从前线军营回到朝堂。
这是太宗践祚之后,做出的一个有意味的重要决定。
党进、潘美等人,乃是太祖时名将,现在太祖驾崩,前线将军有理由回朝参加葬礼。而命令他们回朝的乃是新任大帝宋太宗。他们接受了调遣,也即意味着军权在中枢。中央集权,对于藩镇割据而言,具有秩序价值。党进、潘美之流,如果在前线“辉煌”,承五代流风,不幸被“权反在下”的将士们“阴谋拥戴”,乘国丧期间杀回京师,是可能的——晚唐、五代以来,这样的“阴谋拥戴”,反复上演。更吊诡的是,往往不是主帅造反,而是被部下“拥戴”,不得不反。所谓“部下”,基数庞大,良莠不齐,怀有造反发家念头的不逞之徒,二百年来,并不罕见。假使部下已反,主帅不反,那就有两个结局:主帅回到朝廷,是死罪(事实上也回不去);不回朝廷,是死事(将士们会杀掉主帅,另外“拥戴”他人)。故主帅一旦被将士“拥戴”,只有造反一途。二百年来,中原大地,多少次上演这类充满血腥汗臭的故实。太宗不想出现这类格局,于是抓住时机,行使帝王权力,彰显最高权威。此举自有遏制藩镇流风,捍卫大宋秩序,将可能的悲剧消弭于无形的良苦用心。
说宋初直至太宗时代,武将们多少还遗留着五代藩镇习气,不是虚言。
与太祖时一样,太宗也不主动侵扰契丹。他在践祚的第二天就下诏颁下“五条意见”,其中第二条意见就是命令边境将官,要约束属下士兵,不得侵扰境外契丹之地。
但这个诏令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马仁瑀大闹闻喜宴
当时的边将,瀛州(今属河北省河间)防御使马仁瑀,负责管理霸州军(今属河北),另一位边将李汉超,正做着齐州(今属山东济南)防御使,但被扩大管辖范围,来做云州观察使,同时继续管理齐州军政。李汉超的职责是监管关南屯兵。云州,在今河北北部张家口一带,地理位置已经与契丹犬牙交错。所谓“关南”,乃是当初后周世宗柴荣时,从契丹手里收复的瓦桥、益津、淤口三关(其实还包括瀛州、莫州等地),中原人于是习称这三关以南之地为“关南”。其地略相当于今天河北省西北迤逦东南一带。周世宗打下的关南之地,被大宋所继承,这是自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中原军民“恢复中原”最好的战略成果。
且说马仁瑀。
这位大将军幼时不好好上学,总是逃课。他爹把他弄到乡校去读《孝经》,学了十多天,一个汉字没认识。老师用木板打手心、打屁股,弄得小小马仁瑀怒自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夜半三更,一把火烧了学堂,老师梦中惊醒,在好大一蓬烟火中,跌跌撞撞逃了出来。
据说马仁瑀少时与乡里孩子玩游戏,总是做出排兵布阵的模样,自任“将军”。每次与孩子约定时间,有来晚的,就抽人鞭子。孩子们都怕他。但他又常常买了果子分给伙伴们吃,总是分配很公平。孩子们又都服气他。
青年时期,马仁瑀几乎无师自通,射箭有一套,能挽二百斤强弓。后汉时,投奔到邺镇(今属河北邯郸)郭威麾下。他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赵匡胤,因为据资料推断,赵匡胤从军,也在郭威镇守邺镇时。周世宗时,高平一战,他与赵匡胤同时立功。
周世宗征淮南,攻打楚州水寨时,见水寨中间建有一座飞楼,高达百余尺,相距二百步。飞楼上有南唐瞭望士卒,以为周师奈何不得他,就高声谩骂。周世宗大怒,命令左右向那厮射箭,但是距离太远,射不到。马仁瑀不声不响,扯过弓来,拉满弦,只见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嗖的一声,那厮“应弦而颠”,跟着弦声响过,一头栽倒。
随后,他在跟随周世宗南征北讨时,屡立战功。后周末年,已经做到龙捷左厢都指挥使,禁军左路军的总司令。
大宋建国后,他跟随太祖赵匡胤,平定泽潞(今属山西)时,率师巡边。大军曾到幽州境内,契丹早就听过他的大名,蜷缩着不敢出来。马仁瑀就放纵士兵四野略夺,劫了成千上万的牛马羊。后来又奉命随军征讨川蜀,所在有功。在山东做密州防御使时,群盗在兖州一带活动,首领有一人状貌奇伟,大高个子,身手敏捷,江湖人称“长脚龙”,很为盗贼畏服。当地监军多次征讨,不利。马仁瑀知悉后,率帐下十几人进入泰山,擒了“长脚龙”,平定了齐鲁匪患。
从小胆大妄为的一条好汉,眼里揉不得沙子。
当时赵匡胤的小舅子王继勋常常对将帅们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子来,诸将因为他是皇后的兄弟,不免礼让三分。只有马仁瑀不买他的账,曾经有几次要撸胳膊挽袖子揍这位皇戚。俩人甚至暗暗约定,要在太祖郊区讲武时,私下械斗。老赵得到消息后,谁也不得罪,干脆取消了这次讲武活动。
名相薛居正主持科举,马仁瑀请托照顾某某人。但是到了放榜时一看,某某人名在孙山之外。举子们及第,要吃“闻喜宴”,马仁瑀在自家府邸喝高了酒,带着某某人,大闹“闻喜宴”,当着诸考生狠狠地呵责薛相一番。相国岂可随便凌辱?此事闹大,被专门负责纠弹百官的御史中丞告到朝廷,太祖赵匡胤也不过轻描淡写处理一番完事。赵匡胤知道,马仁瑀还有另外一面:执法公正。他一恶侄杀人,苦主被恶侄派人游说,放弃了司法追究,但马仁瑀还是坚持按照法律程序处理了杀人犯,并给苦主一家安排后事,做了经济补偿。
马仁瑀,就是这样一个人。老赵了解他,对他很优容。
到了太宗朝,刚刚上台的赵炅刚刚出台了不得侵扰边境的诏令,马仁瑀就给新科皇帝来了个难堪。
他居然置大宋诏令于不顾,擅自发动麾下兵马,进入李汉超与契丹胶着的边境地带“略夺”,扩大地盘。
李汉超也是生猛将军,镇守关南,契丹多年不敢觊觎。
宋人田况《儒林公议》说一事。说李汉超带精兵五千,常驻高阳关,此地在今天的河北高阳县境,是契丹南侵的必经之路。李汉超总是担心兵少,就派遣他的儿子带着奏章到朝廷来请求增兵。太祖赵匡胤迎着他说:“是不是你老爸让你来请求增兵啊?”于是让他吃饭,并对他说:“你爸要是不能办我的事,那就等着契丹斩了你爸的脑袋,我再用能办我事的去守边关。兵,我是不能增加的。”然后又解下宝带,让他带给李汉超,还给了优厚的赏赐。从此李汉超能够奋励守边,终其一世,契丹没有能够入寇。
但马仁瑀从关南“略夺”,就涉及李汉超防地的安全问题。于是两大边将从此“交恶”,有了冲突。如此,北境会发生什么事?略知“五代史”,就可以大致推知:格局莫测。
置酒讲解
太宗承继了太祖家法,对这两员悍将也不想“严肃处理”,但边衅一开,如果契丹介入,譬如,像当初契丹收买石敬瑭、赵延寿、杨光远、杜重威一样,收买李汉超或马仁瑀成功,那就又是一个乱哄哄的“五代十国”!
隐患凶险,不得不防。可能的祸患,连萌芽都不让它出现,所谓防患未然,是政治家至为高妙的管理智慧。
自从五代藩镇割据以来,抑制武夫们可能的祸乱,让邦国实现文官治理,是太祖赵匡胤以及大宋历代君王的第一选择——无论发生什么事,可能导致什么结果,大宋再也不允许出现藩镇割据!要理解从“杯酒释兵权”到“冤杀岳鹏举”到“蒙元亡大宋”这条逻辑链上的军政大事件,藩镇割据问题,是大宋历代君王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事实上,从东汉末年“诸侯兼并”以来——直到民国初期,藩镇割据,确实是祸害中原的恶性政治肿瘤。德能兼备的政治家,必须有抑制这个肿瘤生长、割除这个肿瘤存在的英雄手段。大宋历代君王,在这个政治格局中,与汉魏晋隋唐乃至于元明清民国比较,是做得最出色的。终大宋帝国三百年,无藩镇割据事件出现。
但造化潜施,阴阳秘运。大宋在警惕这个“肿瘤”时,却遭遇了史上最糟糕的地缘政治格局。后来的日子里,强悍的女真、蒙元与大宋同在,让中原大宋在闪展腾挪中,由于不存在藩镇力量,也同时失去了地方武装的加持。此事说来话长,容我以后慢表。
且说两将“交恶”,已经构成了可与藩镇割据之乱世产生联想的重大事件,作为邦国领袖人物,必须要处理,抑制可能的“肿瘤”生长!
赵炅选择了一个很有效益的政治平衡点:
“遣使赍金帛赐汉超及仁瑀,令置酒讲解”,派遣使者带着金钱布帛,赏赐给李汉超和马仁瑀,让他们二人置办酒席好话好说,彼此和解。
这路数很像江湖黑道手段,体现了新任帝王的宽厚,但“令置酒讲解”的“令”字,却透露着“老大”的身份地位,五代时期过来、浑身带着江湖气的两位边帅能够感觉到:老大就是老大,毕竟身份不同。昔年赵匡胤都与武夫大佬们结成过“十兄弟”,宋初的武夫们熟悉这种路数。所谓“杯酒释兵权”,很大程度上,也是老赵操练江湖路数解决了藩镇割据隐患。与乃兄比,太宗是个读书人,也不得不对江湖“规则”高看一眼。太宗一纸诏书,“令”二位边帅“置酒讲解”,让二位边帅瞬间感受到新科皇帝的强大气场,于是二人握手言欢。
赵氏兄弟懂江湖路数,但在国家治理方向上,并不依靠江湖路数,而是依靠儒学经典以及《誓碑》《宋刑统》所揭橥的政治正义。这一点很像孙文先生。孙先生当年曾与洪门力量来往,很懂江湖路数,但民国治理,并不依靠洪门,而是依靠《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以及“六法全书”所阐述的政治正义。大宋政权之取得,从合法政府后周朝廷“禅让”而来,但后来不仅成全了柴氏后人,更推演“天下为公”之政治正义,乱世以来的风气为之一变。史称“逆取顺守”,也即悖逆而得天下,循理而治天下。赵氏兄弟有时不得不借助江湖路数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似也可从“逆取顺守”的格局中,揣度一点政治伦理的复杂性。